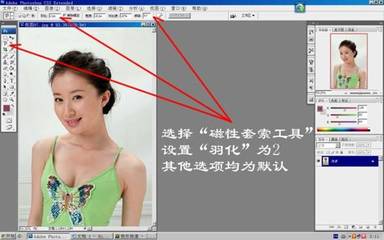文/马戎戎
2004年11月9日,《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的作者,第一个向西方社会披露南京大屠杀历史真相的美国华裔女作家张纯如在美国加州吞枪自杀。传媒普遍认为她生前活在日本右翼势力恐吓阴影中,不堪精神重负而弃世。2007年3月30日,记者在南京专访了张纯如的父母张绍进和张盈盈。
每年的3月28日,张绍进和张盈盈都要到女儿张纯如的墓地上去探望,因为这天是她的生日。2004年11月9日上午,1997年以《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一书成为美国最受瞩目的华裔畅销书作家的张纯如在加州自己的汽车内吞枪自杀,当时她的儿子不过两岁。对她的父母来说,女儿的去世是这一生都难以抹去的阴影。 “女儿死后,我们一度不知道怎么生活。”张纯如的父亲张绍进说。 “纯如去世两年多,两年多来,每一天我们都会问自己,究竟她为什么要自杀?不知道问了多少遍。答案是,没有答案。”母亲张盈盈说。她说,也许有一天,她自己会就这个问题写一本回忆录。 2007年,是《南京大屠杀》出版10周年,从2006年年底开始,加拿大女导演安妮·匹克在加拿大NGO组织——加拿大战争史实维护会(简称“史维会”)和在香港地区大地娱乐公司的支持下,开始着手拍摄纪录片《张纯如》,2007年3月30日,《张纯如》彻底结束了国内的拍摄部分。安妮·匹克对这部纪录片的阐述是:“我们要讲的是女作家如何深入探索一段黑暗的人类历史,并将它还原成文字,著成一本震撼人心的畅销书的故事。这部电影不仅是张纯如的故事,还讲述了1937年发生在南京的故事。我们的电影通过一个勇敢的年轻女性的眼睛,见证了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事件和非人道行径。” 关于纪录片的结尾,安妮·匹克说,她正在设想,以“张纯如的葬礼”来结束。但是她却同样回避了对张纯如死因做探讨:“我回答不了她为什么会在做了母亲之后,依然选择了自杀的方式,我只能说,没有答案。” “我们并没有想到过她会自杀。”张纯如的父亲张绍进依然无法掩饰自己的悲伤。这几乎也是所有从媒体、书籍中认识张纯如的人的困惑。纪录片中,所有关于张纯如的部分,安妮·匹克采用了演员扮演的方式。在纪录片《张纯如》中,扮演张纯如的是加拿大裔华人郑启蕙。郑启蕙长得像张纯如,争取这个角色的时候,她就带着张纯如的照片,举在脸旁,跟导演比划,“你看我像她吗?我演她最合适了”。郑启蕙知道张纯如这个名字时只有18岁,“18岁时,我从一本畅销杂志《读者文摘》的封面上看到了张纯如。我觉得一个华人能登上这样的杂志封面十分了不起,于是开始看她写的书,搜集她的资料。我想写一篇关于她的文章,但还没来得及写,就听说了她自杀的消息,伤心了很久。” 得到出演张纯如的机会后,郑启蕙天天在揣摩张纯如的心情,她拜访了张纯如的朋友、同学,还曾来到南京体验张纯如搜集资料的生活。但她依然无法理解张的自杀:“所有人都觉得她那么坚强,人生很完美。如果我是她,我不会自杀的。” 无论在父母还是在朋友眼中,张纯如都不是一个软弱的女人。张纯如出生在典型的美国华人中产家庭,父亲张绍进,是物理学博士,母亲张盈盈,是研究生物化学的博士,他们都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从台湾地区到美国的新移民。在母亲张盈盈眼中,张纯如“很开朗,是一个很爱说,很爱想的人,希望知道别人的想法,朋友很多。但是她不喜欢做领导者,不喜欢被人追随。她对什么事情都很有主见,总是笑那些追随时尚的人很盲从。她成为独立写作者也是因为不喜欢别人让她去写这个,写那个”。 张盈盈强调,张纯如在美联社、《芝加哥论坛报》的经历只是“实习记者”,做了几个月实习记者后,她退出了媒体,回学校读写作硕士,拿到学位后开始成为一个独立作家,“这本书的选题是她自己报的,开始拿到的启动资金很少,只有几千块,但她立即就去了南京,根本不去想钱的问题”。 与很多人的理解不同,至少在开始几年,《南京大屠杀》一书带给张纯如的影响,更多的是正面而非负面的。 朱成山是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他第一次见到张纯如是在1995年的8月9日。当时,张纯如只有27岁,汉语还说不好。张纯如打动他的是她的“正义感”:“她当时对我说,很长时间以来,西方国家只知道纳粹屠杀犹太人,不知道侵华日军在‘二战’中也疯狂地屠杀中国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自‘二战’胜利以来的几十年,在西方有关日军侵华史实的宣传太少,声音太弱。”

再次见到张纯如,已经是6年后美国旧金山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对那时的张纯如的印象,朱成山用“敏锐而坚毅”来形容她。他提到:“她的演讲题目是‘强奸南京’,当场就有两个日本人站起来向她发难,张纯如立即据理驳斥,批得两个日本人语无伦次,最后只有夹着包灰溜溜地逃离会场。” 在父亲张绍进的眼里,写作《南京大屠杀》之后的女儿“变得越来越有自信。”1998年,日本驻美大使公开发表声明,污蔑《南京大屠杀》是“非常错误的描写”。张纯如的反击非常强硬,她与齐藤邦彦一同接受“吉姆·里勒尔新闻节目”的访谈,当场驳斥。采访时,说起这一段,张盈盈的语气里依然满是对女儿表现的骄傲:“她非常强硬,非常正面的回击,她的英语又好又流利,结果那个日本人当场道歉。” 这一场论战如此成功,以致张纯如被当时的总统克林顿亲自接见。这时张纯如的社会活动开始多起来,1998年,她获得华裔美国妇女联合会颁发的年度国家女性奖。美国公众开始普遍将她看做是“人权斗士”。张纯如官方网页的记录显示,从1998年开始到2003年,几乎每个月都有一到两场在各个大学、学术研讨会上的演讲,内容大多是关于日军侵华、人权、人类社会的不公正等等。 张盈盈回忆,1998年后,世界上许多国家许多种族的人都来找张纯如,希望她能写写自己民族被侵害的历史,包括菲律宾的马尼拉大屠杀,还有印度一个小岛的历史等等。“到后来,纯如也觉得自己的确是在为人权做事。”张绍进说。张纯如的第三本书是《美国华裔史》,讲述华人在美国遭受的歧视。2002年,她开始搜集日本侵华受害人口述历史,而在她死前,刚刚结束了在菲律宾巴丹岛日军战俘营的旅行,准备着手写第四本书。张绍进说,对女儿的写作方向,他们曾表示过忧虑:“我们劝她第三本不要再写这个,但是女儿大了,我们不好干涉太多。” 对于张纯如死前的精神状况,张绍进和张盈盈承认了忧郁症的说法:“她身体不好,晚上睡不着觉,一周去看两次心理医生,但是没有用。我们觉得他们给她吃的药都是错的。”“她从前总是夜里工作,白天睡觉。但是有了孩子以后,她要带孩子,又要做工作,不能再这样做,很辛苦。”张盈盈不认为日本右翼势力的威胁打垮了张纯如,日本右翼势力的确给张纯如寄过两颗子弹,“我们问她,有没有人身攻击发生,她说没有。不过也许是她怕我们担心,不愿意告诉我们”。 张纯如死后,她生前的朋友、纽约大学电影系主任崔明慧披露说,张纯如生前一直带着枪,并说她不敢向人透露她有孩子,怕日本右翼势力对婴儿不利。但是张盈盈否认了这些说法,她强调说:“纯如从来不带枪,带枪只是最后期的事情。”她还说,崔明慧的很多说法“不是真的”。 张绍进和张盈盈提到,张纯如很爱看电影,而且总容易被电影感动。而在生活中,“她听人说话,会跟人家有共鸣”。张盈盈说,别的美国记者,尤其是做杀人放火等这样的社会新闻的,都很有理性,都会自动给自己设置一道“过滤程序”。但是,“纯如没有这个训练,她总是把自己给裹进去,投入得过深”。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王卫星曾为张纯如的写作提供过大量帮助,他的回忆印证了张纯如父母的看法:“她不仅重视文字材料,也注重到现场实地体验和感受当年所发生的事情。在当年南京大屠杀所有重要屠杀现场和丛葬地,她都拍摄、摄像或是陷入沉思中。从她向幸存者所提的问题也可以看出,她尽量想让自己置身于当年南京的环境中。她的问题常常具体到几时起床,早餐吃什么,穿什么样的鞋,走路的模样,以及当时的天气等。” 在加拿大“史维会”多伦多分会主席王裕佳眼中,张纯如的个性“十分单纯”。《南京大屠杀》一书在西方的流行,和王裕佳的推广有很大关系。“史维会”于1996年成立,完全是民间自发的NGO组织,这个组织的宗旨是致力于保存亚洲地区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实,维护公义,促进人文教育和种族和谐。王裕佳用自己的钱邀请张纯如到加拿大,宣传推广《南京大屠杀》,使这本书从加拿大开始,轰动了西方国家。 “这本书能够成功,很大程度是因为张纯如的身份,她是华裔,但她是美国人。如果她是中国人,就很容易让人觉得是政治宣传。”王裕佳说。 张绍进和张盈盈说,张纯如去世后,他们一直致力于继续女儿的事业:“把历史真相公布于众,是中国人的使命,也是纯如的遗志。”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