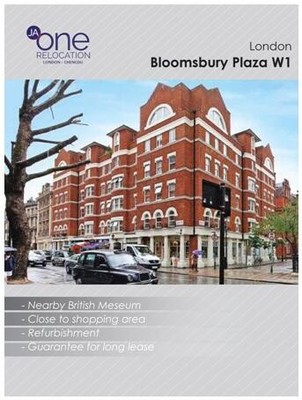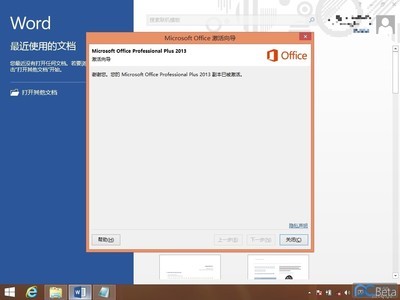文/苌苌
可能是中国越来越值得被认真对待了,最近有个有趣的文化现象,西方当代艺术的重要作品齐聚中国。3月20日“余震:英国当代艺术展1996~2006”在首都博物馆开幕,达米安·赫斯特的作品来了,翠西·艾敏的作品来了,还有查普曼兄弟等的作品,和同期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美国艺术300年”遥相辉映。在欣赏这些极大影响了中国当代艺术家的作品的时候,想到影响了这些英国青年艺术家的美国艺术家杰夫·昆斯等人的作品正在几公里外展出,的确是件奇妙的事情。
最早,英国文化协会是想延续前几年举办亨利·摩尔和安东尼·葛姆雷雕塑展的经验,再在中国做一个英国雕塑回顾展,但后来觉得不足以说明英国文化的真正状况,策展人秦思源与皮力于是经过两年筹备,把英国当代艺术史上最辉煌的一段时期搬到了中国——那就是引起英国整个90年代“文化艺术爆炸”的YBA现象。 YBA现象 YBA是“英国青年艺术家”(Young British Artists)的缩写,最早成规模地出现是在1988年。那一年,达米安·赫斯特在伦敦策划了“冰冻”(Freeze)艺术展成为这一现象的开端。参加者多为他在伦敦歌德史密斯学院的校友,他们给英国当代艺术带来一种新风尚:采用的材料和创作过程比活跃在六七十年代的艺术家更加匪夷所思,精神上体现出一种主张对抗、追求精神进步,但也是玩世不恭的态度。这在当时根本不为博物馆和商业画廊接受,展览不得不在伦敦东区一个廉价的仓库内举行,媒体的反应也很冷淡。 但就在随后10年,“英国青年艺术家”成为英国新文化意识崛起的象征,在英国社会引起重大变革,首先,它改变了艺术和时尚、媒体的关系,这些艺术家被认为是又酷又炫的,他们的作品直接影响到英国时尚和设计的创造力,他们几乎一夜成名,赫斯特等人更被打造成艺术超级明星。它改变了英国的博物馆体系,2000年,现代泰特美术馆的开放,作为这类作品的主要展地,被看做是这一现象的纪念碑。它改变了现代艺术教育和商业操作模式,巩固了“反学院派”的学院派,它对世界当代艺术产生重大影响,之后,你可以用“欧洲艺术中心”称呼伦敦了。 而YBA与英国社会政治相辅相成的关系,如今更被运用为政治学管理研究的典范。1979年撒切尔夫人上台,在当时的左翼文化人士中有一个深入人心的共识,就是保守党的政策和思想不怎么对艺术有好感,尤其是对前卫艺术持厌恶和狭隘的态度。保守党执政英国政府直到1997年,以布莱尔为代表的新工党在选举中获胜,希望树立年轻和变革形象的新工党,需要一种可与之结盟的新兴文化,充满活力的YBA恰巧满足了他们这一需求。 新工党后来被证明对创意文化并不真的关心。但最初,他们对这些文化现象表现出极大兴趣,整个90年代,“英国青年艺术家”和“新工党”两个名词频繁出现,英国文化又恢复了蓬勃活力。在此之前,它已经郁闷了几十年了,60年代他们有披头士,有滚石,最好的摄影师大卫·贝利和西西尔·比顿,影响时尚界风尚的模特儿特威格(Twiggy),都生活在那个时代的英国。1966年,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故事就是“伦敦!一个多姿多彩的城市”。70年代尚有“性手枪”,有朋克,80年代有什么?但到了1997年,美国《名利场》的封面呼应了60年代的观点——“伦敦再度多姿多彩!” 90年代的英国,无论流行音乐、时尚、美术、媒体还是设计,都获得了全新的风格和态度,但它也带着一种复古的意味。从很多方面说,当时英国文化艺术的构成和60年代中期极为相似。比如对“英式风格”的迷恋(Brit被时髦地用作对British的缩写,比如时髦小孩经常挂在口头的Brit-Pop,外形上可联想Verve和“新裤子”乐队的服装发式),对所有老套东西的蔑视,对新技术、性别特征和城市文化充满活力的拥抱,这些都是60年代和90年代共享的时尚因素。另外,“英国青年艺术家”似乎还继承了一些朋克传统,它们的作品经常把观众推入精神临界状态。比如翠西·艾敏的《1963~1995:所有和我睡过的人》,是一顶里面绣满和她睡过的男人、女人的名字的帐篷,赫斯特把鲨鱼弄进福尔马林药缸,又把小牛从中间一劈两半。 社会力量对YBA现象的推动,一个收藏家的作用功不可没,他就是广告业的大鳄查尔斯·萨奇。早在“冰冻”艺术展,他就在现场了,而“英国青年艺术家”这个称呼就是他给起的。他还是萨奇画廊的主人,有过人的眼光和魄力,他先于所有人,以极大的热情拥抱这些艺术家。早在1989年,他以100万英镑收购赫斯特的《圣歌》,把赫斯特本人也惊着了,日后这个拥有亿万英镑的艺术家说,那是他第一次对金钱的力量感到害怕。1997年,他举办“感觉:萨奇收藏的英国青年艺术家作品”的时候,每天吸引3000人参观,媒体竞相报道,展览也成为YBA现象的里程碑。 YBA的风格和立场基本无法总结,但有一些相对具有普遍性的特征。他们是后现代消费社会里成长起来的第一代,“披头士”的歌是他们的摇篮曲,作为艺术专业学生,他们系统地学习过批判性理论,但常常把粗俗的意象和冷静的微妙的概念结合在一起,手法夸张,非常自我,忽略政治,切入社会主题或自身问题,往往非常直接。热衷于反理性(也被人视为做作),他们的早期作品好多看上去的确让人怀疑就为吸引眼球似的。也有人说“穿上讽刺的外衣,贴上都市智慧的标签,转换为艺术创作的深奥语言,但不妨碍与小报分享价值”。YBA对后来艺术家的影响自然不必再多说,但是进入21世纪,新的英国艺术家中还出现一个现象,就是对YBA产生审美疲劳。“反YBA”的艺术——回归到一个安静的状态,讲究技法,潜心研究现代主义——也应运而生。所以展览名为“余震”(Aftershock)。 YBA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影响 策展人皮力用“一颗种子要发芽”形容这场展览,他希望展览能给中国的艺术家和爱好者带来一场新的头脑风暴,就像当年“吉尔伯特和乔治”展带给他的一样。 1992年“吉尔伯特和乔治”刺激中国艺术青年的同时,在英国也催生了YBA革命。在带着参观的时候,皮力一再强调展览的现场感,YBA作品的一个特点,就是必须到现场观看才能感受到它的魅力和震撼力。 YBA的繁荣正好和中国当代艺术的萌芽在同一时期,皮力讲起一件趣事,当年,萨奇的“感觉”展画册是很多中国年轻艺术家的必读书之一。因为看不到原作,艺术家只能猜测是怎么回事。在“余震”的现场,看着那些作品,就特佩服中国艺术家的想象力。比如从画册上看不过是一张照片的吉莉安·韦英的《60分钟沉默》,其实是一部持续60分钟的录像。在现场可以看到,警官们尽管试图保持不动,但身体的疲劳和紧张,让他们时而做出抓耳挠腮状,他们的制服是威严的象征,韦英通过暂时的约束,把他们置身于紧张状态中,给了观众审视他们的机会,实现角色的反串。这个想法,也许激发了J.K.罗琳想象出魔法界那份奇妙的报纸也说不定。还有山姆·泰勒—伍德的《小小的死亡》,是以4分钟录像记录一只兔子在10天时间内的腐烂过程,构图仿古典主义的静物画,加速把所有的心理不适都取消了。而与之相对应的《10米/秒》,则是把一段“一战”时期的医学胶片慢放,一个看似在做体操的男子,到后来才让人意识到,因为他是个外伤致残的受害者,艺术家道格拉斯·戈登想要论证,我们对环境的感知来自它呈现给我们的方式。尽管YBA艺术直到今天才能来中国展览,但是其影响却是早就扩散开来。在2000年一个由栗宪庭策划的“对伤害的迷恋”的展览上,参展艺术家分别使用了人和动物的尸体、血液和脂肪油,来完成他们的作品。
这些作品被认为和社会深层的动荡有密切关系,同时也暗含对东西方社会道德的双向挑战意味等。1999年,邱志杰和吴美纯策划了“后感性”,仅从展览名字,就能体会到“感觉”展对中国当代艺术家的影响。“但问题是,”皮力说,“中国没有一个有效接受外部信息的输入渠道,所有关于西方当代艺术的知识并不是在学校被传授,在电视媒体上客观地介绍,或者艺术家在海外留学获得的,而是来源于口碑相传,来源于老艺术家偶尔带回来的几本画册,他们甚至不能阅读文字。这就是中国艺术家的困境——年轻的艺术家在不了解原作的情况下,预支了那些没有价值的‘自由’以及在各种媒体传播和陈述中变异和沉浮的‘观念’。”但乐观地想,可能也避免了他们被西方观念过度支配——这一让人担心在西方留学的中国艺术青年身上发生的问题。 专访策展人秦思源 秦思源是中英混血儿,1971年生于英国苏格兰爱丁堡,90年代初在北京玩摇滚,后毕业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在大英图书馆工作时开始间接的艺术策展工作,现为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副馆长。 三联生活周刊:艺术家不见得考虑把作品给谁看,策展人却要想把艺术家的话说给谁听,你怎样挑选作品? 秦思源:必须考虑到中国现在还没有好的当代艺术铺垫,不是观众问题,接触任何一种语言都需要有铺垫。这些艺术品都不是政治性的,都是切入社会和人本身的问题,很直接,容易看明白。当然,我们考虑到国情,避免了一些过于刺激的作品。YBA的有些作品比较尖锐,国家体系就可能不接受,为什么这次巡展没有上海?上海不接。我们也想过介绍英国最新的东西,但最近的英国艺术都回归到研究视觉语言本身,还不如这些YBA好看明白呢。 三联生活周刊:一个遗憾,就是觉得作品有点少。 秦思源:有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就是作品借到借不到,我们列了单子,很有针对性地要一个艺术家的作品,但可能借不来。十几个艺术家同时要找很多作品,最后有的可能不是你最早要的,要有一个妥协,一个接近的状态。比如艾敏,当时想要的就是呈现一个相对完整的状态,比如有那张照片,还有那张椅子,都没想到还能借到床。但这张床不是那张床(指她备受争议的作品《我的床》),现在英国的两大报纸都在说这事儿,暗示说好像中国官方不让展,其实不是这样,是我们没借到,泰特现代美术馆不愿借出来。 三联生活周刊:翠西·艾敏对不少中国当代女艺术家产生过影响,普通观众应该怎么理解她? 秦思源:艾敏的作品看起来简单,其实艺术语言上非常到位。艺术对她来说是个自我疗伤的过程。她年轻时总是非常焦虑,曾经说过,要是没有做艺术,她早就死了,于是她把心理的创伤清理出来,但这个过程也可能做出非常糟糕的作品,而她不是,她找到了非常独特的艺术语言,直捣人的灵魂深处,也许是一种天赋吧。她的语言非常直接、纯粹,但不是那种不过脑子的直接,这批艺术家的艺术态度其实很严谨。她不玩政治,就是回到人性本身,她使用的媒介材料就是非常普通的日常用品——绣片,霓虹灯,但就把人性最基本的问题拖出来,为什么她的影响力这么大?她是唯一可以做到这一点的艺术家。
三联生活周刊:你是半个英国人,可能对“英式风格”有更好的转译,它的精神面貌到底是怎样的? 秦思源:当时社会有个氛围,那些年轻人看起来挺玩世不恭的,挺傲的,你可以相信奥西斯(Oasis)是真的一本书都没看过,但布鲁尔(Blur)看了很多书,他也要做出个没看过书的姿态。艺术家也是这么个态度,“我解释那么多干吗,累不累呀。”“我就这样,你爱理不理。”不像以前的知识分子,我要跟你讨论如何如何。比如有人问克利斯·奥菲利为什么用大象粪做作品,他说,“因为那是从大象屁股里拉出来的”。以无聊对无聊。但你看他在一些学术论坛的发言,他不是一个没有思想深度的人。还有翠西·艾敏上电视,喝高了似的,乱骂人,后来她成了明星也跟这有关系。萨拉·卢卡斯摆出一副恶狠狠的女性主义姿态,对英国社会都是一个刺激,尽管她们肯定不希望以此成为明星。赫斯特比较会炒作自己,但他的态度也是你知道就够了,能接受就接受。我是觉得这种感觉比较英国,在欧洲其他国家,不会产生这样的态度。 三联生活周刊:赫斯特现在是亿万富翁了,听说还要在伦敦郊区建一整条艺术街,整个一个艺术大亨? 秦思源:我想起一个问题,创意产业的概念在中国被扭曲,很多人认为就是拿艺术赚钱。创意产业应该是思考如何把创造性更好地作用于社会。比如像《星球大战》的导演乔治·卢卡斯,他以前是个非常实验的导演,如果这个艺术家有实验性,他可以有选择地去做一些和艺术有关的事,赚钱也许他很有商业头脑,而不是以赚钱为目的去搞艺术,那根本行不通。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