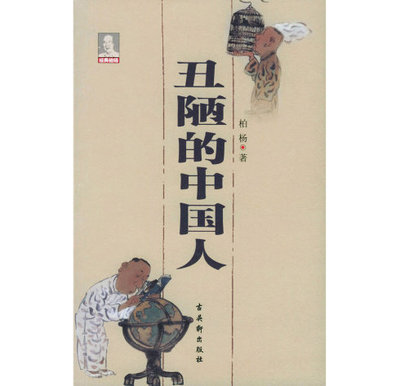文/张晓舟
在宋祖英获提名、李宇春也表达了无限向往之后,我们的脖子越来越长地伸向了格莱美,口水洒向了太平洋。不像奥斯卡,格莱美在中国还没出过一本指南书,光一份格莱美榜单就堪比荷马史诗了。但有几个古典乐迷会在乎迈克·提尔森·托马斯指挥旧金山交响乐团演奏的马勒第七获得两项格莱美呢?不管手伸得有多长,格莱美总是只被当作一个流行王国,所以你无法指责为什么媒体只报道R&B获奖者,而压根不提传统布鲁斯奖和传统民谣奖,即便获奖的是伊克·特纳(Ike Turner)和布鲁斯·斯普林斯汀这样的大佬。连爵士乐似乎都是被淡忘的。
既然格莱美和宋祖英能扯上关系,那我也想补充点格莱美和中国的关系,为什么中国媒体纷纷梦想或者已经开始跑到美国去蹭格莱美皮毛,却连正眼都不好好瞧一瞧一个接一个访问中国的格莱美获奖者——其中好些还是获奖专业户?
我说的当然不是玛丽亚·凯丽,虽然几个月前星海音乐学院漂亮的女学生确实惟妙惟肖地高唱玛丽亚·凯丽来欢迎班卓琴大师贝拉·弗莱克(BelaFleck)。当贝拉·弗莱克所在的麻雀四重奏的主唱王爱华介绍称这位班卓琴手前后曾获得过9项格莱美时,茫然的中国学生才发出了惊叹。这已经是贝拉·弗莱克第二次随麻雀四重奏来中国巡演,他不单传播了班卓琴,似乎还推广了格莱美。现在,他又第10次拿了格莱美,他的乐团Bela Fleck&The Flecktones凭专辑《The Hidden Land》获最佳当代爵士专辑。“弗莱克音调”当然是远比麻雀四重奏优秀的梦幻乐队,但上次在星海音乐学院,这位无比谦和的大师说:“我知道在中国没多少人知道我。” 他的官方网站首页根本没提格莱美,最新的新闻是他和爵士巨人奇克·科里亚(Chick Corea)合作演出。这两人恰恰刚刚“瓜分”了格莱美的爵士奖项,奇克·科里亚凭《The Ultimate Adventure》拿了“最佳爵士演奏专辑”。巧合的是,3月20日他就将来上海,合作伙伴是颤音琴大师加里·伯顿(Gary Burton),或许下一次奇克·科里亚与贝拉·弗莱克的新鲜组合也会有机会来中国。 获本届“最佳爵士乐器独奏奖”以及作为成员之一获“最佳爵士大乐团专辑奖”的迈克·布雷克(Michael Brecker)刚刚在1月14日去世,给格莱美增添一份凝重,这位萨克斯高人对中国并不陌生,十多年前他曾随保罗·西蒙来过中国。 从奇克·科里亚到小一辈份的迈克·布雷克,再到更小一辈份的贝拉·弗莱克,都堪称格莱美家族形象代言人,再清点追溯一下,另两位格莱美获奖专业户赫比·汉科克(Herbie Hancock)和温顿·马萨利斯(Wynton Marsalis)都来过中国演出。抛开爵士,最近还接连有格莱美人士要来中国,3月18日前卫/新古典弦乐四重奏Kronos Quartet和中国琵琶手吴蛮将在上海出演谭盾等人的作品,而3月26日、27日刚获本届最佳雷鬼专辑奖的鲍勃·马利之子吉基·马利(Ziggy Marley)则将访问京沪。言必称格莱美当然是可笑的,但格莱美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么浮华肤浅,媒体和乐迷只热衷于流行、R&B、舞曲、HipHop、摇滚,这难免掩盖了格莱美在更多其他音乐门类里的苦心经营。 当然格莱美始终是保守的,容易唯大牌与销量是瞻,偶尔还会出个把不伦不类乃至荒唐的笑话。成熟一点的乐迷当然知道把新世纪音乐奖给恩雅把雷鬼奖给吉基·马利有些无聊,然而,一个如此成熟的唱片工业总是能提供一个大致可靠的说得过去的音乐标准,格莱美办到49届也快知天命了,它的问题绝不会是简单、粗俗、幼稚、势利乃至腐败——这些统统都属于中国的音乐奖——而是成熟得未免有些烂熟。 所谓成熟,就是重视传统,确立经典——不断将一些音乐、一些价值予以经典化。同时还高度重视跨界杂交品种,本来格莱美就是个大杂烩,一个三头六臂的怪兽。不少得奖专业户都是跨界的老手,比如迈克·布雷克横跨流行与爵士,温顿·马萨利斯纵横爵士与古典,贝拉·弗莱克拿的10个奖五花八门,从民谣到蓝草,从爵士到世界音乐无所不包。格莱美以此展现包容的视野和融合的魄力,而对于本土音乐传统则不惜变本加厉地倾注巩固,比如贝拉·弗莱克的班卓琴蓝草传统背景,更突出的例子是从1984年到1986年,格莱美连续三年给年轻的温顿·马萨利斯“三冠王大满贯”,尽管此后这位小号手依然对查理·帕克在美国没有被看作像舒伯特那样的大人物而感到愤愤不平,但时至今日,应该说从查理·帕克到温顿·马萨利斯的爵士乐已经获得了经典地位,这其中也少不了格莱美的推波助澜。在讥讽格莱美沦为老人院和名人堂的同时,还是应当看到它尊重、弘扬传统,在传统和当代之间逐步确立经典标准的功用——奥斯卡是美国人的眼睛,格莱美是美国人的耳朵,那始终是一个幽深的美国梦,尽管年纪大了耳朵容易变得不好使。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