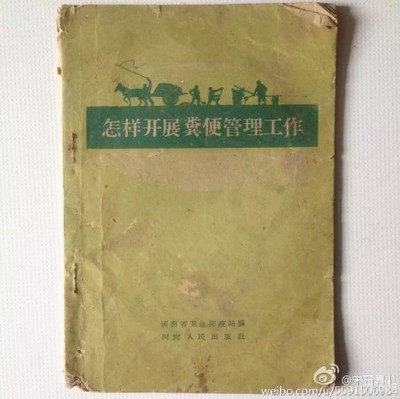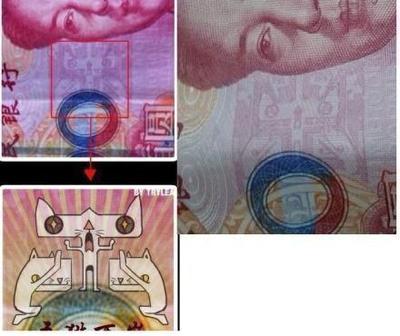黄湘源 至今仍能听见喋喋不休的反对中国股市救市的言论,这让我们不由得想起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1997年亚洲发生金融危机的时候,坚持自由市场主义的国际货币组织和金融机构以拒绝救援要胁首当其冲的东南亚,不准它们的政府出来救市,听任索罗斯们肆无忌惮地扫荡市场。无论是香港特区政府资金的入市狙击,还是马来西亚的外汇管制,一概都被攻击为干预市场。对此,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一提起来就恨得咬牙,他说:一天毁了30年。 金融危机十年轮回,从东方游走到了西方。可是,大难临头的美国人却不仅自己没有坚持曾经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所主张的所谓不干预市场的自由市场主义,而且还理直气壮地要求全世界和它一起大动干戈,不惜一切代价地救市。 仅仅用“百年不遇”四个字来解释一个十年前还曾经那么神圣而不可动摇的主义突然又那么义无反顾走向自己的反面,显然并没有什么说服力。唯一有说服力的说明只有“利益”二字。换言之,十年前的金融危机是人家的,事不关己,不妨高高挂起。而十年后的“百年不遇”则是自己的,事不关己,一关己就乱,在利益攸关的紧要关头,谁也不能免俗。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霸道的美元主宰世界的时代正在“无可奈何花落去”,可惜的是,一个贴满了美元标记的自由市场主义虽然正在美元的世界里节节败退却还在人民币的世界里肆无忌惮地指手画脚。西方的欧美各国可以不遗余力的救市,而东方的中国股市却至今还在视救市为大不韪,这是什么逻辑? 自由市场主义虽然曾经被西方资本主义奉为至高无上的金科玉律,但是,它在本质上其实并不是无政府、无国家的代名词。恰恰相反,西方经济学家在研究苏联和东欧的教训中发现,一个国家职能权威和政府职能,如果不能够建立的话,自由市场也不能够很好地发挥作用。200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在其出版的新书《大破解》一书的开头,就借一位颇有公众良知的商人在美国纽约繁华的曼哈顿42街和第六大道的交叉口处竖立的一块巨大“国家债务电子钟”,“呼唤那些政治家和决策者们能够为这个国家担负起责任……”。一场不请自来的金融海啸,即使未必彻底地摧毁得掉自由市场主义,但至少也足以让人极大地动摇了原来曾经是那么固执到近似于宗教的迷信。 中国的某些学者教授在引进西方的自由市场主义的时候,小心翼翼地去头去尾,只留下了“市场”两字。自由市场主义至今也没有成为中国的宗教,但是,这并没有影响它的信徒们在实用主义地引进西方模式尤其是美国模式的时候,不无炫耀地给自己的实用主义主张贴上这样那样自欺欺人的市场化标签。 不过,中国值得庆幸的也许并不是全盘西化,而是在自己的肩膀上扛着自己的脑袋。但是,让人烦恼的问题往往也就发生在这里,不要说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常常分不清“全盘西化”的“市场化”好,还是“注了水”的“市场化”好,就是海归派不免也会犯“二元论”的错误,比如,他们从来不反对政策挤压泡沫和调控市场,但是,一说到救市,则无不一口一个的“不能救,不必救,亦不可救”。 “不能救,不必救,亦不可救”的理由如果只是说中国股市有泡沫,倒也不难理解。但是,说中国经济现在到了非救不可的地步也是受股市泡沫破裂之累,那就太让人费解了。股市现在连新股也发不出去,融资融券也推不起来,岂不是没有泡沫,也不会拖实体经济后腿了么?何至于股市可以“不能救,不必救,亦不可救”,而实体经济却反而不但要救,而且还非得“出手快、出拳重”不可呢? “崩盘才救”无疑是“推翻重来”的翻版。但是,不要说股市推翻了究竟是为了让谁重来是个问题,更重要的是,股市若真的崩了盘,中国经济不也更将一发而不可收拾吗?那又将更符合哪一家子的利益呢?

在这里,我们不能不想起的是1997年亚洲经济危机东南亚被不准救市的教训。时代不同了,当初美国人放的一个屁,如果也曾有人说是香的,那么,放在今天,谁不说臭不可闻?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