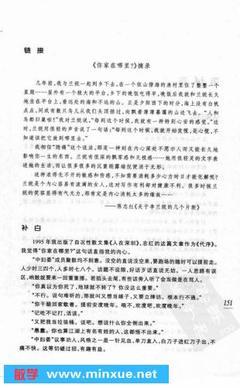环保与企业竞争力的多年对峙最终通过搬迁化解,但大部分高污染、高能耗企业尚不具备首钢的腾挪空间
文|本刊记者 何伊凡
那座冷冰冰的高炉像只失神的独眼,几只麻雀在它眼睑上跳来跳去整理羽毛,张顺勇弯腰,拣起一块碎砖头,远远向麻雀抛去。麻雀盘旋,又落下,其他厂区时常有小火车拉着暗红的铁水跑过,空气灼热,人声嘈杂,实在不是歇脚的好地方。 其他人也不像张顺勇这么清闲,他和麻雀的游戏周而复始。“我和它在一起的时间比老婆还长。”张指着高炉平淡地说,他食指上有段褐色的疤,是钢花的留念。这座4号高炉的寿命超过张的工龄,连续生产了35年零2个月。2008年1月,它和两台烧结机、两座转炉先后停产,按照一个与绿色奥运相关的承诺,首钢将压产400万吨,等于其在北京总产量的一半。 自天安门广场西行17公里,一片管道交错的厂区如同长安街延长线的句点。1919年北洋政府创办的石景山炼铁厂,如今已成北京的工业符号,也是它的环保心结。英国奥委会2007年一直在测试一种面罩,可以让运动员在中国训练时戴上。不管类似担忧在国人眼中何等小题大做,北京仍需采取必要措施净化空气,首钢搬迁就是显示这种决心的强烈信号。 钢铁工业所制造的污染主要包括矿石冶炼、煤炭焦化等流程中产生的粉尘和废气,以及钢渣、焦油渣等固体废弃物,它对水资源的需求也颇为可观。首钢的位置“上风上水”,上世纪60年代,远远就能看到厂区上空一个由黑色、白色、黄色烟雾缠绕成的“锅盖”,地面上的草也挂着一层铁锈,石景山区附近的白庙村,居民都给玻璃贴上厚厚的塑料布,防止粉尘进屋。一个不甚精确的数字是,最严重的时期,首钢在石景山粉尘排放量平均为每年每平方公里34吨。 1964年,经有关部门批准,首钢将钢渣统一倾倒在卢沟桥抗战纪念馆的西北侧。钢渣产生量大约占全部钢产量的10%,随着炼钢能力提升,钢渣山也日渐膨胀,到1991年已绵延1公里,高18米,重达300万吨,卢沟桥上著名的石头狮子,身上麻点越来越多,当地居民认为每天用夹带在风中的钢渣“洗澡”是重要原因,但北京环保局否认了这一说法。 在GDP为王时期,这是容易忽视的代价。上世纪70年代,时任首钢领导的周冠五去日本考察,看到高炉下都有花草,工人带着白手套工作。好胜的周冠五认为首钢应以此为样本,当时很多同事不以为然,认为不可能也无必要。这种想法引起了周心中的不安,他意识到环境污染的压力未来一定会掣肘首钢。 1979年首钢成为国企改革的第一个重大试点,采用利润递增包干,所谓“农业改革看凤阳,工业改革看首钢”,首钢的辉煌由此开始。1989年,其利润年增长率为全球钢铁公司的2.4倍。1992年邓小平视察首钢后,首钢获得了投资立项、外经外贸、融资三方面特权,1994年,其钢产量达到823.7万吨,为全国首位,宝钢与之相比还是个“小弟弟”。 这一时期,首钢开始在山东济宁、广西柳州等地考察,准备异地建厂,或寻求合作,也去了如今的首钢河北曹妃甸基地,当时那里还是一个荒芜的海岛。四处出击的原因一方面是钱包鼓鼓,另一方面在北京的空间压力已经呈现。
异地投资没有下文,而在北京,823.7万吨成为巅峰。周冠五在1995年初离职,时年77岁。自此首钢的产能原地踏步,“要首都还是要首钢”的问题逐渐成为一种呼声,答案自然不言而喻。此后钢铁工业的几轮大发展中,它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对手从身边一个个跃过。为弥补主业竞争力的缺失,首钢惟有大力发展非钢产业。 2001年7月13日那个沸腾的夜晚,首钢的主要领导也彻夜难眠,申奥成功十个小时后,首钢党委召开紧急会,重新研究“十五”期间的环保规划。将首钢的环保问题与奥运会联系起来令他们尴尬,而这个夜晚过后,这个话题将变得无法回避。 实际上,“要首都还是要首钢”一直让首钢焦头烂额,它不希望这是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自周冠五时代就开始大规模绿化,正门前百米如绿色长龙,厂区内有月季园,人工湖中常见野鸭嬉戏。自1995年起,扩产受阻后首钢投入大量资金用于环保,累计21.3亿元,如今设在石景山区的大气污染监测仪,显示的数字并不高于其他区。2007年与2001年相比,二氧化硫、烟尘、粉尘排放总量分别降低了54.6%、45.6%和45.2%。为消化钢渣山,首钢还建成国内第一条钢渣干混砂浆生产线,颇具象征意义的是,所产砂浆大量用于奥运工程。 能否在异地建厂的同时保留北京厂区?是张顺勇等一批老工人曾经的幻想。“新日铁就在东京,人家还是发达国家呢,难道北京就容不下一个首钢?”一位匿名的中层向《中国企业家》发牢骚说,“这一折腾,耗资数百亿啊。” 据说2002年首钢曾在一个报告中作出“实行整体搬迁的方案基本不可行”的结论,搬迁费用过高、影响工业总量和富余职工难以安排是三个原因。但随着奥运临近,整体搬迁已成为宿命,首钢长达90余年的历史中,因为所处的位置,沉沉浮浮,总是离不开“大局”二字。 政府从未向首钢提出过搬迁的正式要求,但对首钢而言不能发展无异于慢性自杀,同时首钢的产品结构以建筑钢材为主,业内戏称为“面条裤腰带”,附加值低,它希望借新项目实现产业升级。“搬迁不是复制,”现任董事长朱继民说,“更不是‘污染搬家’。”首钢仍强调自己是主动迁移,如此不会抹杀其在环保方面多年的苦心经营。 2005年2月,国务院批准了《关于首钢实施搬迁、结构调整和环境治理的方案》,中国钢铁工业史上最大的迁移就此缓缓拉开序幕。首钢在河北迁安已经有一个钢厂,有助于保证其生产衔接。2008年,首钢将按照年产420万吨钢的规模生产,直到2010年停产。今年第三季度每个月最多生产20万吨,主要是为了保证高炉不停工。2008年,因压产首钢直接利润损失将达28亿元人民币。 仅这一次压产,就有8427名职工分流安置,首钢在京的钢铁工人超过3万名,他们中的一部分将转移到曹妃甸,那里大约需要不到1万名工人。张顺勇计划退休,而他的儿子会去曹妃甸,有时他会想象儿子和自己一样,全身包裹,手中紧握着钢钎,世界只剩下面前张牙舞爪的炉火。但实际上儿子的工作只是按动几个电钮,就像20年前周冠五在日本看到的一样,这让他放心而又有些失落。 奥运会期间,钢铁第一大省河北将有42家企业关停,其中大部分为钢铁企业。天津、山西、内蒙古、山东也联动保障北京空气质量,限产或停产高污染企业。在两个月内兑现“绿色”的承诺不困难,但要提升资源利用率,完成节能减排目标却并不容易。国内一种根深蒂固的潜在论调是严格的环保监管政策将破坏企业的竞争力,大部分高污染、高能耗企业尚不具备首钢这样的腾挪空间,它们面临的局面往往是要不消亡,要不就在“圣火”冷却后继续以灰色的方式生存。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