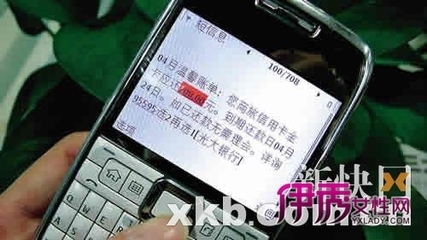作者:■林鹰 一年前,我们有幸经历了史无前例的牛市。一年后,我们同样有幸经历着“百年一遇”的金融风暴。 一年前的8月下旬,当我们把对次贷危机的专题定题为《美国次级债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微妙而深远》时(参见2007年第34期《红周刊》),欧美日澳各地央行多达3000亿美元的救市均告失败,而世界又一次感慨:“谢天谢地,还有中国!”主持人惟一听到的忧虑来自于世界银行研究部研究员邹恒甫:“中国的小股民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不用哭,更不用寻短命……”他的预言旋即遭遇嘲笑,天地良心,那时“黄金十年”梦想灿灿,经济前景生机勃勃,A股市场东方不败…… 如今回头再看,“深远”则深远矣,“微妙”却已成全球骇浪!而当时专栏作者王强在专题下《危机的警示》一文中的两个判断被逐一验证: 高风险高收益类债券衍生品市场面临的挑战或许才刚刚开始; 美国次级债危机的直接影响,主要在于投资该类债券的中资机构。如果传闻属实,则遭受损失是必然的。这些损失必然影响其公司利润,从而影响股票价格。人为的托市行为特别是社论托市的行为,只会使缺乏判断力的投资者在谎言被揭穿后摔得更惨。

单就中国的经济和市场层面而言,从去年冀望“一枝独秀”到如今乞求“独善其身”,从生机勃勃的制造业到频频破产的中小企业,从流动性过剩到“缺钱缺德”,这一切发生得如白驹过隙。我们无法找到“这世界到底怎么啦”的终极答案,却不妨回头想想,为什么会出现郎咸平所说的“我们手气不好什么都碰到了”的局面? 主持人无意去探讨救市,因为全世界有市场的地方都在这么做,我们这么做了,对于一度赤膊相搏的救市与不救市两派来说,也许都是“你无须讶异,更无须惊喜,转瞬间消失了踪影”。与周五注定被讨论得热火朝天的“单边收印花税”和“汇金入市”两大利好相比,笔者更关注的是周初央行的“结构性双降”。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周其仁教授近日撰文说,“中国有条件争取独善其身。我们无须重复令全世界都羡慕的老生常谈——中国拥有巨大的内需潜力”,“真正困难的问题只有一个:究竟怎样才能把中国的内需潜力释放出来”。 如周教授所说,拉动内需是“老生常谈”——因为“老”是“生”拉不动,所以只能“常谈”。在好日子的时候都拉不动的东西,在关门的关门、下岗的下岗、套牢的套牢之关节,“究竟怎样才能”? 今年6月,邹恒甫接受《红周刊》专访时留下的两句话,让我思索良久,一是“我认为现在中国的通货膨胀非常好”,二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大有可为”(参见26期“高端视野”)。对于前者,我的理解是:通胀不是价格问题,而是货币问题,别再继续掩耳盗铃让粮食去承担通胀的罪名;而对于后者,中小企业现状以及与此同时的“经济学家信心指数跌至2004年来最低点”,大约可以从相反的角度说明一切。要解决这一切,“结构性双降”做得到吗? 在文章的开头用了两个“有幸”,后一个注定要挨骂。然而,在作为股民的一生中,能够遇上两起如此极端的经历,不能不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对于个人而言,本期“主题研究”《从百年美股“十熊”看A股18年历次底部的构筑》作者迈克·吴有一个建议:暴跌就是新领导股脱颖而出的观察期,历史证明所有的大飙股都是在大熊市中产生的。对于市场而言,贺宛男曾提出的“暴跌市道也许正是解决大小非的好时机”(参见35期“周末茶坊”)难不成会一语成真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