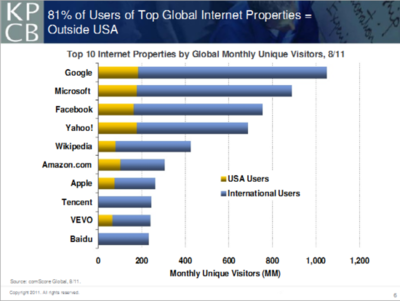一定要做跨国公司的低成本外包商吗?新松从行业幸存者到中国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制造商的成长路径
文岳淼
如果要寻找世界工厂向高级制造跃迁的典型一幕,你不妨到位于沈阳浑南工业区的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公司的车间里看一看。在这里,来自全球的元器件被柔性化地组装起来,成为可下沉于数千米的海底进行作业的机器人,或者在真空环境下精度可切割细胞的电子机械手。这个现代化的工业机器人装配车间就像一个被驯化的机器人城市,它们都被关在铁笼里,口吐火花。装配线在地面和头顶上编织成纵横交错、密密麻麻的图案,空气里漂荡着一丝金属焊烙后的气味。所有工人都戴着颜色鲜艳的头盔,身穿制式统一的蓝色工装,但在多数情况下,他们只做些“辅助工作”:记录数据,或在出问题时向系统发警报。真正的主角?是机器人,它们体积庞大,颜色橘黄,各部位有关节相连,看上去就像科幻故事里那些伸着脖子四处觅食的猛禽。 “这是不是就像电影《终结者》里面的场景一样?”曲道奎说。47岁的曲是新松机器人公司总裁,在此之前,他是一位成绩斐然的资深科学家,拥有数项国家级科研最高荣誉,至今仍是沈阳自动化所机器人技术研究所的博士生导师,带着8名研究生,而新松则是他在2000年力主发起的以沈阳自动化研究所为投资主体的股份制企业。这家公司以“中国机器人之父”——曾经担任国家“863”计划自动化领域首席科学家的蒋新松院士的名字命名。目前,新松已形成工业机器人技术及装备、自动化成套技术装备、仓储物流自动化技术及装备等制造能力,占据着中国大约10%的市场份额,去年销售收入为6亿元,而新签合同额则增长68%,利润几乎翻了一番。 这家成立仅8年的公司一心要为中国和全球提供最高水准和性价比的产品,打败在机器人领域最棒的德国制造和日本制造。不可能吗?曲道奎有自己的底牌,“做同样东西,我们只是国外1/5到1/10的费用。”他告诉《环球企业家》。 幸存者 曲道奎的办公室就在这座巨大的机器人世界的“体内”,站在窗边时,他可以直视那些上上下下、昼夜不停的电梯,5个飞机棚大小的工作室可容纳500名设计师及工作人员。百步之外,是新松刚刚启用不久的技术中心,那里有一个4层高的中庭,可以一览无余地看到楼下的试验车间。曲要求所有出厂的机器人都要在这个车间内做现实工作场景的作业测试,让客户缩短设备调试时间。在车间墙壁上一排排独立的公告栏里,除了图表还是图表,从作业说明书到对某一特种螺丝的质量投诉次数,都如财务报表一样被清楚列明。 这种热火朝天的工作场景其实得来相当不易。早在1980年代末,国内曾经有上百家机器人研究机构从事相关领域研究,但是到目前,专业从事机器人开发的企业只有不到50家。国家曾经将机器人列入“六五”规划,但在此后的20多年间却没有给予持续有力的研发支持,多数机器人方案在研究所就胎死腹中。目前,中国市场上机器人保有量为1.73万台左右,只占全球总量的0.56%,而完全国产的机器人只占30%左右,其余均依赖进口。即使如此,这依然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20年前,机器人几乎百分之百依赖进口。 “我们是这个行业为数不多的幸存者。”曲道奎说。曲曾于1990年代在德国萨尔大学做访问学者,从事机器人控制、运动规则和语言系统方面的研究,对机器人在德国工业领域的成熟应用叹为观止。“国外以企业为研发单元,研发报告出来,仅仅是实际操作运动的开始;而我们则是大学和科研机构,评审会变成了‘送终会’。”曲说。缺乏活力的中国科研机制束缚了科学家的创造性,回国后,曲担任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机器人技术研究开发部部长,在之后6年间,他力求打破这一点:不要一味苦思冥想,而要动手去做。 曲喜欢将各式各样、纷繁芜杂的算法和概念游戏变成现实。他热情高涨地翻阅各种资料,来为这些概念寻找理论依据和现实出口——机器人不是实验室的摆设,它需要走到工厂里面去。满怀激情的曲很快发现一个尴尬的现实:他面临的对手都是瑞士的ABB、德国的KUKA、日本的FANUC、意大利的COMAU、日本的YASKAWA这样的世界级企业,用户购买时主要看重机器人实际运用中能否解决问题,因而依靠价格进行竞争无法压制对手,而此前厂商对国产机器人的应用普遍没有信心。 但这些都并未阻挡新松的扩张,曲放下学者的架子说服对方相信自己,但中国企业间常见的拖欠货款现象又常常使得每一笔合同最终变成另一场噩梦的开始,他不得不四处要账。“这时常让我感到很难堪。”曲说。 但无论如何,他需要走出第一步。1992年,曲有了一个机会。当时华晨金杯遇到一个难题,此前金杯试图用简易机械装置和人力配合的方法为汽车安装发动机,但因为缺少自动跟踪功能,每台安装要耗费至少5分钟时间;而且只要有一台停车,整个生产线就必须完全停下来。 曲试图改变这一切。他开始考虑用柔性的生产线来替代原有的生产线,利用AGV(智能化物流搬运机器人)激光自动导引车将流水线上重达400公斤的发动机迅速而轻松地抬起,然后进行钉螺栓等安装工作,整个过程只有100秒钟。“初试成功给了我们极大的信心。”曲说。 更多的时候,他不得不用数据对抗傲慢和偏见。去年末,新松装检自动化事业部总监刘长勇收到了一封来自上海三电贝洱汽车空调有限公司的表扬信。后者生产的汽车空调压缩机已逾1000万台,在中国汽车空调市场拥有60%以上的市场份额,其压缩机生产线多数精度都要求在微米级,而此前使用的自动化机器人生产线都来自国外,对国内生产设备充满了质疑。刘长勇反复争取,最后被允许以几台工作站作测试。三电贝洱此后用业内“双R法”对设备进行了严格检验,依照以往经验,低于20%就可以使用,低于10%则意味着非常优秀。而当时这家公司使用的进口机器人大部分比分都在20%,而新松的测试结果均低于10%,有些设备甚至达到1%。“结果让他们感到非常震惊。”刘说。最后新松赢得了所有的订单。 曲是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的信奉者,他确信既然在数量级上与国外巨头处于劣势,要想赢得胜利,“必须在决定性的地点把尽可能多的军队投入战斗”。曲将400人的研发力量聚焦在汽车以及相关零部件装配领域,之后再伺机扩张。事实上,汽车行业是机器人运用最为频密的行业。在成熟的汽车制造行业,一条年产10-20万辆的汽车生产线要用到机器人600台,而当时中国汽车行业所用的机器人数量微乎其微。曲随即将业务领域锁定在移动性机器人、焊接机器人和装配搬运机器人的研发上。 曲是各大汽车公司的常客,喜欢出没于机器轰鸣的厂房,他甚至还乐于帮忙,为客户解决国外机器人设备运行过程中的种种问题。1990年代中期,他在一汽大众的冲压生产线看到一片愁容的工人们,原来是机器人出了问题,但维修人员还在海外没有到位。“让我们试试。”曲说,在一片讶异的眼光中,曲很快修好了机器人。“我们就是这样一点点帮助别人来积累自己的信用。”曲说。一年后,曲终于打动了对方,将国内第一条自主研发的机器人冲压自动化线卖给以苛刻著称的德国人。 曲也由此逐渐意识到,由于国内产业工人素质偏低,其对机器人的使用和操作并不科学规范,导致故障频繁,而国际厂商的售后响应服务相对滞缓。“我开始意识到本土化快速服务的重要性,这是我们对抗跨国公司的利器。”曲说。他开始在全国各地机器人使用频密的制造业城市中建立完善的售后支持体系,向客户保证24小时解决问题。 全球对抗 曲道奎敏感地意识到欧洲机器人厂商的优势多数集中在整合全球最好的资源以提供整套设备和工业流水线,而日本则集中于机械手、电子元器件等方面的研究,更习惯闭门造车。曲更倾向于欧洲人的做法——和其他中国制造的成长路径不同,他从一开始就没有选择零部件低廉制造的道路,而是集中于机器人的整个控制器和算法的研究以及定制打包服务的能力,然后通过全球招标采购来获得价格已相当透明的元器件。 曲以出手快和市场反应敏捷著称,现在他把未来赌在狂野设计和热门技术上。他的下一个创想是将方兴未艾的面向家庭用户的服务机器人尽快完全市场化。在曲的办公室楼下就有这么一台持续进化到第三代的样机。设想一下,一个身上装满了感应器和摄像机的人形机器人奔跑起来是什么样?“起初它只会说几句简单的对话,我们花了三年的时间让它彻底实现人机对话。”新松研究院院长徐方指着绿色球场上一个笨拙地奔向足球的淡蓝色人形机器人说。配备了摄像机、红外线传感器和无线网卡的这台机器人每秒能处理数百张图片,从而对周围的状况了如指掌,它可以随时和人自由交谈,甚至还会清洁房屋,如有不明身份者闯入则给主人发短信。 “这台机器人的定价不到1万元。”徐对这项成就感到骄傲。但是曲道奎则抱怨说,他不喜欢这款机器人的外观,“机器人的表情还太呆板。你还得加把劲”。这一切让徐感到很刺激,他时常还会接到千奇百怪的操作难题,比如如何让与信用卡相差无几的超薄LCD板在真空状态下搬运装箱,或者将热烫成型的天然橡胶块装箱运输。 徐没有单独的办公室,他和下属一样坐在格子间里,周围不停有年轻人走来走去,打电话、呼喊对方的名字,墙壁上贴着工作进程表,公司纪律与内部通知,还有各种英文单词和短句,一场学习英语的运动正在公司内部兴起。徐的办公桌上杂乱无章地堆放着各式各样的图纸和报告。他还记得,当他1995年加盟新松担任软件开发设计师时,这里横七竖八摆放着几台被拆卸分解的机器人,还有散乱一地的线路、电子板和螺钉。
尽管在外界看来,徐的工作很“酷”,但事实上这相当枯燥和熬人。徐是中国机器人工业经济勃兴的见证者,比如弧焊机器人,中国从1990年就开始研发,当时控制器实现了国产,而机械本体采购则来自国外;5年之后,控制器和机械本体都实现了国产化。10年后有了样机,然而从实验室走到试制车间又耗费了整整两年时间。徐为此耗费了他人生中最宝贵的青春,最终得到的试验成果是,焊接弧度精度达到0.08毫米,平均无故障时间为5000个小时,价格只有30万人民币,仅仅是之前国外同行售价的1/5。 曲道奎刻意提倡自由交流的氛围,但他本人却没有过多的交流爱好,也不像其他企业家一样喜欢去工厂溜达。曲的书架上堆砌着种类繁多的专业书籍,多数是英文、德文和日文。“不过,我不看什么管理书,废话太多了,我也不崇拜任何明星CEO。”曲说。他崇尚极度放权,在日常的管理中则充当仲裁者和问题终结者的角色。他甚至极少看财务报表,将这类工作交给专业的会计师打理;他也不太过问销售,即使是大规模采购的谈判,他也极少参与。 曲真正热衷的是:挑选人并在合适时机将他放在合适的位置上,与世界各地的同行们交流未来趋势,解决下属无法解决的技术性问题。看上去,曲更像是一个企业家和科学家的混合体,而后者成分更多些。坦言自己经常“不理政事”的曲现在唯一担心的是这家崭露头角的公司会不会出现一种危险的闭关自守倾向——这可能威胁到该公司密切联系顾客和追求创新的能力。 “所有的眼泪、哀叹都将被竞争的咆哮声所淹没。我们应该各取所长,同时规避各类风险。”曲说。他的做法是邀请国内外最优秀的合作伙伴来新松交流研发心得和体验,并将新松全球最核心的供应商压缩到不到30家,通过利益捆绑来驱动它们,并发誓不与那些在信誉方面声名狼藉的公司合作。 新松的发展也让王宏玉有了骄傲感。“我们已经能够在全球某些领域内引导消费了。”这位新松物流与仓储自动化事业部的总经理告诉《环球企业家》。去年,他领导的部门赢得了公司1/3的销售额,并击败国际对手进入通用汽车全球核心供应商的名单。此前,新松就进入通用汽车在中国上海和柳州的工厂,通用汽车全球设备采购部门在例行检查中发现,新松AGV运行记录平均水平大大超出了国外同行,其生产和交货响应周期平均只有4个月,国外则至少需要6-8个月,而且价格相当。通用汽车此后向全球AGV公司发出标书,新松最终赢得胜利,获得70余台总价值在7000多万元人民币的采购订单。 “他们都感到很意外,但事实上,我们在这个领域已经在国内保持了10多年的垄断优势。”曲道奎说。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