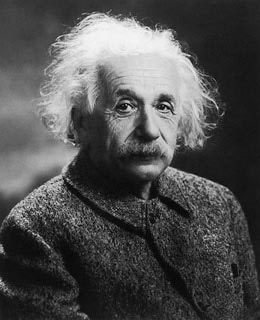任何时代的人都需要文学,需要他们信任的文学,而不主要是通过文学来欣赏机心。
文/张新颖
迟子建新写了一个中篇,叫《草原》。看到这个名字,我就喜欢。这是因为,这个名字暗示着名字之下的作品,最终指向比这个作品大的生活世界。 这个名字,和《边城》,和《呼兰河传》,是一类的。我倒并不是暗示迟子建有什么野心,而要说,这样的名字,隐含着一个作家的小说世界的性质,还隐含着一个作家的小说世界和一个更广阔的生活世界之间的关系。 文学作品,就其内在要求而言,应该具有自身的统一性,它自身就应该构成一个完整的世界;然而,从另外一个层次而言,任何文学作品自身都不是完整的,它植根于它从中诞生的更大的世界。这样一来,对于完整的理解,会产生两种倾向:西方的文学传统倾向于把要表现的内容绝对局限于作品里,作品自身就是一个完满的世界;中国的文学传统则倾向于强调作品和生活世界之间的延续、转化、声息相通,相对于作品的完整性而言,还存在着一个更大更完整的世界。
当代中国的文学创作和观念,可以见到这两种倾向的表现。这个不同,区分出两种类型的作家。一类追求和强调作品内部的整一性,这也就意味着,如果一部作品自身就是完整的,那么它同时也是封闭的,它是自足的,不需要与它之外的世界形成关系。这种类型的作家通常相信个人的独创性,相信叙述和虚构的力量,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可以通过个人独特的创造性,通过叙述和虚构,来创造出一个独立的、纯粹的文学世界。另外一种类型的作家则要谦卑一些,他们相信文学有其出处,这个出处并不仅仅是个人的创造性,也并不仅仅是由叙述和虚构构造而成,这个出处比他们的作品更大也更完整,我们或者可以把这个出处叫做生活世界。他们的作品和这个生活世界之间是相通的,这也就意味着,作品不是封闭式的完整,甚至可以说,相对于生活世界来说,作品永远也不可能是绝对自足式的完整的。 迟子建的文学,正像沈从文、萧红的文学一样,是有出处的文学。从完全自足的艺术品的意义上来说,常常会觉得他们的一些作品是不够精致的,不够完整的,那可能恰恰是因为他们的文学带着其出处的鲜明痕迹和独特气息。把原生的痕迹和气息去除干净,割断与它从中产生出来的生活世界的紧密联系,那就成了摆在博物馆里的艺术品。他们的文学,不是这样的博物馆里的纯粹的艺术品。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他们的一个个作品,可以看成是一块块矿石,粗糙,但是有质地,特别是,一块又一块的矿石之间都可以联系起来,而且共同指向一座富矿,它们的出处。 有出处,才让人信任。这就又谈到信任的问题。似乎我们现在几乎不用信任这样的词来谈论作家作品。 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怎么叙述越来越成为非常多的小说家用力的方向。叙述的自觉当然比叙述的蒙昧好,叙述当然是小说的一个基本问题,无论如何讲究都是应该的;但随之而来的,则是如何叙述的机心,这样那样的机心,在二十多年来的当代小说中随处可见。 一有机心,即无信任。 首先是作家不相信他要写的那个东西本身即是好东西,他要加入个人的机心(个人的创造性之类)才能够使它变为好东西。也就是说,不信任感一开始就存在于写作的内部,存在于写作的过程中。接下来,读者在阅读作品的时候,自觉或者无意识地感受到机心的存在,就产生出隔阂。读者看着作者在那里耍花枪,耍得高明,叫一声好,也就如此而已,信任感是没有的。 作者从他个人的创造性出发,要设计他的叙述,要设计他要叙述的东西,要设计他的叙述有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反应和效果,在这个过程中,读者也被设计了。被设计的读者当然不会信任设计他的作家和作品。 任何时代的人都需要文学,需要他们信任的文学,而不主要是通过文学来欣赏机心。 要使读者信任,首先作者要信任。信任什么?在沈从文、萧红、迟子建这样的作家那里,是信任他们的文学从中产生的广阔的生活世界。他们的自信来自他们相信,相信那个大于他们个人——大于个人的创造性、大于叙述的设计——的生活世界。 他们的文学对生活世界有一种谦逊的态度。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