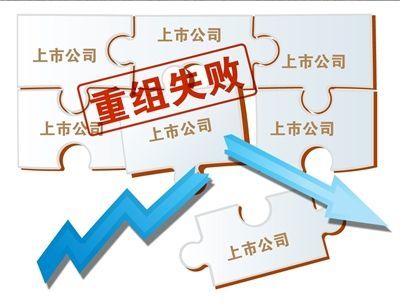经过20多年,改革又回到了出发的时候面对的问题。也许应该再来一次莫干山会议,展开一次关于价格问题的大讨论。
撰稿·汪伟(记者)
进入2008年,张军一直在写书。作为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写作的主题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书中包括了许多“经济学家自己的故事”。这些故事里,最有趣的是“莫干山会议”和“巴山轮会议”。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让包括现任北大副校长张维迎在内一批年轻人崭露头角,20年后,他们几乎都成了中国经济学界的中坚。那一次他们讨论的主题就是价格改革。 张军想给过去30年历史一个经济学的解释。很大一部分就是对价格的解释。张军没有忘记,1980年代的价格改革付出了高昂的学费。1988年8月19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一条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并原则通过《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该《方案》提出,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 消息一出,商店里的货物被抢购一空。银行了发生挤兑。80年代结束的时候,价格改革引发的通货膨胀最终演变成一场社会和政治危机。 回顾往昔,他从来没有忘记这个故事。 价格是80年代的中心 《新民周刊》:80年代的改革似乎可以描述成一场以价格体制改革为中心的改革。 张军:价格问题已经有15年没有很好地讨论。80年代的改革是以价格为中心的,90年代中期以后,从政策制定的角度看,价格改革问题似乎不再重要了。 刚开始改革的时候,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最难的就是价格改革。计划控制下的价格,能源、矿产和农产品的价格都压得很低,这等于是让这些部门来补贴重工业。这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个特征,就是用这些手段转移大量剩余到重工业部门。要改革计划经济,最重要的就是要把这之间的价格理顺。 1980年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为拉美、东欧和苏联进行经济改革提供建议的时候,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价格自由化,而且越快越好,一次到位,不要拖得很久。这是“华盛顿共识”的重要内容。但中国的价格怎么改革,国内有严重的分歧。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上,主张一步到位的人几乎没有。这就是中国文化,没有人认为应该一步到位,没有人敢冒这个风险,而且,政府显然也没有这个打算。最后形成的方案叫做“调放结合”。一部分商品价格逐步调整,另外一些关系不大的商品,计划控制不那么严重的物资,价格基本上就放开。这个方案最后通过张劲夫向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汇报,最后坚定了中央政府对价格体制改革模式的选择,即渐进的、多步走、“调放结合”的方案。到了1985年到1986年,价格改革的效应开始显现出来了。能源、资源的价格基本上没有动,一般商品的价格很快就开放了。 《新民周刊》:双轨制是会上提出来的吗? 张军:所谓的双轨制,也就是计划内还是原来的比较低的计划价格,但是鼓励生产企业多生产,超出配额的部分,可以卖比较高的价格。价格双轨制最早反而是在石油和煤炭行业里形成的。1981年,允许油田超过计划部分的原油可以按照国际市场的价格出口。这个政策很快使得出口原油的同一油田出现了两种价格。1983年,国家用允许出口原油“以出顶进”,在国内加工生产成品油,按国际市场价格在国内销售。这就又出现了成品油的双重价格。
煤炭和原油这两个部门的做法启发了学者和政府,之后开始在其他部门推行。到了1986年,双轨制的弊端显现出来了。由于两种价格差别很大,有人就把通过计划价格买来的商品以市场价卖出,倒买倒卖,赚取差价。那些计划官员掌握了审批权,套利者为此就向他们行贿。执行双轨制作为价格改革的方案,时间其实不长。由于腐败猖獗,很多人都说,再实施下去就要葬送改革。中央政府注意到这个问题,开始加紧研究并轨。《新民周刊》:价格改革最主要的风险在哪里? 张军:通货膨胀。1988年,中央政府提出要“价格闯关”,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邓小平那时候有一些名言,比如说,“理顺物价,改革才能加快步伐”,“物价改革非搞不可,要迎着风险、迎着困难上”,“长痛不如短痛”等等。价格改革的确是有风险的。在一个商品短缺的时代,放开价格引起了席卷全国的挤兑和抢购风潮,影响持续到1989年,一切改革都停了下来。 再来一次“莫干山会议” 《新民周刊》:所以说,价格改革在80年代并没有真正解决? 张军:没有。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随着中国经济逐渐恢复增长,价格改革的呼声再次出现了。大家都已经认识到双轨制下寻租的可怕,因此双轨制不能再持续下去。到了1993年,商品短缺的局面已经大大改善,价格改革以放为主,放了不行又收,收了再放,尽管也导致了通货膨胀,但并没有引起1988年那样严重的社会后果,大部分商品从此实现了市场定价。但能源价格仍没有放开,从那时遗留下来,一直到今天仍然困扰着中国经济。 《新民周刊》:为什么保留了能源没有改? 张军:怕通胀。能源在上游,价格一放,下游全部涨上去了,担心社会承受不了。 《新民周刊》:今天能源价格改不动,还是因为这个担心? 张军:改革有自己的路径依赖。要承认这个现实。今天的宏观经济状况很大程度上是由能源价格决定的。如果能源价格低,能源密集型行业就会发展,如果我们现在完全放开,行不行?下游的产业受不受得了? 不过,今天能源的价格问题和1980年代有很大的不同,“调”的效率要比以前高。从1990年代之后,国内调整能源价格有了风向标,那就是国际市场的价格。我怎么才能知道油价和煤价需要上调呢?如果国内市场的价格低于国际市场的价格,企业就会倾向于出口,反之亦然。所以调价就有了自己的参照物。这种模式就一直延续到现在。能源价格没有放开,而是根据国际市场的价格来进行调整。 《新民周刊》:如果我们在国际油价较低的时候对能源价格进行更彻底改革,就不会有今天这样艰难的局面,我们因此丧失了能源价格改革的最佳时机。 张军:能源对宏观经济来说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正是因为是全局性的,完全放开意味着全局性的利益再分配。在短期内进行这样规模的分配调整,要触动这么多方面的利益,我想不是中国改革的传统,也是政府不愿意看到的。 既然我们已经失去了最好的时机,现在只能考虑次优选择,最好的办法还是主动调。不是一次到位,而是长期、多次调整。调整间隔多久,幅度多大,看当时的情况来决定。这是次优的办法。 《新民周刊》:用吴敬琏先生的话说,由于能源价格管制,人为扭曲了市场价格机制,造就了一批高能耗、高物耗和高污染的“三高”企业。转变经济增长形式已经成了当务之急。但也有人担心,油价涨上去,和国际接轨了,中国的企业会不会大规模倒闭,就业和农民增收的问题怎么办?这个两难局面成了能源价格改革的最大障碍。但长远看来,调整的成本会不会越来越高,甚至和短期内彻底放开相比得不偿失? 张军:价格改革往往要面对这样的两难,没有更好的办法。很多国家就是在价格问题上葬送了自己的经济。因为价格没有改好,有的地方出现百分之几万的通胀,最后经济就完蛋了。80年代中国比较谨慎,集中了那么多人的智慧,总算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新民周刊》:价格还是中国改革的中心的问题吗? 张军:经过20多年,改革又回到了出发的时候面对的问题。我们今天谈经济增长方式转型、谈环境保护、谈通货膨胀等等,其实背后都是一个利益的机制,这个利益机制的中心就是价格。能改的已经改了,剩下的都是难题。回顾一下中国改革的方式,不是一步到位,而是渐进的、实验的、多步走的,有一系列的优点,但是留下一个难题,包括土地的价格、利率也就是货币的价格,都没有解决。也许应该再来一次莫干山会议,展开一次价格问题的大讨论,集思广益。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