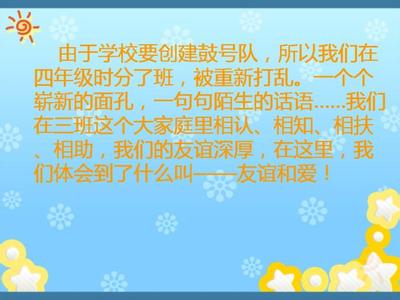系列专题:《让顾客钟情一生的服务体验:欢迎光临》
在佩斯卡工作了8个月,并在新的"熨斗区"建立了自己的午饭常客圈,我决定走出厨房的大门,看看前方的路将引领我往何处走。我开始利用手头的各种资源,其中有我在罗马拉图威玛的乔万尼家族、在纽约的烹饪老师安德烈·阿布拉莫夫,还有父亲,然后在接下来的三个半月到意大利和法国学习厨艺。 这些计划最终提醒我和奥德丽要采取行动了。听说我要离开佩斯卡时,她脱口而出:"什么?!"尽管当时我们俩根本没约会过,但其实我们正在默默地、坚定而含蓄地恋爱着。我们之间的感情别人早就知道了,只有我俩之间没有正式表白过。"我觉得离开前我们需要一起到外面吃顿饭。"我说。离开佩斯卡前,我们一起出去了,约会的安排非常紧凑,这预示了我们结婚后的生活风格--我们有太多事想一起做,只恨时间不够。 我们先去艾冈金大饭店喝一杯,然后去百老汇的布鲁克斯·阿金森剧院看《糊涂戏班》,还没等谢幕就乘出租车到翠贝卡区的Odeon吃晚饭(当时Odeon可能是运河街以南气氛最活跃、饭菜最可口的夜宵餐厅),接着散步到Le Zinc喝了餐后饮品,之后一口气走到"西村"(West Village,即Greenwich Village,格林尼治村),在另外一个最钟爱的夜宵店继续喝,继续聊。随后又散步到22街她的公寓,就在佩斯卡的马路对面。在她公寓中我们一起听她录制的百老汇歌曲的磁带,一直聊到凌晨4点。这时我才起身打车离开市中心回到自己的住所,个把小时后就得到餐馆里上班了。我美滋滋地睡了一觉,醒来还不忘给奥德丽写了一张"谢意卡"(母亲所教的终于有了用武之地),等她早上迟一些醒来时,就在门下发现了卡片。 在佩斯卡我学到了宝贵的经验,学到了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老板和高级管理层对餐馆的财务要高度保密,而我们这些干活的人对预算没有什么概念,更不会计算食物、饮料和人工的费用,只能猜测餐馆是赢利的--猜得也许对也许不对。而且老板经营饭店与其说是非常专业不如说非常感情化,他们的情绪能反映出我们当天工作的表现。老板经常就在自己的餐馆里吃饭待客,而这些饭菜从不收钱,也不记账,这些人也没有给服务生小费。有些服务生是管理层的"红人儿",有些不是。到这里面试的人,在开始谈话之前往往先被上上下下打量一番,我来佩斯卡面试时就是这种遭遇。想想自己偏爱穿袋鼠鞋和灯芯绒裤子竟然也能被录用,真的很让我惊讶。我就像一块海绵,眼睛里充满好奇,什么细节都能吸引我。现在该离开了,该从新的角度认识经营餐馆的良方妙计了。

1984年的最后三个多月,我完全沉浸在意式和法式的烹饪生活中,大部分时间做实习生或主厨的学徒。其实就是做一些没有人愿意做的厨房杂事,因此就不用担心自己的稚嫩厨艺会给大家带来麻烦。在罗马,我与拉图威玛的乔万尼家族相处,学习他们宝贵的烹饪秘诀。当时26岁的我利用一切空闲时间吃遍"永恒之城"(指罗马),以及佛罗伦萨、博洛尼亚、热那亚、皮埃蒙和撒丁尼亚,那简直是天堂的日子。我的两本"圣经"是维克托·哈赞的有开创意义的《意大利美酒》及蓝皮的口袋书《美国人的意大利餐馆指南》。 早上,我在佛罗伦萨的食品集市中央市场或博洛尼亚的"厨房专家"塔布里尼(Tamburini)里闲逛,摸摸新鲜的蔬菜,闻闻香甜的水果,看看油盐酱醋,瞅瞅奇怪的海鲜,对切法非凡的肉块发发感叹,嗅嗅野蘑菇,尝尝萨拉米蒜肠、腌肉和奶酪。弟弟汤米跟我一起待了两星期--作为奋斗之行的伙伴、同志,但主要还是为我多添了一张嘴和一个胃。我们睡便宜的旅馆,因为我发誓,要将有限的预算花在肚子上,而不是枕头上。每到一处我都仔细研究人家的菜单,分析餐馆的设计风格。我习惯把这些潦草地记到日志里,分析出使每个饮食店或餐馆有独特魅力的元素。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