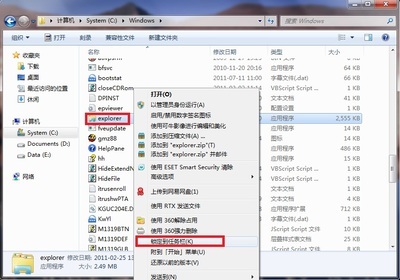在世界工商文明史上,中国无疑是最早慧的国家之一。中国人是一个善于经商——而且是特别善于并乐于经商的民族。在汉代,哲学家王符就说自己所处的时代,从事工商业者十倍于农民,商业流通之盛达到“牛马车舆,填塞道路”的程度。明清以降,“儒贾合流”,“五家之堡必有肆,十家之村必有贾,三十家之城必有商”,甚至连知识精英也不再耻于言商。
千年的“高水平停滞”
从经济要素上分析,中国有发展工商经济的无数优越条件。早在唐宋时期,就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群;宋代水稻和明代棉花的普及造成了人口的大爆炸,中国是第一个人口过亿的国家,庞大的内需市场为工商生产和流通创造了得天独厚的环境。中国还在工商制度创新上拥有很多世界纪录,元代出现了世界上第一张纸币,宋代出现了第一批合股公司和职业经理人阶层,清初则出现了粮食期货贸易。
无比悲哀的是,如此早慧而发达的工商经济,却保持了长达千年的“高水平停滞”。当世界进入到工业革命时期之后,它竟远远落后,受各国欺凌,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东亚病夫”。更让人困惑的是,在全球经济规模第一的国度里,从事工商业的商人阶层却成了一个被妖魔化、边缘化的族群。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极其低下,自《史记》之后,正史之中几乎没有完整的记录。以工商业最为繁华的宋代为例,有名有姓的商人寥寥无几,史书上,连妓女的名字都远远多过商人。在清代,山西商帮控制了中国的盐业、边贸和金融业,其财富总和相当于中央财政收入的两倍,可是在《清史稿》536卷中,被记录在案的晋商仅一人而已。商人阶层的懦弱和缺乏自主精神,更是让人印象深刻。
1932年就到了北平城的美国学者费正清,一生以中国为研究对象,在《中国与美国》一书中,他充满困惑地写道:“一个西方人对于全部中国历史所要问的最迫切的问题之一是,中国商人阶级为什么不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而建立一支工业的或经营企业的独立力量?”为了更形象地描述看到的景象,费正清用了捕鼠的比喻:“中国商人具有一种与西方企业家完全不同的想法:中国的传统不是制造一个更好的捕鼠机,而是从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权。”
实际上,费正清的这个比喻,恰好戳住我们要讨论的要害,那就是在中国两千年的历史上,中国商人参政议政的目标从未改变过——他们依附政府,只是乞求取得经营特权,而从不企图改变或建立一套利于工商、利于自身地位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以商致富,以宦贵之”,这是中国商人深信不疑的保全之道,他们的终极目标,就是把自己变成政府的一分子,从体制外的“乞讨者”转变为体制内的“拥有者”。
从这个角度,历史上的中国商人也从未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参政议政”,确切地说,他们只是“谋政”,抑或“谋权”——追逐特权,是流淌在中国商人血液里永恒的基因。
政商关系的四个困局
国学家钱穆曾提出,中国两千年历史中最重要的关键词有两个,一是“集权”——“中央政府有逐步集权的倾向”,二是“抑商”——“中国传统政治上节制资本的政策,从汉到清,都沿袭着”。
在集权与抑商的背后,是一个无比强悍的政治权力制度安排——高度专制、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中国从公元前7世纪开始,以“管仲变法”为标志,开始探索国家积极干预产业经济的试验,此后多有演进,到“商鞅变法”为极致,并奠定秦始皇灭六国建立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基础。国有资本对国民经济的高度控制,成为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帝国得以维持的根基。
在高度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下,中国的这一部企业史,归根到底是一部政商博弈史。当政府为了政权稳定,全面控制了重要的生产资料之后,它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经济组织,它必然有自己的利益需求,必然会制度性地压抑民间工商业。由此,出现了四个非常具备中国特色的“经典困境”。
其一,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楚河汉界”,前者垄断上游的资源型产业,后者则控制中下游的消费生产领域,中国的市场经济出现“只有底层,没有顶层”的奇特景象。
其二,政府与民间没有形成对等的契约关系,民间资本的积累缺乏制度性保障。在皇权制度及其法权体系中,人民的财产合法性建立在“皇恩浩荡”的前提之下,因此,政权对人民财产的剥夺带有不容置疑的正当性。
其三,权贵资本横行,寻租现象历代不绝,
财富向权力、资源和土地猛烈地聚集。社会资产不是在生产领域积累放大,而是在流通领域内反复地重新分配,技术革命几无发生的土壤。
其四,如果出现强烈的恐惧心理和财富幻灭感,产业资本从生产型向消费型转移,经济成长从而失去创新动力。

政府与工商阶层的对立、紧张关系,贯穿于整整两千年的帝国时期,已俨然成为一种类似胎记般的传统,那种不对等的、没有契约精神的原则似乎从来没有被尖锐地打破过,对工商业的压抑及异化是一种顽强的中国式传统。在传统的重压下,中国商人本能地把自己弱化了,失去了“参政议政”的兴趣和能力,“附政”成为最重要的生存手段。
平等是议政之前提
叙述至此,我们就可以回答“费正清之问”了——为什么中国的商人不是去制造捕鼠机,而是去追求捕鼠的特权?答案其实是明显的:如果没有获得捕鼠的特权,再高效的捕鼠机都无法工作。而特权在谁之手?政府也。
费正清在研究中也给出了类似的答案:“绅士家庭最好的保障并不仅仅在于依靠占有土地,而是依靠土地所有权和官吏特权的联合。家庭财产并不是一种保障。”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王毅在《中国皇权制度研究》中给出同样的结论:“托庇于官僚政治之下,是制度环境对于中国商人生存出路的根本性规定。”
更让商人阶层痛苦的是,在历史的爆裂点上,他们的处境往往是两难的:集权体制从根本上侵害他们的利益,可是当体制崩溃的时候,他们又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因为人们对统治者的愤怒,将首先倾泻到那些生活在他们身边的有产者身上——在他们看来,正是这些人的富有造成了社会的不公平,相对于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人们更容易痛恨身边的有产者。
我们这个国家,只要没有外患内乱,放纵民间,允许自由从商,30年可出现盛世,50年可成为最强盛的国家,可是接下来必然会重新出现国家主义,必然再度回到中央高度集权的逻辑之中,必然造成国营经济空前繁荣的景象。无数英雄俊杰,在这种轮回游戏里火中取栗,成就功名,万千市井繁荣,在这个历史搅拌机里被碾成碎片。
因而,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两千余年来,国家机器对商业的控制、干扰及盘剥,是阻碍工商文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政府如何在经济活动中端正自己的立场与角色,工商业者如何与政府平等相处,迄今是一个危险的,甚至仍然带有某种禁忌性的话题——或许只有在这个问题得到解决之后,我们才能更进一步探讨企业家的议政空间。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