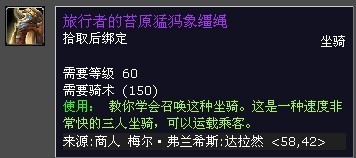记者/周阳
“玩”能带来经济上的收益,就个体来说并非一个新鲜的可能。调查世界上许多大型公司的创始人,他们的最初动机可能都带有“玩”的成分——被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未来愿景激动从而展开某种具有测试性质的行动,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玩”,但这种寓意只能无法复制地存在于个人的体验中。
而这个伟大时代以前的艺术家们的音乐绘画雕塑,可能在某些人眼中具有群体意义上的“玩”性质,但无论他们中间谁的画作卖出如何的天价,无论他们如何希望自己的创作能给自己带来丰厚的财富,仍然不能指望从他们当中发展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因为从个性化的精神劳动到社会化的财富生产之间,信息沟通也好,价格形成也好,成本都是如此之高,这不符合“经济”的原则。 “玩”之所以能够发展为一种经济形态,成为一个群体的理性经济选择,必须是经济、文化、社会结构以及科技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因为只有具备了一定的资源配置的条件,才有可能将私人生活领域的“玩”以最低的成本纳入到社会性的财富创造运动中。 从全球经济发展态势来看,现在正是时候。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玩”已经可以作为一个人、一个企业、一个产业乃至一个国家的经济资源了。比如Google,比如英国伦敦创意市集上的年轻男女。 关于Google如何要求员工们花更多的时间来“玩”,关于Google如何的“奢华”以解除传统上班体制对人精神的折磨,在互联网业界已经口耳相传:往来于办公室之间,员工可骑乘电动滑板车或儿童玩具车,健身球与M&M‘s巧克力随处可见,门户玄关处还有数百盏迷幻熔岩灯,公司里还有宠物的位置。这里更像一个“托儿所”,员工三分之二的时间被要求用来“玩”,因为“这样比较能激发创意。”Google的员工说,“我们没有正式的公司文化。”
事实上,这可能正是“玩经济”与以往经济形态对于经济资源的利用和组织的不同之处。在以Google为典型代表的“玩”经济形态下,产品的成功没有一定的公式,因为市场需求(demand)来自于使用者关于“玩”这一层面的渴望,因而也没有僵化的组织和制度来确保某种被类型化的成功;相反,只有那些具有可经济化的“玩”资源的人群才能成为新的禀赋资源,无论是Google旗下的工程师,还是具有想象力的外援设计师。 不仅是互联网界,在英国伦敦的创意市集上也聚集着一群按照“玩”经济形态的规律聚合在一起的年轻人。他们这样界定自己:“你想从你的设计和品牌中传达什么讯息?”“新鲜好玩,又有出乎意料之外的美。”“你们锁定的客户是谁?”“想在生活中拥有另一个特殊创造物的人”……他们几乎完全靠自己的直觉来确定为市场供应什么;他们的生活“不按常理,没有规律,难以定义,混乱”,你可能看到他们每天都在闲逛,但他们会告诉你“我的休闲和工作是一致的”、“休闲,那是什么……”——正是他们,使伦敦成为全球创意产业的亮点。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