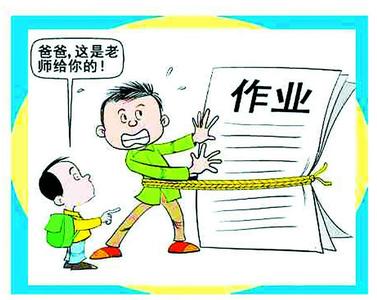系列专题:《经济自由的全球化:全球化为什么可行》
同时,发展中国家总体的婴儿死亡率从1970年的107‰下降到1980年的87‰,2000年的58‰。在东亚这个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则从1980年的56‰下降到2000年的35‰。在南亚,婴儿死亡率从1980年的119‰下降到2000年的73‰。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的进步又是最慢的,但也从1980年的116‰下降到了2000年的91‰。 失去自己的孩子是人生可能遭受的最痛苦的打击之一,因此,婴儿死亡率的下降本身就是极大的福音,预期寿命的延长也不例外。此外这些改进还意味着对教育的投资会变得更有价值。全世界的家庭正变得越来越小,对儿童的教育则越来越受到重视。平均来说,发展中国家的成人识字率已经从1970年的53%提高到了1998年的74%。到2000年,成年男性的文盲率在东亚国家下降到了8%,而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还有30%,在南亚为34%(这实在令人汗颜)。成年女性的文盲率比男性更为普遍,但也在改善。从1990年到2000年,东亚国家的女性文盲率从29%下降到了21%,在南亚国家则从66%下降到57%(这更加令人尴尬),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从60%下降到47%。年轻人中的文盲比率大大下降,这就保证了随着时代的进步该比率还将下降。 生育率的下降同样令人印象深刻。发展中国家总体的平均女性生育率从1980年的4.1下降到2000年的2.8,东亚国家从3.0降至2.1,已接近基本替代率,拉美国家从4.1下降到2.6,甚至南亚国家也从5.3下降到了3.3。在这个指标上,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的进步幅度又是最小的,但也从6.6下降到了2000年的5.2。总体来说,生育率的下降告诉我们,女性对于生育有了更大的控制,孩子数量减少意味着每个孩子得到的来自父母的投资有所增加,并且对孩子生存、成熟的信心有所提高。发展中国家正在发生的人口结构的变化特别令人鼓舞,这既是人们的福利得到改善的标志,又是促进改善的动力。 我们再看看饥饿问题。食品产量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了人口的增长,自1961年至1999年,全球的人均日食物供应量增长了24%,其中发展中国家增长了39%,达到2 684卡路里。到1999年,中国的人均日食物供应量增长了82%,达到3 044卡路里,而在1961年仅能保证基本生存,为1 636卡路里。印度在1950~1951年的水平为1635卡路里,到1999年增长了48%,达到2 417。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估计,每个成年人每天大约需要2 000~2 310卡路里的食物供应,从这个标准看,发展中国家的食物供应水平已经从缺乏达到了充足。饥饿现象依然存在,但联合国粮农组织估计,长期营养不良的总人数已经从1969~1971年的约9.2亿下降到1997~1999年的7.9亿,占发展中国家人口的比例也从35%降至17%。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经济增长缓慢,饥饿的情况也要糟糕得多,从1979~1981年到1997~1999年,营养不良的人口所占的比例从38%下降到34%,但绝对数量却由于人口的迅速增加从1.68亿上升到1.94亿。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