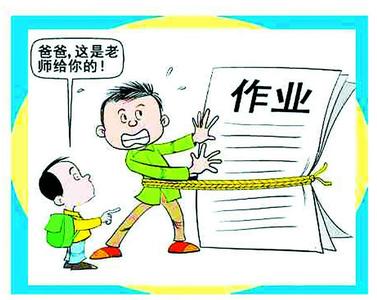系列专题:《经济自由的全球化:全球化为什么可行》
其次,尽管最富裕国家和最贫穷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的相对比值一直在拉大,但居住在世界最贫困国家中的世界人口的比重却在下降。30年以前,中国和印度位于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列,而今天的最穷国家却是塞拉利昂,人口只有500万的小国。中国的平均收入今天已经是塞拉利昂的10倍以上。如今,世界上最大的极端贫困的国家是尼日利亚,它在2000年拥有1?27亿人口,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真实收入水平只有美国的1/40,中国的1/5。因此这就意味着,世界上最富裕国富和最贫困国家的平均收入水平比的扩大,与按人口权重计算的各国间不平等程度的缩小,其实并不矛盾。还有,世界上各个国家内部的不平等情况完全有可能扩大(马祖尔认为这是事实,其实不然),但全球的不平等情况仍然可能同时缩小。除非国家内部的个人之间的不平等的扩大,能够抵消各个国家之间以人口权重计算的不平等的缩小,否则,不但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在缩小,而且全球的个人之间的收入差距也会随之缩小。 来自牛津大学的安德烈·波尔索(Andrea Boltho)和罗马大学的吉亚尼·托尼奥罗(Gianni Toniolo)计算了49个国家(包含世界人口总数的80%)自1900年以来按人口权重计算的不平等状况的变化。在计算不平等指标--基尼系数--的时候,他们把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平均收入乘以各个国家的人口,结果发现,各国之间按此方法计算的不平等水平在1980年达到了峰值,为0?54,此后则下降了9个百分点,达到0?50,这是过去60年以来从未见到过的好转。各国之间的不平等状况的改善正是我们期望看到的情况。 衡量各国之间的不平等状况要考虑人口多寡的因素,是因为我们关心的是人的生活状况,而不是抽象的国家。因此,正确的做法就一定是也要同时考虑各个国家内部的收入分配的变化。弗朗索瓦·布吉翁(Fran?ois Bourguignon)和克里斯蒂安·莫里森(Christian Morrison)为世界银行提供的论文对1820~1992年的收入分配情况进行了大胆的前沿研究,如图9?1所示,他们得出了如下五个重要结论: 第一,从1820年到1980年,全球的个人之间的不平等状况逐渐扩大。

第二,在过去160年中,全球不平等状况的扩大全部都是来自国家之间的差距的扩大,而不是来自国家内部的变化。他们经过相对粗略的估计发现,各国内部在1980年的不平等状况并没有1820年严重。 第三,在1820年,个人之间的不平等只有13%的部分是由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导致,而到了1980年,由国家之间的差距导致的不平等却占到了60%。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各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的差异可以完全解释世界不平等的扩大"。到1980年,决定某个人的贫富状况的最大的单一因素不再是他所处的阶级或从事的职业,而是他所居住的位置。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