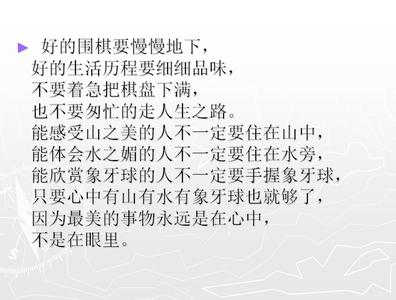系列专题:《寻找真我思索生命:原点》
而我们的校长是一个严肃的人,他个子瘦小,说着很难明白的方言,不苟言笑。但偶然的一次玩耍中,我们几个小朋友在他抽屉里发现了一本私人相册,那里面竟有着我们全班同学的照片--也算是年幼的我第一次清楚看见所谓的"爱"的启蒙吧。 慢慢地长大后,脑海里也有了一些好奇,这位校长究竟是怎样的背景呢?他是大陆人,为何一个人来到香港建立起来这家慈善学校?各方面的打听和道听途说中勾勒出来的校长形象:他是一个出生在中国大陆的普通年青人,已婚。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受到了什么精神的感召,忽然毅然决定离开家乡奔赴香港开创另外一种人生。靠着那一点点的储蓄,他在徙置区七层大厦的天台一点一点地搭建起这所小学来,从找老师,找赞助,到自己亲自教学,他每天都住在学校内的一个小小房间内,没有任何多余的享受,连卫生间也没有,惟一一台小小的旧电视,一拨又一拨天真烂漫到不知世事的小孩,陪伴他度过了数十年的漫长岁月。据说他很少回家乡,仅以书信与妻子来往,只因为舍不得花费。他没有给自己开任何薪酬,只求三餐温饱,却常常为了其他老师的薪资而奔波叹息。成年之后我想起他来,也不禁想像,他后悔吗?他孤独吗?他想家吗?是什么让他愿意这样的付出?是什么一直让他这样无怨无悔地生活? ……究竟为什么,在这样一种生活中,我记忆里他的眼神,却总是安定、满足而充满信心,仿佛活在莫大的喜悦中?

还记得每一次校长最温柔的眼神都是在我们去校长室拿信的时候从他脸上自然地流露出来--除了邮寄我们的各科成绩单给助养者之外,我们也会写一些幼稚却真诚的信件给我们的"助养父母"(这是从英文翻译而来的习惯称呼)。小小年纪不谙英文的我,用歪歪扭扭的中文字写信,幸亏宣明会会负责把书信译为英文,转交到对方手中。之后便是漫长的等待,直到收到大海对面热情洋溢的回信为止。鸿雁往来,一来一去之间我慢慢地在通信中得知自己的助养者究竟是什么人:他们是一对澳大利亚夫妇,男主人是一位牧师,女主人是家庭主妇。他们自己也有三四个小孩,是一个极其温馨而尽享天伦之乐的幸福家庭。每次,他们寄来的信件或明信片中,都不会对我的成绩有所苛责,而是絮絮叨叨闲话家常一般,说给我听各种各样的家庭琐事,什么浇花啦,遛狗啦,他们的小孩在学校里参加了什么社团或是什么运动……等等等等;我便也逐渐鼓起勇气将我在学校学到的每一点滴有用的小细节,交到的每一个新朋友,甚至一些小烦恼都一股脑儿地向他们倾诉。彼此之间如同真正的家人一般,似乎真的成为了远在重洋之外的那个家庭的一份子。除去他们对我金钱的资助外,这样的通信,在精神上令我变得富足,也令我的性格在成长过程中最关键的一段时间里趋向了完善和开朗,对我的人生观和价值理念来说,无疑具有一个良好而温暖的影响。资助有价情无价。这样的关怀,现在回头看来,实在是我生命中的无价之宝。维系人类之间情感和关系的链条,当时我已在懵懂中学到一二。现在回想起来,忽然明白,我的助养父母,我的校长,甚至宣明会的很多工作人员,他们都是这个世界上并不主流,却为数不少的同一类型的人。他们有着同样的信念,对他人、对社会,甚至对世界的关怀。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