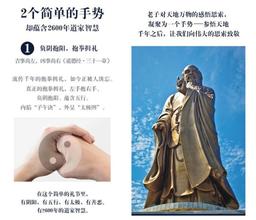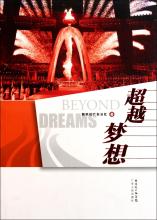系列专题:《名记基础:特稿采写宝典》
作品不多,堆在地上也就1米高;烧后成灰,也就是多半骨灰盒。 张敏的特稿数量虽然不多,但是,每一篇特稿都写的文气十足。洛阳纸贵。 据笔者所知,近几年,著名作家在《家庭》、《知音》上刊发的特稿有,叶永烈《走出毛泽东家族光环》、《何智丽走出婚变阴影》;邓刚《温馨的"拖累"》、《母亲八十有一》;梁晓声《母亲,我不识字的文学导师》;莫应丰《事到如今悔也迟》;徐志耕《海天襟怀》;陈建功《七兄妹对命运说不》等。 二、从大报编委到著名特手 2004年,高汉明想学习《华西都市报》的操作技巧,把特兄特妹们的特稿集中起来,"批发"给各家媒体,共同致富。可是,他花了不少电话费,却没有联系到多少"订货单位",更让他生气和不解的是,有的国家级报纸的编辑竟然反问他"什么是特稿?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弄得他像跟夜游症患者对话似的,非常郁闷。 隔行如隔山。鱼儿在水里游着,你觉得它很憋气,就把它捞出来呼吸新鲜空气,它活蹦乱跳着,你很欣慰,以为自己做了一件善事,救了它的性命。可是,要不了多久,它就玩完了--站在人的角度思考鱼的活法,就像站在鱼的角度担忧人的活法一样,怎么说得通? 周泽新,1955年7月出生,湖北荆州日报社副总编辑,分管《荆州晚报》,主任记者。在报社里摸爬滚打20来年,什么文体没摆弄过?可是,对于特稿,他也曾知之甚少,闹过笑话。下面,是他的一个自述,可以原汁原味地再现当年的情景: 我生活在一个叫荆州的小城里。知道湖北的那个荆州吗?就是《三国演义》里几十回提到的荆州,有一道中国最完整古城墙的荆州。 1998年上半年一天,我去《荆州晚报》周末部闲逛,黄道强问道:"你是不是在外边搞兼职赚了很多钱?"我说:"对天发誓,我没搞兼职。"他神秘地一笑:"我给你指一条致富路,写特稿。"

当时,我在《荆州日报》星期天特刊部当主任,是报社编委,虽然也写"特稿",但那是什么特稿呢?随便写个东西就自己发了。我不知道外边有一个特稿世界。当记者出身的我还顽固地认为,以前我在那么多权威的报纸上发新闻稿,没见赚多少钱,发不了财的。 黄道强骄傲地告诉我,他和周末部主任徐至伟写特稿,还出国开笔会。 《荆州晚报》是荆州日报社主办的。他们的办公室就在隔壁,他们言必称特稿,每天一脸灿烂地拿着各地飞来的稿费汇款单。我仰视他们。 那年8月,长江爆发特大洪水,我上了抗洪前线采访,带几个人驻扎在荆江分洪指挥部,统管日报、晚报前线记者,配车配人,住在宾馆,有吃有喝,占据了新闻资源。《知音》编辑知道了我的名字,托人一个接一个地打电话约稿催稿,可是迟钝的我还没意识到生产特稿的大好时机已到,只是卖力地完成"本报讯"。 荆江已经"封渡"。徐至伟、黄道强却想办法先后从江北来到江南,找到了我的驻地,美其名曰来慰问"周老"。我心里明白,他们是偷偷摸摸来的,可能还是来写他们的宝贝特稿。 到了8月中旬,抗洪接近尾声,心急如焚的《知音》编辑还是没等到我发去的特稿,就把我所写的刊登在本报的长篇通讯《英勇悲壮虎渡河》要去,发表在《知音》上,稿费照发。这是一篇反映长江支流溃堤的特稿,我的第一篇对外发的特稿。 突然间,我猛醒:一个多月来,在宾馆,"抗洪一线"的全国各路记者之所以抢看《荆州日报》、《荆州晚报》,就是因为看中了我们这些当地记者所写的详尽新闻,可以用二手的东西写通讯和特稿。 睡狮醒了,立马发威。我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写了3万多字的《荆江分洪,千钧一发》和每篇5000多字的《长江洪水对民垸的无情判决》、《50万条蛇被洪水冲跑以后……》。我在书房里挂上荆江流域地图,搜集了一尺多高的抗洪资料,赤膊上阵,日夜写稿,写的是昏天黑地。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