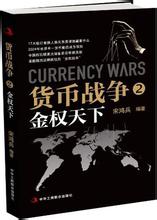系列专题:《活着和死亡:向记忆道歉》
生产组在海边,风大。我们都吹得像渔民,黑得自己都讨厌自己了。莲吹不黑。小脸吹得又红又白。让人眼红。她老是对着水田照镜子:"班长,什么时候让我到镇里照张相啊。"

莲到了镇里照相馆照了一张一寸照片。很灿烂。一星期后,女兵们在照相馆的大橱窗里看到了莲的照片。放大的。足足有解放军画报那么大。莲去了小镇照相馆讨,人家说:"拿五块钱来。"我看了。对照相馆的人说:"你等着。" 我和莲到了政治处打了一张证明:XXX同志系我部野战二所内科战士。中国人民解放军XXX野战医院政治处。 我们拿回了照片。莲把照片挂在墙上。照片上了颜色了。军装涂成了鸡尿黄,脸蛋抹得红红的。嘴也是。 女兵们都笑。特别是那些大城市来的兵。莲问我:"她们为什么笑我?"我说:"你把照片收起来了。我就告诉你。" 莲把照片抱在怀里。 "她们都是从北京上海来的。好照片见得多了。笑你不是很正常吗?" "她们没有我好看。" 我说:"那肯定的。你最好看了。" 莲戴军帽总是往后扣在后脑勺上,前面留着厚厚的刘海。两只小辫子按内务条令不过肩。我们几个老兵戴帽子就扣在头上,不留刘海。特别是我,老远看男女不分。 让司务长说起来,这个小老表妹子,漂亮得狠。 新兵班结束。莲到了内科当卫生员。她有什么事都找我。一口一个班长。 "班长,她们都瞧不起人。"莲说:"你们城里人都穿奶罩。就瞧不起人。" 我大笑。莲比我还大二岁,就是不戴胸罩。早上跑操的时候,胸前抖得厉害。男兵老是看,她自己还不觉得。 星期天请了假,带莲上小镇子里买胸罩。小镇没有,只能跨过现在被评为文化遗产的五里桥去另一个大点的镇子。找了一个女营业员,买了两个八十五公分的。回来一戴正好。 莲朋友很少,除了我就是同她一起参军的北京兵。晚饭后,我们就到后山的金钱松林里散步。她会倒着走在我们前头对我们说:"想不想听我唱歌?我好会唱的。" 于是就唱。 "井岗山上哟荷嘿太阳红罗哎,太阳就是毛泽东哎。" "五彩云霞空中飘,红军从咱家乡过。" 她唱歌带着一点小嗓,可以听到一丝气从她的嗓子里窜出来,声音就变得很柔软。从高高的金钱松林里冒出来,整个后山都是她的世界了。 可是,莲在病房不愿意伺候病人,怕。 卫生员是干什么的?端尿端屎、扫地洗痰盂、送饭送菜、给病人洗脸洗澡。多了。就是给病人当保姆。不想干?请走。 "班长,那些病人好脏哦。吃不消的。"莲说。 "吃不消也要吃啊。你想不想去军校读书啊?" "想是想,就是怕。" "怕也要干。就当是你亲妈。" "我妈妈从来不叫我干这种丢人的事情。" 终于有一天,莲把一个伤员的便盆打翻了,不去替病人收拾,自己蹲在地上吐起来。 所长说,不行就退伍吧。 后勤的一位首长说话了:"毛主席说,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贫下中农的后代要重点培养。不适合当卫生员就送军校去学护士。" 莲走了。 我还在病房当我的卫生员。她对我说:"班长。你要好好表现。也去读书。" 再看到莲是我从军校回去到医院。莲告诉我,她提干了,一个月五十四块五。她戴了一块上海表,穿了一件淡黄的的确良衬衣。我在学校也提干了,就是不敢穿的确良,怕别人说自己搞特殊化,照旧是发的棉布衬衫。手表也不敢戴,放在抽屉里。那是一块越战军用侦察手表,黑色,有方位刻度,夜光。防四十米深水。莲看到了。说不好看。还是上海表洋气。她的被子也换了,托人从杭州买了一条红的绸缎被面。我还是军用被子。我喜欢那种绿色。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