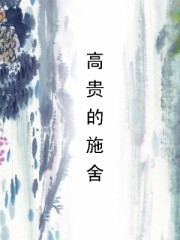莫言获诺贝尔奖的消息公布后,我发了电邮给“葛老”,对他说他的译文对莫言获奖功不可没。“葛老”是我和郑树森教授对老友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的昵称。莫言拿奖,靠的当然是自己功夫,但因为十多个评委中只得马悦然(G·ran Malmqvist)教授通汉语,其他评委对莫言的评价,只得通过翻译。 葛浩文英译《红高粱》于1993年春在美国和英国同时出版。由于译者的名气,原著作品的特色和出版社鼎力的推动三者配搭得宜,《Red Sorghum》在1993年亮相时可说是英译中国文学一大盛事。

英国汉学家W.J.F. Jenner读中国现代文学,认为像巴金、茅盾这些作家,在中国尽享经典地位,但在英语世界却难有市场。为什么?他的解释是,外国读者除非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有特殊的爱恋,否则怎会有兴趣融入中国文学感时忧国的世界?既然这样,那么依Jenner的看法,哪类作品比较容易吸引西方读者的注意呢?他话说得斩钉截铁:be different。要与别不同。独辟蹊径。 打开“新时期”冒起的“先锋派”小说家的作品看,不难发觉无论在题材上或叙事手法上他们的小说都说得上“离经叛道”,够different的了。《红高粱》第一章第一句就见颠覆传统:“一九三九年古历八月初九,我父亲这个土匪种十四岁多一点。” 英译《红高粱》在美国上市后,我看到过的书评,几乎一致交口称誉。《纽约》杂志书评人Rhoda Koenig以“Sauage Grace”为标题,指出书中许多意象,独具匠心,摄人心弦,虽然有不少场面是暴戾的、血淋淋的。 “Sauage Grace”可译为“野蛮的典雅”。这是修辞学上的“逆喻”(oxymoron),看来自相矛盾,却不碍矛盾统一,也是人生实况的一个写照。用莫言自己的话说:这是“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神圣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二位一体的结合。 莫言的叙事手法,卖尽乖巧,一时魔幻,一时后设,一时荒谬,一时意识流,要译成外文,不易周转。《红高粱》的作者有幸,得到葛浩文充当他英语世界的“代言人”。葛老中文扎实,身怀十八般武艺。这已够难得的了,更难得的是他的英文书写能兼顾雅俗、暴烈与温柔各层次的语境。没有这种能耐,怎胜任把莫言小说世界“野蛮的典雅”的面貌重组出来? 当年在《纽约时报》写《红高粱》书评的是Wilborn Hampton,国际新闻版编辑。他给此书打分数用的标准是:译文的好坏、故事本身有什么值得西方读者一看的地方。Hampton不谙中文,因此他衡量译文好坏的绳规倒也简单:葛浩文的英文写得到不到家。他推许英译《红高粱》的文字vibrant,色彩鲜明,活泼有生气。故事和人物呢?层次多面,引人入胜。书评人的结论是:莫言那些“土匪种”的角色和入了神话结构的高密东北乡从此入了世界文学的版图。 莫言的作品何止“三反四反”。以“阴谋论”的眼光看,他既反封建,也反时髦。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吃胎盘和roast baby的王八蛋是汉人,奈何美帝及其同路人的学者专家,对反映“龙的传人”种种“劣根性”的魔幻书写却情有独钟。怎不教人掷笔三叹。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