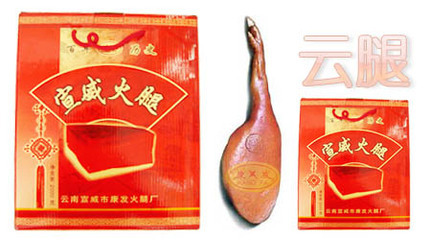一转眼19年过去了,这期间我不仅向老师学到了水墨技法,也学到了不少为人做事的道理。
我的老师邓锡良
金克强
和邓锡良先生相识,要从1989年说起。
那年我38岁,在神州书画学校任客座讲师已有9个年头了。一日,在报纸上看到一条短讯:青年花鸟画家郭永琰画展在南方五省市巡回展出。郭永琰正是我在神州书画学校结识的好友。以前,我只知道他除了画西画,也在学国画。没想到短短几年竟有如此长足的进步。惊喜之余,我拨通了永琰的电话,以示祝贺。永琰当晚便带着他的画作影印集到我家来了。看着一幅幅水墨淋漓的花鸟画作,我简直是为永琰取得的成绩叹为观止了。我虽是一名油画爱好者,对于中国画也并不陌生。这里的斤两也是看得出的。永琰从我的眼神中看出了我的向往,便问我想不想学国画。我说想,就这样,次日他便将我引见给了时年61岁的邓锡良先生。
邓先生见了我头一句话便问:“你能坚持学下去吗?”
我说:“能!”
邓老师又说:“从来只有学生不学的,没有老师不教的。”
我再次保证一定踏踏实实跟邓先生学画,绝不三心二意。这也是我和老师的口头约定。
1956年,28岁的邓锡良先生就读于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有缘在北京和平画店结识了国画大师李苦禅先生,进而登堂入室,成为苦禅先生最得意也最忠诚的弟子。在随苦老近30年的学习期间,邓先生不但在艺术上形成独特的风格,在人格魅力上也深受苦禅老师影响,并形成风范。正像苦禅老人的夫人李慧文女士所言:“锡良和苦禅学画二十八载,不论顺境、逆境,始终不离不弃,侍奉左右”。
邓锡良先生从事国画研究创作60余年,甘于淡泊,不计名利,从不做卖画的生意。对于教学,他也像他的恩师苦禅老人一样不收学生一文钱的学费。这在今天,实不多见。
锡良先生对恩师至忠,对学生和他人也是至爱。他门下入室弟子数十人,教过的学生更是数以百计。对于生活困难的学生,经常伸出援手,少则几十元,多则数百元。这在当时每月薪金仅有一、二百元的先生来讲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每个学生手里都有几十张他给画的稿子。至于同邓老师合作或有邓老师题跋的画作就更多了。
锡良先生为人作画,即使画得再好,也让别人拿走,决不反悔。有一次他为我画猫,头一张形神毕肖,乃是不可多得的佳作。先生想留作稿样,便接连又画两幅,均不如第一张。当为画题款时,我对先生说:“您把第二幅或第三幅题上给我便行了”,先生却说:“不能这么做,怎么说的便怎么办”。硬是坚持把最好的一张送给了我。
如是者三,这么些年下来,我手中存的先生作品中有几幅,如《葡萄·松鼠》、《有馀图》、《猫蝶图》、《鹭柳春风》,均是先生画册上同类作品所不及的。
我一向对先生的话唯命是从,可有一次却对先生的命令推而又推。那还是在北京闹“非典”的时候,一位师兄由于患直肠癌导致癌细胞扩散,在肿瘤医院化疗两个月后回家休养。邓老师闻讯后,马上交给我200元钱,让我给师兄送去。这着实让我为难了。自从师兄生病以来,我一直都为他捏把汗,放心不下。但非典时期,人人自危,很多接触过危险地区的人员都被列为疑似病人进行隔离,平日里亲如一家的街坊邻居见了面,也都噤若寒蝉匆匆擦肩而过。此时,让我去和一个刚出院不久的病人接触,万一染上非典,后果不堪设想。尤其那时候邓先生及夫人年事已高,我经常过去服侍左右,如果再因此把非典传染给邓先生一家,那我更是愧对恩师。我左右为难,不觉之中七天过去了,先生急了;“我要是年轻,早就去了”。在此情景下,我只好瞒着家人带着十二分小心,去看望师兄,用“舍命陪君子”这样的词汇来形容当时的心情真不为过。
锡良老师画画,却不做画的生意,这在与他交往的人中是众所周知的。在北池子头条那两间拥挤的平房中,床底下堆满了几麻袋信件。都是素未谋面的人慕名索画寄来的。先生有求必应,有信必复。也有生人冒昧登门造访的,他不但白给人家作画,道远的、有残疾的、还要留人吃饭。有的人实在过意不去,拿出钱来酬谢,邓老师也是坚辞不受。仅举一例,可见一斑:大约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一个冬天,天上飘着大雪,丰台302医院的一位外科主任到学校向邓老师求画一幅雄鹰图。邓老师当即答应按地址寄去。后来这位老医生又亲自送来一本神话辞典表示谢意,说刚从一位老画家那儿来,画了两只青蛙,要了40元钱。这与锡良先生的慷慨相比,反差甚大。锡良先生手中的画笔从来不为人役使。十几年前,先生应邀去外省作画,完成任务之余,抽空为服务员画了几张,不想邀请单位的一位联系人进来了,见状便说:“邓老,您怎么还给他们画画呢?他们可都是合同工。”锡良先生遂操起画笔问那个人:“这画笔是你拿着还是我拿着?”那人说:“您拿着。”锡良先生正色道:“那你还管得了我给谁画画吗?”事后据老师说,连烧锅炉的工人,他都给画了画。在锡良先生心中,他的画是不分等级的,他也绝不会拿自己的作品去钻营、去巴结、去逢迎。

衡量一位艺术家高低的标准是什么?不是金钱,也不是地位,更不是那些廉价的炒作和书托、画托的欺诈。唯一的标准便是艺术作品本身。邓锡良老师早已把绘画看作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半个多世纪了,他从未放下手中的画笔,创作了数以万计的作品。正是这种多年的积淀,他才能厚积薄发,举重若轻,技艺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看锡良先生画画,无疑是一种享受。2008年锡良先生应邀前往山东聊城、冠县作画。我作为随行人员,一同前往。不到一个星期,除了参观游览,锡良先生洋洋洒洒连续作画数十幅。大到丈二匹的巨幅,小到四尺三裁的小画,无一不是笔精墨到、气满神足。在画丈二匹的巨幅画作《十里荷塘》时,只见先生用废宣纸蘸墨在画纸上直接点染,兴起时便直接用墨盘向画面泼洒。走笔如飞,仅用了一个多小时便完成了。一时间画幅上水墨淋漓,水痕夹杂着墨痕更有一种自然天成的味道。如此庞大的画作谁又能想到出自一位80岁高龄的老人之手呢?看似毫不费力、信手拈来,岂不知那是邓老多年临池不辍的结果。邓老在人陪同下到李苦禅老师年轻时上学的地方拜谒。有人看到泡桐,问他怎么入画。回来后,邓老不假思索,不到一个小时,一幅彩墨俱全六尺整纸的泡桐便画完了。在那万花攒簇的花丛中,或飞或立几只八哥穿插其中。举座哗然,可谓神来之笔。人云未见其画,已闻其香,此之谓也。“凡大家作画,要胸中先有所见之物,然后方能下笔有神。”白石老人所言即此理也。临走时锡良老人照例也没忘记为服务员留下两幅墨迹:《墨牡丹·蝴蝶》、《白鹭》。邓老师在迟暮之年想到的并不是什么颐养天年,而是执意要为世界、为社会留下点什么。这种老有所成,老有所为的精神不正是我们年轻人要起而效法的吗?
邓锡良老师的艺术人生,在潜移默化间,全方位地传承了以苦禅先生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理念和艺术精神衣钵。1987年,秉承苦禅先生遗愿,由苦禅先生的夫人李慧文女士及他的儿子李杭、李燕出面,在山东济南李苦禅纪念馆为其举办了苦禅先生众多弟子中,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的邓锡良画展。一时观者如堵,好评如潮。那时59岁的锡良老师正值年富力强,4张六尺整纸的画作,约用两个小时便完成了。时隔21年后,李苦禅纪念馆又为邓老师在山东济南举办第二次画展。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祝贺邓锡良先生的画展成功举办。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