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雨,成都飞深圳。
80年代刚到深圳创业不久,读了张五常先生的《卖桔者说》,文章举例日常生活来对经济学原理深入浅出的讲解,引人入胜。因张先生的通俗文章知道了佛里德曼、高斯、制度经济学。以后有幸认识了张先生,03年攀登珠峰,张先生赠写了一首诗,很在意装裱挂起来。近期《劳动合同法》无论学界、商界引起很大的反响。引荐张先生的一篇文章,其从劳动契约的角度认为新公布的《劳动合同法》对劳资双方都没有获得利益而反对。文章如下:
国内称"合同",我爱称"合约",是同一回事,只觉得"约"字是仄音,较为顺耳。
写了几期中国最近推出的新劳动合同法,读者反应多,同意或反对的都拿不准问题的重心所在。是我之过:怕读者跟不上,没有把经济理论的要点写出来。今天看,劳动市场的反应愈来愈麻烦,不容易的理论也要申述一下,希望北京的朋友用心细想。
首先要说的,是新劳动法的意图是把租值转移,或把劳资双方的收入再分配。收入再分配的方法有多种,为祸最大的通常是干预合约的自由选择,而新劳动法正是这种干预。如果从资方取一元,劳方得一元,没有其它效应,我们不容易反对。如果资方失一元,劳方得六毫,社会损失四毫,不利,伦理上也有支持的理由。但如果资方失一元,劳方不得反失,那我们就没有理由接受了。目今所见,新劳动法的效应是劳资双方皆失!某些人会获得权力上升带来的甜头,但不会是资方,也不会是劳苦大众。是中国经改的关键时刻,我们的注意力要集中在低下阶层的生活改进。这几年他们的收入上升得非常快,说过了,新劳动法把这发展的上升直线打折了。
从一个真实故事说起吧。一九四三年的夏天,我七岁,桂林大疏散时坐火车顶到柳州会合母亲,继续走。柳州疏散得八八九九了。母亲选水路走,要从柳州到桂平那方向去。她带着几个孩子到江边找船。不知是谁找到一艘木船,情况还好,可用,但船夫何来呢?该船可坐约三十人,找乘客联手出钱不难,但要找苦力,船行主要靠苦力在岸上的山脚下以绳拉动。找到的十多个苦力互不相识,是乌合之众。母亲带着几个孩子,是大客户,参与了拉船费用与管理安排的商讨。花不了多少时间,大家同意选出一个判头,算是船程的老板,苦力人数足够,工资等都同意了。船起行后,有一个拿着鞭子的人监管着拉船的苦力,见偷懒的挥鞭而下。
母亲是我曾经认识的最聪明的人,落荒逃难之际不忘教子。船起行后,她静悄悄地对我说:「那个坐在船头的判头老板是苦力们委任的,那个在岸上拿着鞭子的监工也是苦力们聘请的。你说怪不怪?我知道,因为他们洽商时我在场。」
一九七○年,在西雅图华大任职,多伦多大学的John McManus到我家小住,提到他正在动笔的关于公司的文章,我认为他的分析不对,向他举出广西的拉船例子。他把这例子写进文章内,脚注说是我的。后来Michael Jensen与William Meckling发表他们的公司文章,再举这例子,说是McManus的。八十年代后期,一位澳州教授以拉船的例子说苦力是被雇,不是雇主,文章题目用上我的名字。胆大包天,他竟然到港大来讲解该文。我在座,只问几句他就讲不下去了。
听说北大的张老弟维迎曾经研究过究竟是资本雇用劳力还是劳力雇用资本这个话题。我没有跟进,不知维迎的结论。但我想,谁雇用谁大可争议,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合约的安排不同,交易费用有别,减低交易费用是经济发展之途,而从这角度看,合约的自由选择有关键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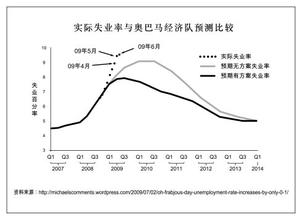
这就带来我自己一九八三发表的《公司的合约本质》,整篇文章是关于劳动合同的经济分析,没有其它。首先要说的,是劳资双方是合伙人。一方出力,另一方出钱,不是合伙是什么?合伙当然不是仇家,毋须敌对。当然,因为交易费用的存在,任何合约都可以有纠纷,但政府立法例,左右合约,有意或无意间增加了劳资双方的敌对,从而增加交易费用,对经济整体的杀伤力可以大得惊人。
为什么会有公司的存在呢?首先是史密斯的造针工厂,分工合作可获大利。上述的拉船例子是另一方面的合作图利之举。一艘可坐三十人的船,一个人拉不动,要用苦力十多个。船大乘客多,十多个一起拉,每个乘客的平均成本比一个苦力拉一只小艇的乘客平均成本低很多。为了减低成本而获利,大家就「埋堆」或组成公司了。「公」者,共同也;「司」者,执行也。
还有另一个远为湛深的问题,由高斯一九三七首先提出。「被雇」的劳工,大有奴隶之慨,由老板或经理或管工指挥工作,不靠市场的价格指引,那是为什么?其实不是奴隶,因为劳工有自由不参与公司,可以自己到街头卖花生去。
 爱华网
爱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