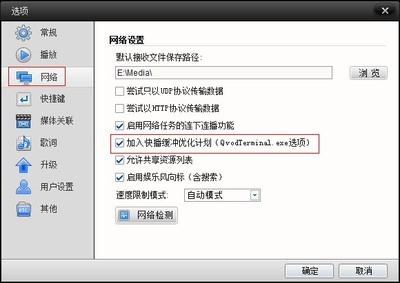在十八大提出“收入倍增计划”之后,各省市均热烈响应,部分省市更已制定加速计划—据《京华时报》12月3日报道,黑龙江制定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幅为12%以上,而中西部地区则普遍将为期10年(2010-2020年)的收入倍增计划,浓缩为5年提前至2015年前后完成。 对中央“收入倍增计划”的响应和加速,不仅表明各级政府已经意识到,提高居民收入是呼应民心之举,其关系民心所向刻不容缓,亦表明在经济增长动力源泉的选择上,提高居民收入增加消费占比已经形成共识,其关系经济转型不可或缺。 回顾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我们会发现,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速除少数年份外,其余均低于GDP增速,而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则在改革开放初期之后,大幅低于GDP增速。而如果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速计,再减去物价上涨(CPI)指数,两者的差距会更大。 在改革开放的早中期,居民人均收入低于GDP增速,固然可以理解为,在资本和技术要素过于缺失的早中期,需要相对通过对人均收入增速的抑制,以吸引资本、并促进资源整合。与此同时,在改革开放早中期,亦相对需要持续的大规模基础设施投入,以逐渐形成更具吸引力的投资环境,而这亦需要对人均收入增速的相对抑制。但是,在2000年、尤其是我国加入WTO之后,在经济增速、尤其是外贸增速超速前行的同时,我国要素资源的构成亦已发生本质变化,核心要素资源稀缺由之前的资本和技术,日益转变为能源和人力,以及环境承受能力的大幅降低。在这种格局之下,大幅增加居民人均收入,并以此逐渐扭转以出口和投资为导向的经济增长结构,则显然是绝对必要的。 实际上,对于增加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重要性的认知,近年来已逐渐形成政界和学界的共识,相关举措亦已逐步推进实施—比如,最低工资标准的累次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相对健全,以及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不断上调。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近年来,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正与经济增速日趋贴近。 可是,在相对肯定的同时,我们依然会发现,增加居民人均支配收入的力度仍然偏弱,一来我国近年来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速仍然相对低于GDP增速,二来酝酿长达8年之久的收入分配总体方案至今仍束之高阁。更令人窘迫的是,在居民人均收入增速相对提高之下,贫富收入差距却以更大的幅度在放大。 贫富差距的过于悬殊,不仅让“人均”收入相对提高的意义聊胜于无,更无法真正解决我国经济增长结构的扭曲—因为,极少数富裕人群的消费,往往以炫耀性消费为主,而试图通过消费促进我国的经济增长,则须大幅增加更多人群的日常消费。 对我国贫富差距日渐悬殊进行探寻,我们则会发现,其根源在于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剪刀差、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盈利能力的背离,以及行政和事业单位人员过多的灰色收入。在度过改革开放前10年之后,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剪刀差持续维持在2.6-3.3之间,而国有企业则在近10年的“国进民退”之下,依赖诸多政策资源的倾斜,其赢利能力正以民企盈利能力的弱化为代价,而行政和事业单位人员的灰色收入,则更在近5年来的行政主导性投资扩张之下,不但屡禁不止,其操作空间和数额反而大幅放大。 缩小城乡居民收入的剪刀差,才能切实加大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减少对国企过多的政策倾斜,才能相对平衡国企和民企之间明显背离的盈利能力,杜绝行政和事业单位人员的灰色收入,才能真正使行政职能转变得到彰显。 而这些欲得以实现,则显然需要以公平为前提。缺乏公平的制度与环境,则上述不同层面所体现的贫富差距,不仅难以缩小,更会持续放大。而贫富差距的难以弥补,则必然会造成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无法有效推进,而在经济增长结构持续扭曲之下,“收入倍增计划”(纯倍增)则极有可能最终沦为空谈。

实现收入倍增计划,公平既是目的,更是前提。在历年经济高速增长之下,只有相应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才能切实彰显经济改革的公平性,而惟有以公平为前提,亦才能从制度层面降低贫富差距,通过经济结构的优化推动新一轮经济增长,从而真正实现收入倍增计划。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