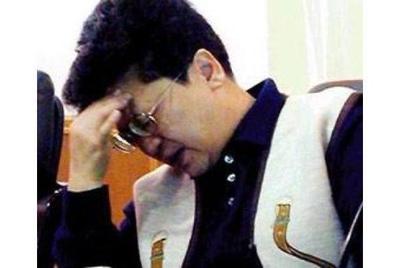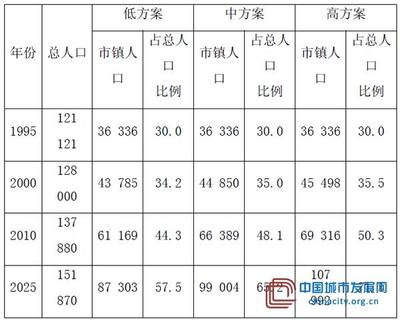中国的企业家往往喜欢追求完美,但又似乎总难以摆脱一种失败的宿命。其实,历史对一个企业家是否伟大的评价标准,不是看他在各方面有多么完美,而是这个企业家的自我选择是不是符合“神性”——自然与社会规律!正如克林顿,他并不算是一个好的丈夫,但绝对是一个伟大的总统。
作者简介:姜汝祥,北京锡恩管理顾问公司总裁
知耻而后勇:不懂得暂停的人不会真正懂加速
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二十多年之后,整体上,中国相当一批企业家在思维上应当调整一下,不妨在高速增长的轨道上暂停一下,也不妨在业务上收缩一下阵线,整理一下思路,回答一些基本的问题。只有懂得暂停的人,才真正懂得加速。
市场经济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市场经济建立在符合人的利益本性之上,这种经济也就拥有了不依赖于伟人,而依赖于机制的特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是机制而不是我们的主观努力,决定了企业的增长速度,一旦增长机制建立起来,持之以恒,你就是不想发财都难。索芙特总裁有一次对我说,市场真正的本质是有人卖,而不是有人买。我觉得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道理很简单,“有人买”是顾客需求,“有人卖”则是企业组织、制度与文化,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增长机制。从古到今,顾客需求都不是问题,那为什么是市场经济创造出物质的极大繁荣?答案就在于市场经济解决了有人“替你卖”——企业做到了把若干个体户组成一体,同时又保证单个人利益,利益机制一旦与资金、设备一样成为企业增长要素,做好了,你就是想不发财都难。反过来讲,如果你没有建立起真正的增长机制,那么,目前的繁荣可能也只能是昙花一现。
举个简单的例子。为什么最近几年中国股市会出现长期低迷?甚至政府的若干救市策略均显效不大?为什么不少上市公司的老总前赴后继入狱或下台?为什么不可一世的德隆会在一夜之间就成为历史?
答案其实并不复杂。没有建立起一套“让员工为你玩命”的共赢机制,靠炒作包装,靠投机取巧,能够兴盛一时,如何欺骗一世?
所以,请企业家们暂停一下吧!因为时代正在改变,如果说过去的主要矛盾是政府在行政干预市场与企业运营,企业家抱怨的是法制化不健全、市场不健全,导致企业做不大、做不强的话,我觉得现在应当反过来了。现在的情况是,正是政府的法制化努力,正是市场的规范化努力,导致了股市的低迷,导致一大批上市公司业绩的衰退,导致一大批“乱世英雄型”企业家的落马。
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的“资本运营”这类词,就成为一个贬义词,这个词是中国企业利用政策转折与消费者不成熟,趁市场不成熟牟取暴利的代名词。这个词是一个历史时代的产物,可以理解,但每一个时代都应当有自己的主题词。今天,中国企业的主题词应当是“以打造内功为核心的竞争力培育”。再谈什么资本运营之内,那不仅与趋势背道而驰,而且也是中国企业做大做强历程中的一种耻辱。
王安之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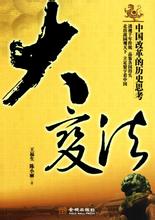
一个强大的企业背后,通常有一位优秀的企业家,而评判他优秀的标准,不是看他的战略有多么超前,个人多么有才华,甚至说对家庭多么有责任感,而应该是,他所领导的企业能否在行业中独领风骚,不管他用的是小农文化也好,帝王权谋也罢。
在1985年《福布斯》“美国400名最富有的人物”名单上,一名优秀的中国企业家王安位居第8,王安公司是当时美国最优秀的计算机公司,全球最优秀的CEO钱伯斯当年就是从王安公司出来的。
但是,当1992年,王安公司宣布破产保护,公司股票价格由全盛时期的43美元跌到75美分时,它的失败表面上是没有抓住个人电脑这一历史机遇,但研究公司历史的管理学家早就有了定论,王安公司的死亡不是因为技术,即使在个人电脑技术上,王安公司直到破产时,也并不落后于当时的IBM多少。
那么王安公司究竟倒在了那里?真正导致王安公司死亡的,是王安公司的管理文化。王安公司的管理在本质上,使用的是中国帝王的驭人之术。
王安24岁赴美,在应聘IBM时备受侮辱。王安开公司后,很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想改变华人在美国的形象。这种自尊与复仇既体现在他坚持用中国名字命名公司,也体现在他的管理方式上。
众所周知,王安实验室的“三剑客”考布劳、斯加尔和考尔科,尽管才华横溢,但却相处得并不好。王安不仅没有设法通过战略设计与制度安排,将他们统一在公司的战略目标下,而是让他们各自负责一个项目,鼓励他们三人相互竞争,然后王安像皇帝一样,从平衡这些能人中获得好处。
1986年1月,王安任命36岁的儿子王列为公司的总裁。年轻气盛且接受过正规教育的王列提出了很多看似先进的创造性主张。比如他让考布劳三人统一思想,停止开发那些互相之间不能匹配的产品。他认为计算机和办公自动化未来的出路在于系统化,在于整个系统互相配合和补充,而不在于单一产品的功能。
他的想法受到了公司不少人的拥护,事实上从今天来看无疑也是正确的,然而,他却失败了。失败的原因在于,王安公司的运行方式是一种能人体制,王列哪里有他父亲那种个人权威与管理能力?
1984年,斯加尔决定离开王安实验室。1985年,考尔科也离开了王安实验室。考布劳、斯加尔、考尔科三人可以说是实验室的三根支柱,他们为公司带来了几十亿美元的利润,然而他们三人都离开了,与其说,他们是因为受不了王列的工作方式而离开的,不如说,他们只能在王安这种“强人”领导下才能相安无事。
王安公司的兴亡,再次演绎了中国古代王朝更替的兴衰律——王朝因为伟大的帝王而兴,王朝因为没有伟大的帝王而死。我建议中国的企业家好好花时间关注一下海外华人企业的兴衰史,因为这些兴衰史对我们今天的这些优秀企业是一个重要的提醒:帝王谋略与管理企业短时间内并不矛盾,而且还会减少创业时期的“管理成本”。小农文化与强大的销售额短时间内也并不矛盾,而且在某个强人下还有可能“超速发展”。
其实,王安算是一个优秀的企业家,只是他的最大败笔在于,把公司的大权传给了自己的儿子。
“若神不在,一切皆无”:当过时的是整体而不是个人
不幸的是,经营企业是一个马拉松,而不是百米赛跑。所以,华人另一个伟大的企业宏基,它的创始人施振荣先生很早就给自己制定了退休计划,也很早就决定不把位子传给自己的家族。当退休时间临近的时候,宏基正处于劣势,很多人都会预计他不会退休,要退也会选择宏基业绩好的时候呀?但施振荣先生毅然退下,结果宏基不仅没有垮下,反而在职业经理人的打理下欣欣向荣!
其实,退不退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退是为什么,不退又是为什么?从历史的长河来看,每一个具体的生命都包含着悲剧性的价值,因为我们的生命太短暂了,生命的短暂使我们永远到达不了自由的彼岸。正因为如此,生命的价值就在于选择,而选择的前提是必须有标准。没有标准,哪有选择?所以,管理作为一种管理人的科学,它本身的首要任务就是建立“标准”,这就是德鲁克所讲的,管理学为什么会比宗教学更接近“上帝”,因为“若神不在,一切皆无”。
中国有句古话说得好: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当“天”与神一样只不过是一个代名词,代表着控制万物运转的自然之律。那么,我觉得无论多么伟大的企业家,要使得短暂的人生有价值,就需要问自己一句话:我选择什么?有时候,提出一个正确的问题比解决问题本身还要重要,因为这使我们的生命开始有了价值。否则用毕生的精力去回答一个错误的问题,就必然会出现像三九的赵新先,长虹的倪润峰这样的悲剧。
要回答“我选择什么”,前提是“我选择的标准”是什么?在这一点,我建议张瑞敏,以及若干像张瑞敏一样雄才大略的企业家,不妨跳出眼前的是是非非,不妨把成功看得淡一点,把眼光放到那些世界一流企业的创始人群体身上,以福特公司的亨利·福特,IBM的沃森,摩托罗拉的高尔文,沃尔玛的山姆·沃尔顿等这些伟大的企业家为标杆,有了这一标准,然后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亨利·福特,托马斯·沃森,保罗·高尔文,山姆·沃尔顿在我今天的位置,他们会选择什么?
也许,我们永远也无法像这些伟大的企业家一样,做出那么伟大的事业,但是,像他们一样思考,像他们一样选择,却是让我们的生命拥有价值的唯一归宿。事实上,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在读这些伟大企业家的传记中,我们会发现事实与想象的相反,像福特这样的伟大企业家,同样有着常人的许多错误。比如福特经常听不进不同意见,迷恋权力,管理作风粗暴,比如他在T型车的成功上过于轻敌,被通用汽车超过。比如IBM的创始人沃森,喜欢个人崇拜,喜欢独断专行等。
但是,请注意,一个企业家的伟大,并不是因为他不犯错误,历史并不在意一个人犯下的错误,包括在个人品行上的巨大错误,历史对一个企业家是否伟大的评价标准,是这个企业家的自我选择是不是符合“神性”——自然与社会规律!
一旦懂得了这一点,一旦懂得中国目前的优秀企业家与福特、IBM沃森这样一批伟大企业家的差别,不是个人品行与才能,而是他们成功的制度环境。当我们站在时代的角度去看中国企业管理方式,我们就会明白,中国目前这一代优秀企业家,我们不排除个别人的超越,但从整体上看,从时代的角度看,他们的历史使命已经结束,整体上他们都应当集体退下,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代人的过时问题。
这就像运动员一样,如果功勋卓越的上一代运动员不退下,就没有下一代优秀运动员的崛起。我们应当懂得一点,当前进的道路出现分叉的时候,决定成败的就不完全是能力,而更多的是你的选择,你选择了什么,你就是什么。
“宪政精神”才是企业持续之源
一个企业要做好,需要一个优秀的企业家,而企业要持续,却依赖于制度文明。所谓制度文明决定企业成败,其实是想表明一种发展观:没有坏人,只有坏的制度。在好的制度下,坏人也会变成好人,而在坏的制度下,好人也会变成坏人。
也有很多企业家觉得奇怪:“你看我们的制度已经制订了几十本了,可为什么仍然是毛病百出?”问得好,如果制度就等同于制度文明,那么经营企业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简单的事了。制度之所以能够成为文明,核心在于制度在制订的时候,其首要目的就是约束制订者本人。想想吧,我们为什么要制订这个而不是另一个制度?我们为什么要这样订而不是那样制订一个制度?核心在于,我们承认自己超越不了自己,我们承认人性之软弱,于是我们借助制度的公开,透明与处罚来制约自己。
一旦我们能够制约自己,物质财富的繁荣也就是时间问题了。在大多数情况下,阻碍我们致富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自己,是我们头脑中那些“自以为是”的观念。如果我们将制度的基点放在企业发展的要求上,放在企业家自我放纵的制约上。那么,专制一点独裁一点又如何?
然而恰恰在这一点上,中国最优秀的一批企业家大多是相反。我们大都对如何“人治人,己治己”的方法烂熟于胸,而对“法治人,法治己”总觉得隔一层,不过瘾。
法治与人治最大的差别在于,人治是一种基于个人感情与信任的放权系统——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在人治下,我对你全面信任,全面放权,如果没有结果,不是你这件事做不好,而是你对不起我,或背叛我。
问题的关键在于,在短期内,人治远远比法治的效率要高要快,所谓“士为知己者死”,感情与信任往往能够创造奇迹,而我们的环境又往往是一个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环境。所以,我们也就不奇怪为什么中国目前最著名的那批公司中,大多仍然是一个人治的天下,谁不想要奇迹?
相应的,法治的管理体系要发力,就要慢多了。因为法治是一种基于责任约束的奖励惩罚系统。而这种约束源于企业之所以为企业的公理假定:比如人生而自私,企业生而逐利;比如欲望偏好决定购买偏好,比如平等竞争,公平交易等不需要讨论的前提。
标准并不高,但一经确定就必须遵守或做到,一切与此相违背的规则都要修改,这就是“宪政精神”!因为宪法构成了一个国家最基本的底线要求:如果做不到这些底线,国家就不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同样,企业也需要确立这种“宪政精神”,如果做不到这些底线,企业就不再是现代意义上的企业,那也许只不是某些英雄赚钱,或实现个人梦想的工具而已!
为什么企业需要“宪政精神”来支撑才能持续?这不仅是因为宪政的本质在于服从公理、遵循规律,更重要的是,宪政精神的核心在于“低标准,严要求”——每个人都可以做到,而做到的都是最基本的,这不一定帮助你发大财,但却能够保证你不死。反过来看,人治下的感情与信任却正好相反,高标准,高要求——只能做一时,很难做一世。结果就必然是广泛的做假,拉帮结派,以及形式主义等等。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