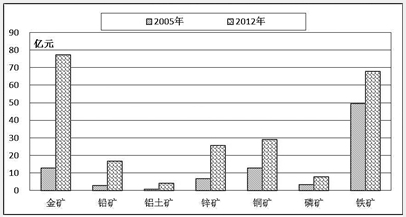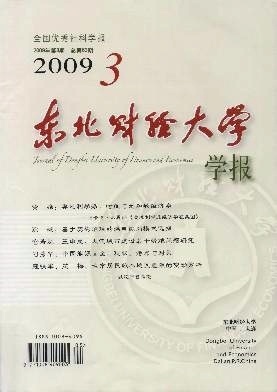真实的分布式能源应用其实并不遥远,就是现在!只不过,所应用的地方有点让人意料不到——美国监狱。 Santa Rita 监狱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阿拉米达县,关押着4000名囚犯。在最近,这所监狱完成了一项分布式能源应用。监狱内的柴油发电机、风力涡轮机、太阳能电池板、燃料电池所产生的电力被集合在一起,形成一个脱离集中供电的大型电网而独立运作的微型电网。在遇到大电网断电的意外情况时,微型电网可以为监狱继续供应电力,每年能为监狱节约10万美元。而当大电网遇到用电高峰时,微型电网还可以把自己多余的电力出售给电力公司。 这是个典型的分布式能源应用,其最大不同之处在于把电压很不稳定的、时断时续的风能与太阳能电力,同常规的柴油发电机和燃料电池电力融合在了一起,形成一个独立的微电网。

这个微电网既不同于常规的紧急备用电源系统,也不是独立的一大块蓄电池,更不是风能、太阳能电网,而是在这几者的基础上前进了一步。在无风或太阳落山时,可以供电;在柴油发电机使用受限制时,也可以供电——这些都在于微型电网把不同能源电力整合在了一起使用。这除了得益于数千块电池组成的超级阵列外,更为重要的是靠专门的电力电子设备及控制软件把多个能源系统与储能设备整合在一起,进行不间断供电。这个微电网中每个能源点处与大电网的连接处都安装了如同大型计算机大小的网络控制器。能调整不同能源电力频率和电压的设备,则可以用来协调来自风能、太阳能电池、柴油发电机和其他能源的电力。专门的软件系统,用于帮助微电网从每个电源都尽量获取最多的电力,并对用电需求做出反应,比如在大电网用电高峰时为其补输电力。 显然,这个美国目前为止最大的微型电网,也是一个最先进的智能电网。这种分布式能源微电网,虽然在现在还只是作为传统能源大电网的备份补充,但几年之后在某些地区完全可成为传统电网的替代品。因为要想解决当下能源价格高企,以及增加能源开发和利用过程中的安全性和高效性,唯有改变整个的能源系统,掀起一场能源革命。一场既是关于能源自身的革命,也是一场由能源而引发的最后一次工业革命。 能源创新之困 安迪·凯斯勒在自己的著作《我们如何来到现在:商业、技术与金融趣史》的第一句话是:“一切都始于工业革命。”这句话或许需要再延伸一下:一切都始于能源所驱动的工业革命。无论是最初人类用蒸汽机动力炼铁、纺织、运输(蒸汽机车),还是后来在电力大规模广泛应用后掀起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高涨及持续,以及被称为最后一次工业革命的第三次工业革命都与能源相关——无论是能源的开采(生产)、交易,还是应用、创新。 但现在来看,人类与能源的关系似乎陷入了一个怪圈:在最开始,人类拼命地开采、使用能源,赚了很多钱;也就在三、四百年后的现在,人类用之前赚到的钱应对自己当初对能源的过度开采和使用带来的种种危机,弥补错失。与当初人类在发现煤、石油、核动力时的欣喜若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现在的人类苦恼于能源创新,苦恼于如何探索种种新能源。确切地说,真正苦恼于如何探索出一种性价比更合适的、更清洁的电力产生和利用方式。至于究竟是哪种能源产生的,在一些人看来其实并不重要。所以说,人们关心的并不是有哪些类似太阳能、风能新能源出来,而是苦心寻找现有能源电力的生产、利用方式。但这并不容易! 能源及电力网的创新速度远远低于IT、互联网,美国的一些能源创新中心往往都是用10年的时间集中解决一个问题,而创新成果至少需要在50~60年后才能产生影响。另一方面,其所需要投入的研发费用与失效率也高得离谱,“美国国会在授权新能源项目贷款时,就已经知道会有失败,并另会专门划拨出100亿美元来弥补损失。”美国能源部长朱棣文如是说。更有人预计,能源创新资金的失效率普遍会超过90%,“在你投入研发上的金额和你收回的金额之间,没有明确的映射关系,而资金不足还会拖延进展速度。” 实际上,正如我们看到的Santa Rita 监狱的分布式能源应用,能源创新是一项复杂的技术,能源创新之困是技术之困。风能、太阳能电力之所以一直坐在替补席上,根本的原因就是没有解决掉技术难题,比如传输并网、储能等。能源创新需要全球成千上万家的芯片、软件、电力设备、能源开采、储能等众多行业的技术公司参与其中,尝试新技术应用,增加成效率。想想看爱迪生在找到钨丝之前,尝试过多少种材料吧。 能源自身的革命 能源自身的革命是由技术驱动的一场革命。 人类应用电力以来,就习惯了“大集中”。电力靠大发电厂集中生产,然后又靠大电网集中传输,但在最终使用时却是分散的。在分散应用时,根据需求的不同才需要调电压,才需要变电站。这种由生产方来控制需求方的方式,有悖于正常的供应关系,但它之所以一直存在,根结在于人们在煤、石油、水利、核能的开采及电力生产方式一直都是技术密集型的,单独个人或一家一户是做不来的。而风能和太阳能之所以被人们看做新能源来应用,在于其开采、生产方式的技术允许个人、一个家庭来做。 诺伯特·罗尔斯(Norbert Leurs)是德国的一名农夫,他以种马铃薯和养猪维持全家生计。几年前,一家小型风能公司在他的土豆田里竖起了一座70米高的风机。这让罗尔斯在收获土豆的同时,每年还可以得到风能公司6%的电力销售收入,约9500美元。罗尔斯正考虑在田里再多增加2到3台风机,每个都有140米高。不仅如此,罗尔斯还贷款在自家的猪圈、谷仓和房屋顶上都安装了太阳能电池板,生产的电力除了自己用之外,还可以出售给当地的电力部门,这让罗尔斯每年可以赚到28万美元,预计在还清贷款后可以获得200万美元的收入。 最近罗尔斯又得知,美国一家公司正在研究制造一种新型的太阳能电池板薄膜,能使电池板的成本降低一半以上,这就让太阳能发电足可与化石燃料电力竞争。这种新材料能使太阳能电池更有效,生产出更多的电力只需要一定量的材料和设备,同时还能降低安装成本,因为只需要较少的太阳能电池板。 对于自己一直所担心的电池板朝向及采光问题,罗尔斯发现一种解决办法,在每个电池面板上安装一个2美元的微处理器,以此对那些成片的镜子或光电板进行优化,让它们更轻、更可靠,能源效率更高。这些微处理器可以控制面板的朝向,能让每块板都独立地跟踪太阳,以取代过去使用更多钢材、更大的齿轮和齿轮箱的系统。罗尔斯正在考虑换装这种新型电池板。 新技术让罗尔斯这样的家庭实现电力自给自足的同时,还能把多余电力出售出去,让罗尔斯家由以前单纯的电力用户变为用户、电力生产者、利益获得者。所以,现在的关键是要把分散的用户变成生产者,把更多的小型风机、新型太阳能电池板安装在地间地头、房屋屋顶,让每一间房屋、每一栋楼房都成为一个小发电厂——但这还不够!要想将每一大洲的每一栋建筑都转化为微型发电厂,还需要解决智能控制问题。 虚拟“发电站” Santa Rita 监狱微电网的工作原理与IT中的云计算非常类似,把不同的能源电力汇集使用,多余的能源部分被外部电网回收,共享给更多的人来使用,其分布式能源应用的先进之处在于其对微电网电力的生产、利用的控制能力。这个微电网虽然只是一个样本,但却已经掀开能源革命的一角,即用虚拟发电站。 莱茵-鲁尔地区在历史上除了是兵家必争之地,还是德国的重工业区,并且是德国人口密度最高的区域,这里的狂野空地上矗立着风电涡轮机、建筑屋顶上铺盖着太阳能电池板,还有其他一些可再生性的新能源设备。德国四大发电公司之一RWE集团正在通过一套智能软件系统统筹安排该地区各种能源设备的电力输出,实现稳定供电,并获得政府补贴。 依靠这套软件系统,RWE可以控制数量众多的能源设备或分布式储能站,协调它们的电力输出。软件系统会对该区域内的可再生能源发电机组进行数字监控,将它们产生的电力集结在一些,当形成较大的供应量时,再通过计算机进行交易,在能源市场上出售。 这套软件的根本目标就是把区域内数千个单独供电时都不可靠的可再生能源,转换成电力部门可以信赖的巨大网络,一张能源互联网。对于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电力而言,这套系统让它们的电力有能力与天然气、煤炭和核能发电站展开合同竞争。 可以肯定的是,随着人们对大数据处理能力的提高,人们已经可以借助智能化软件系统来计算可用电力供给的详细数据以及对这些信息进行提前预测。这就不需要再为解决太阳能发电站和风力发电场不能提供稳定均匀电力问题,而苦心钻研大规模能源存储技术。 有了这种虚拟电厂,在必要时电力公司可以集结全区域、全国内的所有的储能电池、停靠的电动汽车、家庭用发电机组,以及为大型建筑供电力的大型机组,来制造电力供电。在德国,5%的用电量可通过这种方式解决。 最后一次工业革命 分布式能源得以根本应用,完全在于智能化控制技术的应用。智能化控制技术把微电网、大电网变成了另一种可以传输电力信息的的能源互联网。而在经济学家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看来:当通信革命和能源革命相结合时,就会出现一次新的工业革命。 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18世纪60年代~19世纪40年代),通信技术发生了革命性变化,从手工印刷到蒸汽机动力印刷,后者可以实现低成本大量印制和传播信息,类似今天互联网所实现的变化。于是出现公立学校,大量识字劳动力。这时出现了新的通信系统去管理以煤炭为基础的新能源系统。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19世纪70年代-20世纪初),通信与能源再度携手,集中的电力、电话以及后来的无线电和电视机,可以管理更复杂的石油管道网、汽车路网,进而为城市文化的兴起提供了可能性。里夫金认为,“现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正在死去,以能源为主要支柱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在到来。”里夫金的著作《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提到,第三次工业革命有五个支柱分别是:1.向可再生能源转型;2.以建筑为单位的小型电站;3.扩展到所有基础设施上的能源生产和储存;4.充电式交通系统从互动式电网中获取电能;5.能源互联网。 在这最后一次工业革命中,一些大企业必然要消亡,另外一些要想不“死去”,必须转型。转型的企业要从初级生产(Primary Production)转为聚合者(Aggregator)的角色。 以电力公司为例,他们必然要抛弃掉过去一直所习惯的制造、分配、售卖电力的旧模式。随着数以百万计的个体来自己创造绿色电力,把绿色电力回输到电网,这就迫使电力公司接受一个新现实:我们都在制造新电力,你的角色要怎么调整?你要来怎么经营这个能源互联网? 现在的电力公司应该把角色转变到为中小企业管理绿色电力流(Energy Flows)上来,要降低他们的能源成本,提高热能动力效率。电力公司的客户现在要与其一同分享生产力提升带来的收益。在欧洲,一些电力公司已经在向这个新模式转型,但它们并未放弃旧模式,而是采用两个组合,逐渐抛弃旧的集中模式,让新模式用20~30年时间内逐渐应用起来。 在这最后一次工业革命中,个人、企业、社区都通过能源互联网联系起来,能源互联网可以超越地域局限,实现整个大洲范围内的连接,白天太阳照射的地区把剩余能源分享给已经是黑夜的其他地区,风能、生物能、潮汐的能源也实现分享。最终,提高能源互联网水平方向上的规模效应,进而实现支持整个大洲经济的作用。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