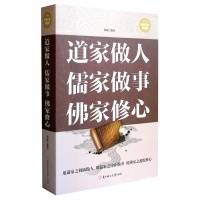十多年前,针对商业伦理这一话题的言论,基本呈现一种批判——辩护模式:一方面,充当“社会的良知”,着眼于社会底层民众和弱势群体利益的人们激烈地抨击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道德沦丧现象;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坚定支持者以及市场经济发展中的既得利益者更多地用“市场经济发展初期”或“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必然付出一些社会代价为由进行辩护。批判者既带着强烈的情感因素,很多时候有意无意地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了市场经济本身,辩护者也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商业伦理这一本题,讨论更多地成了隐性的支持还是反对市场经济的争议,商业伦理问题很多时候变成了论争的手段而非目的,没有得到切实的讨论。
现在,要不要搞市场经济已经不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而近年来,世界范围内若干严重的商业丑闻的暴露,再次激起了人们对商业伦理进行讨论的热情。在中国,商业活动中的败德行为,如欺诈、侵权、不守信、“不按牌理出牌”等等,似乎更加普遍。虽然在当前的工商业界,人们讨论的焦点仍然集中在核心竞争力、渠道、物流、信息化、资本运作等问题上,但诚信缺失带来的交易成本过高等问题也引起了人们相当的重视,建设一个信誉社会以促进经济发展的呼吁不绝于耳;而在思想界和学术界,这样的讨论就更热切一些。商业伦理问题,已经成为一个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市场经济是信誉经济,健康的市场经济环境,需要健全的商业伦理支撑,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对商业伦理的讨论,也已经走向切实并逐步深入。

在中国的文化背景和语境中,谈伦理问题,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儒家思想。儒家的思想体系,本质上是一个政治伦理的体系,两千多年中,儒家思想构筑了中国的社会秩序,也构筑了中国人的伦理意识。至今,儒家思想仍然为中国人的伦理思考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在当前西方不少学者青睐东方传统文化,寄希望于借助东方传统文化救治后现代社会的诸多弊病的背景下,中国倡导儒家思想的声音也变得更加响亮。面对商业活动中败德行为泛滥的现象,不少人希望通过倡导儒家的伦理规范,挽救日下的世风,重树道德秩序。近年来对“儒商”的呼唤,正是这一愿望的一种突出表现。
儒家思想的突出特征之一,是以“礼义”而非“法规”来建构社会秩序,认为以“礼仪”为最高准则建构的社会优于以“法规”建构的社会。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① 明确地区分了二者的优劣,表明了儒者的社会理想和社会取向。
“礼”主要针对社会规范的层面,其核心是对社会地位的象征性表达和展示,目的在于通过种种仪式化的象征性表达和展示,明确界定人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和身份,使社会各阶层的人各安本分,维护社会的稳定。在孔子对管仲的评价中,很突出的表现出了这种观念: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仲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仲而知礼,孰不知礼?”②在这一段评论中,得出管仲“不知礼”的结论的理由,是管仲立了塞门,修了坫台,而这二者,本都是“邦君”才应享用的,带有象征意义。孔子以极其强烈的语气抨击这种行为,“管仲而知礼,孰不知礼?”这种观念,对后代中国产生了极深刻的影响,以后的历朝历代,这种行为可以严重到定为谋反罪,犯者被处以极刑。
“义”主要针对个人修养的层面,其核心是克制自身的欲望以符合“礼”的要求。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③“仁”是精神实质,是“体”;而“义”是“仁”的精神所要求的个人修养和行为准则,“礼”是“仁”的精神所体现的社会规范,二者是“用”。以“礼”为基础建构的社会,要求社会成员安于本分,顺从(对父母的“孝”和对君王的“忠”)和谦让(比如孔融让梨)成为必不可少的美德。对个人欲望的克制,是社会建立“礼”的秩序的根本保障。由此,儒家所倡导的道德标准“义”就和着眼于个体利益的“利”相互对立,“义”和“利”之间的紧张关系,也成了儒家思想家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
在孔子的时代,二者之间的对立和紧张已经表现得相当明显。对于作为社会精英和觉悟者的儒者而言,自觉的修养具有对社会的道义承担的意义,通过“修身”、“齐家”,进而“治国”、“平天下”。为了“天下大同”的最高理想,严格的自我克制不仅有了意义,而且成为崇高,这样的人也因此被称为“君子”。而思想境界达不到“君子”那样的圣徒的高度的人们,不可避免地要追求个人的利益,他们被称为“小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④ 这首先还不是一个对事实的陈述,更是一个道德评价,一种道德法庭的宣判,一褒一贬,一倡导一斥责,旗帜鲜明,毫不含糊。
在孔子的论述中,对个人利益的追求还存在一定的生存空间,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 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⑤
孔子认可人们希望富贵而厌恶贫贱这种欲望的合理性,只是强调君子不能违背“仁”的精神。从行文上看,承认希望富贵这一欲望的合理性,是把它作为强调不能违背“仁”的精神这个主旨的反衬,这本身已经体现出二者之间的紧张关系;从实际经验看,孔子本人就为了自己的理想,从“俸粟六万”、“由大司寇行摄相事”⑥ 的鲁国离去,并且终生颠沛流离,“礼义”的理想追求,始终难与富贵的自然欲望相容。这样的论述,表现出在孔子的观念世界中,“义”和“利”固然对立,却还没有严重到你死我活的程度。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经济的发展,物质世界渐渐能够较多地满足人们地欲求,同时又激起人们更多的欲望。然而,各种社会和经济资源主要操纵在各级官吏手中,人们难于通过合法途径追求个人利益,社会也没有发展起严格细致的法制体系对权力进行有效监控,对“公民”的个人权利进行明确界定和有效保护,甚至根本还没有通行的基于产权的契约观念。在这样的背景下,“义”和“利”之间的对立自然越来越严重,终于,在严肃的思想家的观念世界中,问题尖锐到了这样的程度:或者放弃“礼义”的理想追求,或者彻底否定追求个人利益和物质享受的道德合理性。放弃“礼义”的理想追求,意味着整个中国社会的崩溃或重组,在还不可能拥有一种全新的社会组织方式,能够将人们对个人利益和物质享受的追求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结合起来,不产生根本性的冲突,并且建立一套有效的机制解决必然会存在的矛盾的时候,对于一个严肃的儒家思想家,只能有一种选择。终于,朱熹明确而坚定地判决:存天理,灭人欲。人的欲望和“天理”完全对立起来了,不能“灭人欲”,就无法“存天理”。中国有一句常用语:天理不容,那几乎是对一个人最恶毒的诅咒。
朱熹对儒家思想的改造和发扬,完全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彻底地贯彻了儒家的基本诉求和社会主张,他因此获得了广泛的尊崇,他对儒家经典的解释,成为其后八百年中的经典阐释和官方意识形态。但是,以我们今天的眼光去观照,经过朱熹的改造和发扬,儒家思想变得远离甚至是反对人类的正常生活了,它的道德要求,不是促进了解放和发展人性这一历史前进的必然趋势,而是产生了极大的阻碍作用。它越来越成为中世纪基督教式的教条,并且由于它和帝国的政权紧密结合,成为帝国赖以存在的思想基础,因而变得特别顽固和难以挣脱。三十年前,中国人还在用“狠挖私字一闪念”的集体运动方式希图锻造纯洁的道德;三年前,王海打假再次引起人们的讨论,而讨论的焦点,不是打假取得了多少成就,有过那些失误,还有那些困难,如何打得更准更广,居然是王海打假究竟是出于牟利的目的还是为了维护社会正义;直到现在,商界人士仍然惯用一句“在商言商”,其重要功能之一,乃是规避人们的道德质问;很多贴近生活的思考者,常常有意无意地对“义”、“利”二元对立的道德观念进行颠覆。⑦ 这些现象从正反两方面体现出:那种把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和道德的合理性完全对立起来的思维模式,直到今天还影响着甚至统治着很多中国人的道德直觉和伦理思考。这也正是十多年前在商业伦理的讨论中,商业伦理本身成了台球桌上的母球——用它把别的球撞进袋,自己却不能进袋——的一个重要原因。
九百年前,朱熹由于不可能找到一种新的社会组织方式而以一种近乎殉道的崇高情怀选择了“存天理,灭人欲”。我们比他幸运,今天的市场经济社会,商业社会,正是一个把人们各自追求自身利益和物质享受的行为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结合起来,二者没有根本性的冲突的社会组织方式。建构社会的基础,不再是需要人们“克己”去“复”的“礼”,而是基于产权的契约观念,是对公民个人权利进行明确界定和有效保护、对公共权力进行有效监控的法制体系和法治政治。因此,“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一类道德法庭的判词,已经失去了效力。适应这一现代社会的商业伦理规范,应该建立在契约观念的基础之上。契约观念的淡薄,正是当前商业伦理缺失的思想根源;法制体系的无力,更是败德行为泛滥的直接原因。当前健全商业伦理的要点,也就在于加强法制建设和树立契约观念。要树立契约观念,首先就要彻底颠覆维护社会等级秩序的“礼”和“义”、“利”二元对立的伦理体系和道德思维模式。在这样的背景下,希望祭起“克己复礼”的大旗来拯救道德,恐怕只会带来混乱。儒家的具体主张中,大概还有一个引申来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对今天的商业伦理建设有些意义,不过,又必须对“道”作彻底的重新阐释:它绝不是维护“礼”的那个道,而是……。但是,核心元件完全更换后,还要贴上“儒家”的商标就不太合适,何况市场推广也可能受到影响。
如果一定要说儒家思想至今还鲜活的内容,那就是它思想基础中关注社会人生并且勇于担当的精神,这将是全人类永恒的精神和道德资源。
注释:
① 《论语·为政篇》
② 《论语·八佾篇》③ 《论语·颜渊篇》④ 《论语·里仁篇》⑤ 《论语·里仁篇》⑥ 《史记·孔子世家》⑦ 限于篇幅,难于引用例证。仅举出一篇典型的短论,游宇明《我们遗漏了什么》,见漓江出版社《2002中国年度最佳杂文》。茅于轼先生所著《中国人的道德前景》更是直接针对这一论题的典型文献。参考书目:
1、 《论语》
2、 司马迁《史记》
3、 朱熹《四书集注》
4、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及《万历十五年》
5、 威廉·帕·克莱默《理念与公正》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