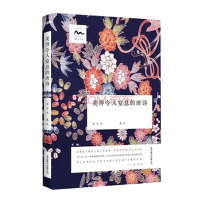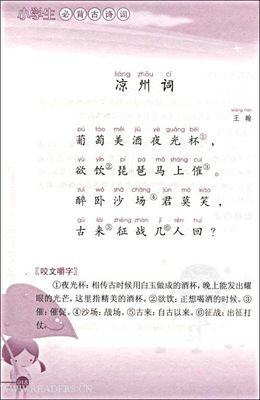前进策略&远景投资 袁岳 郎咸平教授与张维迎教授的隔空交火颇有一些看点,但也深有一些疑点。在我看来,作为两位偏于宏观经济学视角的经济学家,在讨论类似国有企业及企业家作用之类偏于微观的经济学问题时,都有一些明显的盲点。
1.国有企业民营化恐怕势不可挡。这已经不在于理论上国有化与民营化孰利孰弊的问题,而在于今天从政府、银行、国企经理人甚至国企员工已普遍对高度而广泛的国有化不持信心和耐心,在一个众人无心恋战之处仍要人勉力驻留,似乎肯定无利市可期,还不如趁国企未被完全掏空之时及时出手,尚有余值可期,这就是我所说的“瓜趁好时卖”的道理。实际上,国有资产从未如张教授这样的经济学家们所称的那样发生过产权人缺位的问题,而实际上是一个以借助于行政型监管机制难以避免低效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以普世的长期实践证明难以解决,因此除非少量非以政府控制而难保国计民生之需的企业,大家对于实行广泛的 “国进民退”应无异议。

2.转制的公平性。国有企业在本质上是全民资产,需有最低限度的具有政治 性的处置程序,至少由有代议之责的全国人大决议许可,而不应将国有企业转制变成由一个企业的职工、或一个企业之经理人、或某个地方政府部门、或者中央政府就可决定的事项。法定的全民资产转制授权程序既可以解决国有资产处分的合法依据与原则问题,也可以解除当前这种法源不明的政治性处分中产生的不确定法律状况:有的人害怕“国有资产流失”之议,有的人则确实可利用客观上存在的私下交易产生的空间而进行问题交易。
3.公众的话语权。有精英主义倾向的张维迎认为郎咸平是一个公众舆论的迎合者,而且暗示公众舆论并非总是公众利益的适当代表者。问题不在于平民主义与精英注意谁更能代表公众的真实利益,而在于国有资产问题恰是一个与全民有关,每个人乃至每农民也有权置啄的问题,至少是有权了解去向和处分方式的问题。试问,今日已处分或待处分的国有资产的处置过程与模式,有多少面向一般民众的透明度?不错,大众情绪并非总是适宜的,但是大众情绪成为理性的公共意见的前提,是给予公众尽可能多的信息与让公众有充分地了解真相和参与讨论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今天有关国有资产的转型和处分的公开化信息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同样针对国有资产处分的公共讨论不是多了也是少了;而真正大众利益的代言人不是多了而是少了。
今天有一些经济学家自觉或不自觉地试图代表某些利益集团的利益,另一些些经济学家自觉不自觉地试图代表公众的利益,也有一些经济学家的言论显示出他们试图在不同的场合取悦不同的听众而自相矛盾。实际上,在这个利益分化的时代,代表某个特定利益集团的利益是一件正常的事,这种有所分工的公开而沟通性的代表制可以让我们的学者认真专注地从一种明确的立场说清一些方面的道理,并忠诚地为这些道理辩护。相对的,游移地为不同利益集团声言,使得不少学者的论辩显得过于业余、空洞、逢场作戏与情绪化,也常常有伪托超脱与假充公正的道德虚伪嫌疑。
4.企业家角色。郎咸平说到国有企业经理人的职业责任的时候是对的,但也许只是对了一半。的确今天不少国有企业在被赋予经理人经营责任的时候,没有给予相应的对称的酬偿体系,以致不少的国企经理人有强烈的不平感。这种不平感仅仅以责任感类的教训不足以平之。但是仅仅这样的不平,而使其拥有对于产权的主张权利也显得过于简单了。公平的酬偿体系与公开的选聘机制应是解决尚余的国有企业经理人经营角色的基本模式中的两个不能偏废的因素。因为纵使是民营化企业,给予经理人适当的酬偿也是使其能作出积极贡献的基本前提。但是如果支持国有企业经理人具有自然的处置国有企业的优先权,那么将极大地刺激他们设计有利于自己尽快占有国有资产的关联机制的积极性;最终由于他们是最接近与最了解特定国有资产的内部机制者,而使他们相对于其他可能的竞争者具有不当的要挟筹码及不公平的主张能力。
5.不能什么都要民营。在中国,不少公共资源仍具有稀缺性,因此包括国立医院、学校等大众高度需求的公共资源不适合简单地私有化并实行营利化,专业性的非营利托管机制(是公私机制结合的一种管理模式)也许更适合这类事业的发展。在所有的私有化形式中,国有企事业单位经营管理人在担当管理职责的同时,可以另行设立或参与涉及相同和关联业务性质的企业与事业单位(如公立学校校长另设办私立学校,国有纺织企业经理同时可持有私有的纺织企业股份),最具备通过关联交易或资源转移的模式实现不当图利,因此需要明令禁止。
6.国有资产处置模式的精细化。在常规条件下,一个管理健全完善的企业去兼并另一个管理健全的企业,从管理消化与文化融合走向健康经营,通常也具有很大的难度。因此,从国际企业界实践的层面来看,企业的兼并应该是一件审慎而渐进的工作。而在目前的国有资产民营化的过程中发生如此多的管理水平极其有限的民营资本大规模兼并需转制的国有企业的现象,其间固然不乏盲目无知之人,而更大的原因是在国有资产的估值与交易程序上存在极大的瑕疵,从而使得简单的资产转手处置也存在很大的盈利空间,或者相当一些资本运营者通过榨取这类丰厚的资产残值就足以弥补其投入之价,而转制后的企业营运情况是否变为优良还是值得怀疑的。目前一次受到世界银行资助的转制企业实际经营状况的全国性调查正在进行,但大量个案证明,兼并转制与经营好转的正面案例还不够普遍与有力。
7.国有企业经理人的政治角色功能。郎咸平以一般经理人的经营责任期望国有企业经理人也是很有点不公平的。实际上,国有企业经理需要受到诸如市场信号、政策管制与政治信号、意识形态信号和地位特殊的国有企业员工势力的多层控制。他混合有商业政治家、官僚商人的角色。这恰恰也是有必要我支持主张透过普遍的民营化,使得企业家角色趋向简单化的基本原因。国有企业经营人员过去甚少按照一般企业追求市场目标的意识与技能加以训练,所以不少人单纯地恪守政府之规。今天他们在MBA课程或者其他现代管理理念中获得的训练,与他们传统的意识发生了“天人之战”。需知他们的意识进步恰恰导致了他们与进步相对较慢的监管管理机制间更大的反差。公平地说,如果不考虑政治公平性,假定现在让国有企业的管理阶层成为产权人阶层,在保证商业发展与政府财税收入的意义上不见得是一个坏的做法,至少他们将回归为经营目标清晰单一的商人。
8.经济学家的局限性。郎咸平主张之保有国有企业与张维迎的力推民营化其本身各擅有一定道理。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控制机制与转型机制的设计,郎如果提出可行的企业良性控制之道,张如果提出公平的国有资产转型程序,其实就都可以成为更具实质政策价值的操作性主张。而提出这样的一些管理对策恰恰是经济学家的软肋,而扮演业余管理学家的某些经济学家正是用高来高去的经济学议题与非此即彼的制度选择掩盖了他们更该给出的也是人们更期待的管理对策上的无解。在国有企业问题上,我们有理由期待与关注更多的系统的管理技术方案,而不该总是似是而非的制度选择方案。制度选择应辅之以更为详尽成型的管理技术方案,而且即使有了这样的方案,我们还是应首先尝试技术性的解决方案,而不是选择模糊歧议且成本巨大的制度选择方案。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