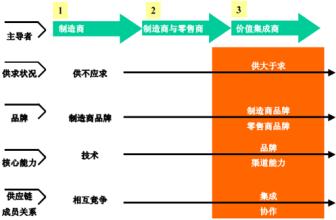我在华润创业做过的生意中,最有感情的是收购和重组大港渤海啤酒厂。收购的最初谈判是在1995年末,我刚好四十岁。作为主管华润中国啤酒生意的执行董事, 93年我刚刚完成对中国第二大啤酒厂—沈阳雪花啤酒厂的收购;95年又完成了同世界第四大啤酒商的合资,组建了华润创业酿造公司;背后有两个有钱的股东撑腰,面对急需资金的中国啤酒业,我像阔佬进菜市场一样,想买啥就买啥,真可谓春风得意。
为完成华润啤酒在中国的扩张,第一战就是要通过收购一间大港的啤酒厂进入大港。我不仅是华润啤酒战略的主要制定者,还是它的执行者。因此,能不能进入大连就是检验我自己行不行。(在此,我奉劝各位老板:你如果能让下属自己出主意,自己订计划,自己去完成; 你的下属就同你一样累了,你的生意就好了)。
大港市里有两间啤酒厂,一间叫大港啤酒厂,年产十三万吨啤酒,占大港80%市场,年年赚钱;另一间叫黄海啤酒厂,年产二万吨啤酒,年年亏损。华润的名气和关系使我顺利同大港市政府取得接触,大港市很痛快的表示可以卖黄海啤酒厂。我闻讯大喜,急赴大港;宾主相见,气氛友好;第二天就看厂并开始谈判。对方的主谈代表是黄海啤酒厂的厂长—李向阳,他的顶头上司是经委主任;经委主任的顶头上司是一位的副市长。我来大港市最初接触的是主任和副市长,我知道他们是幕后的决策人物。
李厂长大我来两岁,同我一样也是下过乡的知青,是个爽快人。我们一开谈就直奔主题—谈谁占大股?谁当总经理?华润创业在中国的合资原则是:华润创业必须占绝对大股,最好100%。当他知道我们必须占绝对大股的原则后,剩下的问题就是谁当总经理?我说:“你当总经理,但当你做不好时,我们有权撤你。”(在此,我想给在中国做合并与收购的同行们一点建议,这个问题是任何交易都不能回避的,不论是多么专业的谈判,多么巧妙的股权设计,不解决这个问题,任何投资都是在沙滩上盖楼,因为中国的文化不是一个尊重资本的文化)。余下的谈判就集中资产评估和债务重组上。于是,第一轮谈判结束,整个过程比较坦诚和顺利。
可是,我按照上次谈判约定的时间要来大港时,老李却推迟同我见面。说:“他们的资产评估工作尚未准备好。” 两个星期过去了,仍未准备好。我知道有事了。急飞大港,求见李厂长。可我在大港的酒店的等了三天,也没见成。想见主任和那位副市长也不好见了。回香港后,我只得请华润集团的头头出面给我疏通大港的关系,结果他们反馈回来的消息是,因为我态度飞扬跋扈,黄海啤酒厂不喜欢同我合作。我蒙了,我是东北人,我知道东北人那种为了掩盖自卑所表现出来的极度自大的脆弱心理;因此,我从香港回东北做生意时,面对我的同类,我时刻提醒自己要加倍谦卑和收敛,见谁恨不得都叫大哥,大爷,怎么还给人飞扬跋扈的印象呢?多亏华润集团的面子,大港方同意恢复谈判。干脆我不出面了,叫一个比我谦虚的人去吧。可主谈的同事,在大港谈了一个星期,回来告诉我,对方根本不想同我们谈,原因是他们想同一个德国啤酒厂合资,并且一个副市长带队去德国考察了。我急了。立即写公函给李厂长,请求他在有竞争者加入的情况下也应给我一个同等竞争的机会。然而,他连我的信也不复了。我只得又通过私人关系去大港市做工作,结果我被告知:德国公司出的价比我的高,德国公司通过很硬的关系找到大港,他们准备用二手设备同黄海合资。我通过商业调查公司马上把这个德国公司的资料查出来,一看竟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我真生气了!我是用真金白银的美元买这个亏损的工厂,还要用真金白银的美元进口新设备,扩大这个工厂,我当然要尽可能把这间工厂的估值压低;而对方是用二手设备投资,他们当然可以把黄海的估值提高,因为他们设备的估值也可以提高,谁都知道二手设备是没有标准价钱的。我和西德人的出价是不能比较的,因为,一个是梨,一个是苹果;一个是黄花姑娘,一个是半老徐娘。可中国的事就是怪,越是常识的事越搞不清楚。对大港市来说,我的方案从任何角度都明显好过对方:引进了新的资金;还了银行贷款;政府甩了一个亏损企业;华润再投入新钱扩大生产,这对大港是多好的事!可我有这么多优势,我还是先谈的;可还没比赛,我竟被一个不是同量级别的对手挤出局?这是什么?这是被人强奸?这件事让我理解了女人被强奸的滋味—吃了亏,想说不好说;不说又难受;说了又怕说不清楚。我他妈是男人呀?男人被强奸的滋味,更难受!我当时已忘了我是在做生意,我只知道我要讨不出个说法,我这一辈子的天都得是阴的。
于是,我上串下跳,动用了所有正式和非正式渠道,试图把局面扭回来。二个月过去了,我明白了,谁都帮不了我了。中间人带回的话都是:这事多难多难。正式渠道的得到的反馈都是:同等条件下会照顾华润的。可我的情报告诉我:对方已与西德人越走越进了。我只能找大港那位全国出名的牛英十市长单独谈,把这个故事讲清楚(我当时没有想如果找牛也解决不了怎么办,后来别人跟我开玩笑说:“你当时就是个秋菊,如果牛市长不解决,你一定会想办法找他爸”) 。在此之前,在正式场合我曾见过几次见牛英十市长。可每次见面人很多,时间也很短;特别是我不能当着他的下属面,告他下属的状。机会来了。我的朋友告诉我:牛英十率团到深圳招商来了,住在哪个酒店,哪个房间。我扔下所有事情,飞车从香港跑到深圳,住进同一间酒店,同一个楼层,守了三天。上天助我!一个非常具有戏剧性的开端,使我有机会单独向牛英十市长陈诉了冤情。

然而,事情的解决远没我想的那样简单。牛英十的直接过问,只不过给了我一个能和对手较量的机会。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让牛市长和他的那些中立幕僚们相信:谁的方案对大港市好?我的对手,可以说是一个人,也可以说是一个政府系统;因为,他们给牛市长关于这个项目的意见,都是以政府部门的名义上报的;他们是牛市长的下属,他们是大港市利益的代表。而我的报告仅代表一个同大港市利益有冲突的唯利是图的外商意见。于是,我必须象一个被告一样,用真诚和友善,同时还不能让对方感到傻,也不能让对方不来台,向那个部门(他是我对手的代表同时也是这件事的裁判)来解释商人的原罪¯¯华润买这个厂不是想卖掉赚钱;华润是有工业啤酒经验的,因为我们的合作伙伴是世界第四大啤酒商;以及这两个方案的区别和我们的优势。尽管我一秒钟也不愿面对这样为官不公,为商不诚的经济官员,但我一分钟也不敢怠慢他们,因为我不想让他们再抓到任何节外生枝的口实。他们被我的死缠烂打软磨硬泡激怒了,行文上都不顾基本的礼貌,表现出恼羞成怒来了。然而,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我们之间的每一份报告和每一次通信,我都抄送给牛市长一份。两个月过去了,牛市长不仅知道了谁的方案好,也知道了谁在里从中捣鬼。
我又一次来到大港,牛市长把我和李厂长请到他的办公室,我开始很奇怪为什么只请李厂长一人,主任呢 副市长呢?他象李厂长表态了:“我很在意同华润的合资,希望你能谈成。”我明白了,牛英十是那种干事一竿子插到底的人。我曾遇到过很多牛英十级别的官,也给他们出过同样的难题,但他们处理问题的手段,大都是不能治病也不死人的标准官僚式的。牛英十是一位能解决问题的官僚,我相信大港市不是因为牛英十不可能有今天的面貌。有人说:“牛英十就知道种花种草搞市容。”我说:“有粉谁不往脸上擦?市长也是人呀!可有人能擦出个大家闺秀,有人怎么捣鼓还是个村姑。”这个项目使我多少明白了,当官不容易,像牛英十这么个强势的官,想改变这么一件小事都这么难。我再一次来大港时,老李带着他的全体领导班子,穿着西服带着领带在火车站迎接我。可我一点没有胜利者的喜悦,心理反而有一丝苦涩。因为,我和老李第一次见面已有六个月了,真正的商业谈判今天才开始;价钱没确定,谁知道后面还会有什么波折?老李把我带到了一个酒馆,然后,让别人都回去了。他端起酒来跟我说:“这六个月,我是里外不是人,成了替罪羊。跟你们谈吧,别人不高兴;不跟你们谈吧,牛市长不高兴;不合资吧,企业活不下去,我这厂长做不成;合资吧,你们不用我,我这厂长也做不下去。反正都是死了,咱们谈吧。”然后,他又告诉我这次市里把谈判的决策权从经委口转到轻工局,局里让他出面谈,但价钱由上头决定。我也端起酒来说:“谢谢,你同我讲真心话。咱们好好谈吧,谈成之后,你还做这间工厂的总经理,只不过你为华润打工了。”然后,我们俩人在半个小时喝了两瓶白酒。我醒来时不知道几点钟,感到浑身疼痛,一看到他在我房间里坐着。我说: “几点了?”他说:“四点了。”我说:“这是什么酒店?”他说:“富丽华,你经常住的。”我说:“我怎么回来地?他说:我把你背回来。我再一看,我的衣服也不是我的了。我问:我的衣服呢?他说:脏了,我给你换了。第一天早上,一照镜子,我发现我象被谁打了一顿。眼也青了,头上还包着纱布。他还在我房间,我说怎么了?”他说:“昨天喝酒时,你去洗手间从楼梯上滑了下去,头磕了一个口子,缝了四针;衣服也全是血,我去商店给你买了一套换上。”睁着青了的眼睛,看着镜子里我那幅残兵败将的样子,我问自己:“值么?”不过从此,我和老李成哥们了。
接下的问题是价钱问题。此时,我明白了,赌徒输得越多越不能收手的心理。价钱的问题解决不了,我的血就会白流。之后的两个月,我同老李,工厂的总会师,局里的总会计师,主管副处长,处长,副局长,局长开过无数次会,吃过无数次饭,喝过无数次酒,已至于我们都开发出我们之间特有的笑话。我又明白了:“国有资产是冰棍,被太阳晒化了,没人理;谁要咬一口,就有人管。”是呀!谁愿意承担把企业便宜的卖给我们的责任?我和我的同事必须象每一个有关人员(怪了!所有人都仅仅是有关?)和每一个有关部门,把企业的资产价值的计算方法先讲清楚;然后再把渤海啤酒的当前净资产告诉他们。然而,一个连年亏损的企业,一个仅有二年的啤酒牌子,他们在账面资产总价1.3亿元之上,竟还要加4千万的商誉。这是我吃不下去的毒果,这是我的股东不能接受的价钱,也会让同行笑掉大牙的交易。可是他们有国有资产管理局的评估,如果低过这个评估,就是牛英十也不敢卖!这个评估合不合理,只有专业人员才能说得清。本来专业人员之间的对话应是专业和平等的,可因为对方是国有资产管理局的专业人员,在他听完我们的商誉计算方法后,竟可以对我们的专业人员说:“我们的商誉计算方法,是国家机密,无可奉告。”然而,这令人嘡目结舌的无可奉告竟帮了我的大忙,因为它使得在场的大港官员们知道了我的价钱是合理的。再不接受我的方案有点“实在说不过去了。我赢了!赢的真惨!靠的是别人的同情和可怜!最后,究竟是谁拍的板,同意了我的价钱,到现在我也搞不清楚。反正是轻工局长正式通知我:可以起草文件了。看,这就是国有资产的毛病¯你永远不知道谁是它的真正老板。
前后十个月,一波三折,暗涛涌涌,峰回路转,柳暗花明我终于拿下了大港渤海啤酒厂。这是我独立负责完成的第一个收购项目,是在所有人都看不到希望,所有人都束手无策时,命运帮助我把它做成。它是我的私生子。在生它的过程中,我完成了对中国商人的思考---三陪小姐。我只不过是在一个众多三陪小姐中做得更忘我的一个罢了,醉酒了,一不小心了怀了个孩子。
但私生子也是孩子,我必须把他养大。
未完待续,黄铁鹰 2002年7月28日 墨尔本。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