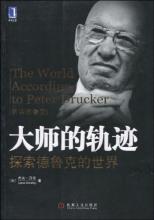第三章 新的挑战管理热潮及其思想基础——基础领域中对新知识为需要——生产率的需要——超越分权化——对新模式的需要——从人事管理到对人的领导——新的需求——企业家式的管理人员——多机构的管理——知识与知识劳动者——多国与多文化的管理——管理与生活的质量——管理的新作用
管理热潮在思想上的有七点::(1)作为提高劳动生产率关键因素的工作的科学管理;(2)作为基本组织原则的分权化原则;(3)作为使人适合于组织结构的正常方法的人事管理(包括作业说明、职工考评、工薪管理及“人际关系”);(4)在目前为今后的管理需要培训管理人员;(5)管理会计,即应用分析和情报作为管理决策的依据;(6)市场推销;(7)长期规划。
上述七点中的每一点都在管理热潮出现以前就已成功地在实行(正如在上一章结尾部分“附记:管理的根源和历史”一节中所阐述的)。换句话说,管理热潮只不过使之得以改进。、补充、修订,而很少创新。它使得到那时为止只是少数专家的神秘知识的东西成为各地的管理人员都能掌握的知识,使得到那时只是少数例外的事物成为普遍的实践。基础领域中对新知识的需要
在六十年代末或七十年代初,人们已清楚地看出,管理热潮作为依据的那些知识已经不够了。在绝大多数基础领域中都产生了对新知识的需要,特别是有关生产率、组织设计和结构、对人的管理等领域。科学管理再也不能使生产率进一步提高。在每一个国家都存在着由于严重的通货膨胀而产生的生产率危机。回想起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时期在西欧和日本出现的生产率的巨幅增长,部分地是由于管理改进的结果。主要的因素是,很大数量的入从西西里、西班牙、日本北部山区这样一些低生产率的勉强生存的农业区迁移到了高生产率的工业区。如果没有这种大规模的移民,这些成长地区的生产率的提高可能只是微不足道的。但这种迁移浪潮已经过去了。西欧显然已经达到了它吸收外来工人能力的极限。在日本,处于那种勉强生活的农业人口已不多了。从今以后,这些国家的生产率的提高必须依靠现有工人在现有工作上提高生产率来达到。与此同时,对经济成长的需求却提高了,而这种经济成长只有通过生产率的提高才能实现。例如,每一个人都“了解”(许多人现在仍然认为),丰裕将会大大降低对经济成长的需求。一旦我们知道了如何生产物质财富,社会经济函数中的需求肯定就会减少。而事实上我们却面对着人们的期望日益增长的浪潮。当肯尼迪总统在六十年代早期提出丰裕这个词时,他脑子里想到的是在世界上贫穷的、不发达的国家中对经济报酬和满足的需求会有爆炸性的增长。但是,丰裕也使得发达国家中仍然贫穷的那些人(不论是美国的黑人还是西西里的农民),在人们的期望方面产生了同样的增长浪潮。而丰裕本身对经济成长的需求却快于它们自己所能达到的能力。同大众性报纸上头条新闻所讲的相反,受过教育的青年人没有显示出什么迹象,他们会减少对传统的经济商品和服务的需求(虽然被叫做“思格尔定律”的传统经济理论曾经预言会有这种减少)。此外,他们还对新的服务和新的满足——教育、保健、住房、闲暇——表现出众不满足的胃口。同样是新的、也许是更费钱的一种需求是清洁的环境。从今天来看,它简直是一种奢侈。昨天,在城市贫民窟和农村小屋中,人们能够享受到清洁的空气、清洁的街道、安全的饮水、卫生而未被污染的食物,现在,这些只是一种梦想。这些新的期望和需求中的每一种都需要做出巨大的经济努力,每一项都需要动用大量的经济资源。尤其重要的是,其中每一项都要求经济有前所未有的经济剩余。换句话说,要满足这些需求,就要求生产率有很大的提高。我们知道所需要的是些什么。首先,传统的观点只集中注意于生产率的一个因素:劳动。但是,生产率是生产的全部三个因素——土地、劳动、资本——平衡发展的结果。即使从劳动力的生产率来讲,我们也只是进行了第一步:对工作的各个片断进行了分析。我们需要了解生产的原则,以便把工作结合成为最有生产率的生产过程。我们还需要把工作和工人的极不相同的要求和逻辑加以协调。超越分权化
分权化在它适应的地方是最好的组织设计原则。但其应用的条件都是相当苛刻的。它适用于原先设计得拥有不同的产品线来满足不同市场的制造业。它不能完善地或恰当地适用于非制造业。它也不能适用于那些市场无限重叠、用相同的生产过程生产各种不同产品的加工制造业(如制铝业或制钢业)。我们还知道,对于正在进行中的企业的经营工作,分权化是一种最好的原则。但它并不能满足创新工作的组织需求。对于组织高层管理的工作,就它本身来讲也是不够的。我们出于以往的经验而在寻找一些新的——迄今主要仍是试验性的——组织设计原则:工作任务小组、模拟性分权化、系统组织。它们迄今还远不能令人满意,但它们的出现充分表明对于新的组织模式的巨大需要。我们知道,管理热潮使之普遍化的那种组织模式只是一种特殊的模式,而且事实上已经不是占统治地位的一种模式。管理热潮在一切领域所依据的都是制造业公司中所做的工作。这种制造业公司基本上只制造一种产品或拥有一条产品线,在一个国家的市场内经营、雇佣的主要是手工劳动。换句话说,其模式是通用汽车公司。但是,被管理和组织的占统治地位的机构,即使在工商领域中,也愈来愈不是制造业公司,不是只在一个国家或一个市场中经营的单一产品的公司,不是主要雇佣手工劳动的公司。它们是服务行业的企业——银行或零售企业——以及医院和大学等非工商业机构。它们是多种产品、多种工艺技术、多个市场的企业。它们是多国企业。而且,中心的人力资源已日益不是手工劳动者——熟练工人或非熟练工人,而是知识劳动者:公司的总经理,但也包括计算机程序员、工程师、医疗技术人员、医院院长、销售员和成本会计师、教师,以及整个被雇佣的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这些人在每一个发达国家中都已成了人口的中心。换句话说,昨天的模式已日益不适用,但我们迄今还没有一种新的模式。从人事管理到对人的领导
最后,我们还知道,我们必须超越人事管理。我们必须学会对人们进行领导而不是加以限制。我们传统方法不外包含三种成分:一是慈善家式的,对那些不能照料自己的人,照顾他们的需要、住房、保健、福利;另外一种成分是照章办事的,用日常方式来处理经常重复发生的与雇用有关的问题;最后一种成分,也是占主要地位的,是防止和解决发生的麻烦。最重要的是,他们把人看成是一种潜在的威胁。传统的方法是需要的,但它们是不够的。除此之外,我们必须把人看成是资源和机会,而不是问题、负担和威胁.我们必须学会领导而不是管制,引导而不是控制。新的需求
当老的方法和老的知识,在重要的领域中已经陈旧时,在全新的领域中出现了各种需求。这些新的领域在管理热潮开始时只有很少的人有所预测,根本谈不上对其作什么研究。管理热潮作为依据的某些基本假设——过去——一个世纪中管理工作以此为依据的一些假设——由于新的发展需要新的视野、新的工作和新的知识而开始受到人们的怀疑。企业家式的管理人员
在一个世纪的四分之三的时间里,管理主要意味着对已经建立起来的、继续进行中的企业进行管理。企业家精神和创新思想虽然被许多管理书籍提到过,但从1900年到现在并未被看成是中心的项目。从今以后,企业管理除了使现有的事物最优化以外,必须日益重视创新的工作。管理人员必须成为企业家,必须学会建立和管理创新的组织。我们面临着创新的时期,正好像现代工业诞生的十九世纪下半叶那个时期那样。在那个时期,在美国内战结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五十年中,平均每十五个月或十八个月就有一项新的重大发明出现。每一项重大发明都引出新的企业和全新的产业部门。事实上,我们目前认为是“现代的”所有产业部门,包括飞机制造业和电子工业.都是从十九世纪后期到二十世纪早期的这些重大发明中产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重建时期所取得的经济增长,主要得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已得到充分发展的工艺技术,以及以这些工艺技术为基础的四大产业部门:钢铁工业、汽车工业、科学的农业以及有机化学。目前我们又面临着另一次重大的工艺技术变革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经济和工业发展的猛力推进将来自以新的、二十世纪的工艺技术为基础的产业部门及其发展。同十九世纪后期形成尖锐对比的是,这一次,新工艺技术的大多数将在现有的企业中产生,并应用于现有企业之中。在十九世纪后期,主要是发明家个人在发明:一个西门士、一个诺贝尔、一个爱迪生、一个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A1exander Graham Bell),都是一个人独自工作,至多有一些助手。 在那个时候,成功地把一项发明付之应用很快地就形成了一个新的企业。但并不是企业产生新的发明。而在目前,预期将做出创新的将愈来愈是现存的企业,常常是大企业——简单的原因是,创新所需要的有训练的人和资金都在现存企业、通常是大企业中。所以,管理当局必须学会在经营一个现存的组织的同时,还要经营一个新的、创新的组织。对社会方面创新的需要甚至可能比对技术方面创新的需要更大。社会方面的创新对社会和经济的变革和发展所起的作用,同技术方面的创新所起的作用一样大。我们社会的各种需要——世界上三分之二的贫穷地区在社会和经济上迅速发展的需要、我们大城市中的各种需要、环境方面的各种需要、教育和卫生保健方面的各种需要——这些都是企业和企业的管理人员在社会创新方面的各种机会。它们对于企业家来讲是各种机会,从而对企业管理当局的知识、技巧和成就提出了挑战和要求。多机构的管理
管理热潮是一个工商企业管理的热潮,而上一世纪的绝大多数管理工作都集中于对工商企业进行管理。但是,现在我们知道,我们的所有机构都需要管理。这种观点在几年以前还会被认为是一种奇谈怪论(目前在英国和法国的许多企业和服务机构中的管理人员还是这样认为的)。在以前,经营一家企业同管理一个公共服务机构(如一家医院)被看成是大不相同的。一个机构的使命和目标的确有着根本的不同。如果为了纠正一个公共服务机构的毛病而企图使它“象企业一样地”来进行管理,那是极为不妥当的(对此,见第十一章到第十四章)。但是,一家投资金融公司的管理也不同于一家钢铁厂或一家百货公司的管理。而且,公共服务机构的管理人员同一家企业的管理人员面对着同样的一些任务:执行这个机构之所以存在的一些职能;使工作有生产性而且职工有成就;控制本机构对社会的冲击并承担其社会责任。这些都是管理的任务。公共服务机构也同样地面对着创新的挑战,并且必须掌握其成长、多角化和复杂化。而且我们已了解到,并且在前面已经讲过,管理的中心需要就是,使一个非工商业的机构、服务性机构能够进行管理,并能管理得有成效。知识与知识劳动者
发达国家中今后数十年内的主要管理任务就是要使知识具有生产性。体力劳动者已是过去的劳动者—我们在这条战线上所能进行的全部战斗只是一种后卫战。一个发达经济的基本资本资源、基本投资、但同时也是成本中心的是知识劳动者。这种知识劳动者投入工作的是他在系统的教育中所学得的东西,即概念、思想和理论,而不是他的体力技能或筋肉。泰罗把知识投入工作,以便使体力劳动者更有生产力。他的工业工程师是制造过程中所雇佣的第一批知识劳动者。但是泰罗自己从来没有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应用“科学管理”的工业工程师的“生产率”是由什么构成的?由于泰罗的工作的结果,我们可以确定体力劳动者的生产率是什么,但是我们还不能回答工业工程师或其他任何知识劳动者的生产率是什么这一问题。使我们知道体力劳动者的生产率的那些量度,如每小时或每元工资所生产产品的件数,如果用于知识劳动者,是完全不合适的。如果一个工程部门以很快的速度、很大的勤奋和很漂亮的形式绘制出一些销售不出去的产品的图纸,那么可以说再没有比这更为无用和无生产性的事了。换句话说,知识劳动者的生产率主要是质量。有一件事是很清楚的:使知识具有生产性将给职务结构、职业途径和组织带来急剧的变革,正好像在工厂中采用科学管理对体力劳动所带来的急剧变革一样。入门的职位——就是使受过正规高等教育的青年人进入工作和实践的成人世界的职位——必将有急剧的变革,才能使知识劳动者成为有生产性的。.因为,十分清楚,如果知识劳动者不能了解他自己,了解他适合于什么工作,他怎样才能工作得最好,知识就不能成为有生产性的。在知识工作中,设计和执行不可能分开。相反的,知识劳动者必须能够自己进行计划。目前的入门职位一般不能做到达一点。它们是以下述假设为依据的,即工业工程师或工作研究专家这样的高级专家可以客观地制定一种完成任一工作的最好方法。这种假设对于体力工作来说,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的,而对知识工作则完全不能适用,完全是错误的。也可能存在着一种最好的方法,但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个人。它并不完全由工作的生理特点、甚或心理特点来决定。它也是与个人气质有关的。多日与多文化的管理
存在着一种使工商企业的管理成为多国管理的需要。从经济上说,世界特别是发达的世界已经成为一个市场。而不发达的贫穷困家同发达国家的差别仅在于它们没有能力提供它们愿意有的那些东西。,不论世界在政治上可能怎样划分,从其需求、胃口、经济价值观方面来讲,整个世界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购买中心。多国企业使生产性资源、市场机会和有才能的人超出国界而得以最好地利用。所以,它是对当前经济现实的一种正常的、事实上是必需的反应。但是,所有这些发展却给管理带来了前人没有遇到过的各种复杂性。因为,管理同时也是一种文化和一种价值观及信念的系统。它也是某一社会使其自己的价值观和信念成为生产性的一种手段。管理可以看成是一种桥梁,它连结着正在迅速成为世界性的文明和表现着不同传统、价值观、信念及遗产的文化。管理必须成为一种能使文化上的差异为人类的共同目标服务的工具。与此同时,管理已日益不是在一个国家的文化、法律或主权的范围内进行,而是多国化了。事实上,管理正在成为一种真正的世界经济的一个机构——迄今几乎是唯一的机构。我们现在知道,管理必须使个人、社团和社会的价值观、志向和传统为了一个共同的生产目标而成为生产性的。如果管理不能成功地使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特殊的文化遗产发挥作用,那么社会和经济发展就不可能实现。这当然是日本的伟大经验——而日本在一个世纪以前就能设法做到使其社会的传统和人的价值观为一个现代的工业化国家的新目标服务这一事实就表明了,为什么日本成功了,而所有其它的非西方国家到目前为止都失败了。管理必须看成既是一种科学,又是一种人性;既是一种能加以客观验证的各种发现的陈述,又是一种信念和经验的体系。在个别国家中,特别是在发达国家中,工商企业已经迅速地失去其作为典型的、普遍的、社会的代表形式的特殊地位;组织起来的机构也要求进行管理。但是,超越了国界,工商企业却正在迅速地取得它在个别的发达国家中已经不存在的那种特殊地位。超越了国界,工商企业正在迅速地取得这种特殊地位,成为表现一个世界性经济和世界性知识社会的现实的一种机构。我们需要学习如何使超越国界的、即在一个共同的世界经济中对管理统一性的需要,同文化上多样性的需要这两者在一个机构和一种管理中协调起来。管理与生活的质量
由于我们的社会正在迅速地成为一个由各种组织构成的社会,所有各种机构,其中包括工商企业,都必须对生活的质量负起责任来,必须把实现基本的社会价值、信念和目标作为它们每日正常活动的一项主要目标,而不把它看成是在它们正常主要职能之外并加以限制的一种社会责任。各种机构必须学会使生活的质量同它们的主要任务相一致。就工商企业来讲,这就意味首要把提高生活的质量看成是能经由经营管理而转变成盈利性企业的一种机会。这也日益适用于个人愿望的满足上。目前我们可见的最具体的社会环境就是组织。家庭是私人的而不是公共的——这当然并不是讲它不重要。社区正日益地纳入于组织之中.管理的任务就在于使个人的价值观和志向转化为组织的力量和成就。如果象工业关系理论甚至人际关系理论传统地认为的那样,仅仅限于使人满足,即没有什么不满,那显然是不够的。一种形象化的说法也许是,在今后十年内,我们将更少关心于使个人适应于组织需要的管理人员培训,而更多关心使组织适应于个人的需要、志向和潜力的管理发展。我们也知道,管理带来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经济和社会发展是管理的结果。在一百年以前,从每一种物质度量标准来看,日本是一个不发达的国家。但是,日本很快就产生了有伟大能力、的确是很出色的管理。明治时期的日本在二十五年内就成为一个发达国家了,而在某些方面,如在识字教育方面,成为所有国家中最发达的了。我们现在认识到,应该成为不够发达的世界的发展模式的不应该是经济学家提出的传统的模式——十八世纪的英国或十九世纪的德国,而应该是明治时期的日本。任何地方,如果我们只是提供生产的经济要素、特别是资本,我们就不能取得发展。在产生了管理力量的少数例子中,都取得了迅速的发展。换句话说,与发展有关的是一种人的力量而不是经济的财富。而人的力量的产生和指引却是管理的任务。管理是动力,而发展是结果。但是,比新任务更重要的是管理的新作用。管理正在迅速地成为发达国家的中心资源和发展中国家的基本需要。管理和管理人员正在从工商企业即社会经济机构所特别关心的事物变成发达社会的特别器官。管理的状况和管理人员的作为因而将日益成为——这是完全正当的——一个为公众关心的事情,而不只是一个只为专家所关心的事情。管理将如同它关心可衡量的成果那样,日益关心基本信念和价值观的表现。管理将如同它努力于提高生活水平一样,将日益努力于提高生活的质量。我们必须学会运用的有许多新的管理工具,以及新的技术。存在着许多新的、艰巨的任务。但是,管理的最大变革是,发达国家中社会的志向、价值现以至其生存都将取决于其管理人员的成就、能力、热忱和价值观。下一代人的任务是使我们新多元社会中的新组织机构为了个人、社区和社会而更有生产性。这首先是管理的任务。附记:管理的根源及历史近来有些管理学的作者似乎认为是管理热潮发明了管理,或者至少是发现了管理。这当然是无稽之谈。作为一种实践和一个思考与研究的领域,管理都已经有了很长的历史,其根源几乎可以追溯到二百年以前。人们可以说,早在人们谈论管理以前,管理就已经被发现了。一些伟大的英国经济学家,从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到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1772—1823),到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包括他们的继承者和反对者卡尔·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都不知道什么管理。对他们来讲,经济是不具人格和客观性的。正如古典传统的当代解释者、英裔美国人肯尼思·博尔丁(Kenneth Boulding,生于1910年)所说的,“经济学所探讨的是商品的行为,而不是人的行为。”或者,像马克思所认为的,占统治地位的是非人格的历史规律,人只能适应。人在最好的情况下只能充分利用经济所提供的可能性,而在最坏的情况下却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并浪费资源。最后一位伟大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艾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842—1924)的确把管理加到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些生产因素中去。但这只是一种并非出于衷心的让步。即使对于马歇尔来讲,管理也只是一种外在的因素,而不是中心的因素。但是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另外一种不同的态度,即把管理人员置于经济的中心,并强调管理工作能使资源得到更好的利用。赛伊(J.B.Say,1767—1832)也许是法国和欧洲大陆所产生的最有才华的经济学家。他是亚当·斯密的早期追随者,并且是《国富论》在法国的宣传者。但在他自己的著作中所研究的中心却不是生产因素,而是一个他自己创造出来的名词——企业家。企业家把资源从生产率较低的投资引向生产率较高的投资,从而创造了财富。追随赛伊的有法国传统的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特别是弗兰索瓦·傅立叶(Francois Fourier,1772—1837)和那位古怪的天才圣西门(Comte de Saint Simon,1760—1825)。虽然在当时还不存在着大企业和经理,傅立叶和圣西门却都在管理已实际存在以前就预见到了其发展并“发现”了管理。圣西门特别预见到了企业的兴起,使资源更有生产率的任务,以及社会结构的建立。他预见到了管理的任务。正是由于他们强调管理是一种独立而不同的力量,是一种能够独立于生产因素和历史规律而发生作用的力量,马克思才竭力地批评这些法国人并讽刺他们是“空想主义者”。但是,正是这些法国人——特别是圣西门——实际上建立了每一种社会主义经济赖以设计的基本概念和方法。不论俄国人今天多么推崇马克思的名字,他们精神上的先驱却是圣西门。管理在美国也早就被看成是一种中心因素。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1757—1804)在其有名的《有关制造业的报告》中,开始是按照亚当·斯密的观点,但接着他就强调管理的建设性的、有目的的、系统性的作用。他把管理而不是经济力量看成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动力,而企业则是经济进步的承担者。在他之后,亨利·克莱(Henry C1ay,1777—1852)在其有名的《美国系统》中提出了可以叫做系统化的经济发展的最初蓝图。稍迟一些,苏格兰的一位实业家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1771—1858)成为第一位实际上的经理。欧文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在其拉那克的纺织厂中首先着手解决生产率和激励、工人同工作的关系、工人同企业的关系,以及工人同管理当局的关系等问题——这些问题至今仍是管理中的关键问题。在欧文身上,经理作为一个真实的人而出现,不象在赛伊、傅立叶、圣西门、汉密尔顿、克莱那里那样,只是一种抽象的概念。但是,欧文之后很久才出现了他的继承者。大型组织的兴起
首先发生的是大型组织的兴起。它是同时——约在1870年左右——在两个地方兴起的。在北美,横跨大陆的铁路成为一个管理上的问题;而在欧洲大陆,那些具有企业性目标、全国性范围、多个总部的“通用银行”使得传统的结构和观念无法适用而需要进行管理。
反应之一来自美国的亨利·汤(Henry Towne,1844—1924),特别是在《作为经济学家的工程师》这篇论文中,汤提出了可以称之为第一份的管理计划。他提出的基本问题有:效率与效果、工作的组织与工厂中的社会组织即工人的组织、市场中决定的即消费者决定的价值与技术上的成就等。从汤开始,人们开始系统地关心管理的任务和管理的工作之期的相互关系。大约与此同时,德国的乔治·西门士(George Siemens,1839—1901)在把德意志银行建设成为欧洲大陆首屈一指的金融机构的过程中,首先设计出了一个有效的高层管理机构,首先深入思考高层管理的任务,并首先着手解决大型组织中的信息交流和情报等基本问题(关于西门士,见第四十九章)。在日本,由明治时期的政治家转变为企业领导者的涩泽荣一(1840—1931)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首先提出了工商企业同国家利益的关系、企业需要同个人道德的关系等基本问题。他着手系统地解决管理教育问题。他首先意识到了专业管理人员的出现。日本在本世纪能在经济上处于领先地位,大部分是由于涩泽荣一的思想和工作为之打下了基础。数十年后,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现代管理的所有主要观点都已形成。而这些也都是在许多国家中独立地形成的。弗雷德里克·W·泰罗(Frederick W.Taylor,1856—1915)这位自学成才的美国工程师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对工人的工作进行研究。目前,贬低泰罗并批评他那套过时的心理学已成为一种时髦。但泰罗是人类有史以来不把人的工作看成是理所当然而对之进行考察和研究的第一个人。他对工作进行研究的方法至今仍是一种基础(对此见第十七章)。泰罗虽然明显地是以一个十九世纪的人来对待工人的,但他却是从社会的观点,而不是从工程或获利的观点出发的。使泰罗从事其工作并激励他坚持下去的,首先是一种要把工人从繁重的劳动和身心的伤害中解脱出来的愿望。此外,他还希望能打破古典经济学家(包括马克思)的工资铁律。这种工资铁律宣称工人在经济上的没有保证和长期的贫困是不可避免的。泰罗的希望是,通过提高劳动的生产率能够使工人享有更好的生活。而泰罗的这一希望在各个发达国家中已大致成为事实。大约在这同一期间,法国当时已算很大的一家煤矿公司的领导人亨利·法约尔(Henri Fayol,1841—1925)首先深入思考了组织结构的问题,并首先提出了企业组织的合理方法、职能性原则。在德国,沃尔特·拉特淄(Walter Rathenau,1867—1922)早期是在一家大公司中接受的训练。这家公司就是相当于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的德国通用电气公司。这家公司是沃尔特的父亲埃米尔(Emil1838—1915)首先建立起来的,但其发展大部分是在乔治·西门士的监督之下进行的。沃尔特·拉特淄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大企业在现代社会和现代国家中处于怎样的一种地位?它对后两者有些什么影响?它的基本贡献和基本责任是什么?”目前绝大多数有关企业的社会责任的问题已由拉特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年代中首先提出来并思考过了。与此同时,也是在德国,尤金·施马伦巴赫(Eugen Schmalenbach,1873——1955)这样的一些人建立了一门“经营学”的新学科。以后发展起来的一些管理学科,如管理会计、运筹学、决策论等。大部分只是(虽然人们并没有意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年代的“经营学”的进一步扩展。而在美国,出生于德国的雨果·芒斯特伯(Hugo Muensterberg,1863—1916)首先试图把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特别是心理学应用于现代组织和管理。
第一次管理热潮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了所谓第一次管理热潮。它主要是由当时深受尊敬的两位政治家引起的,即美国的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1874—1964)和捷克的托马斯·马萨里克(Thomas J.Masary K,1850—1937)。胡佛这位教友派工程师之所以在全世界出名,是由于他把管理的各项原则应用于历史上第一次的大规模外援活动:救济成千上万的饥民——首先,在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在比利时救济活动中;然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中欧和东欧的救济活动中。但是,提出能用管理来恢复欧洲遭受战争破坏的经济的思想者却是马萨里克这位历史学家,他成了新成立的捷克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过了二十五年,马萨里克的这一思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马歇尔计划中得到了实现。这两个人奠定了国际管理运动的基础并试图把管理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力量来加以动员。但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期间却没有出现类似的思想,这是一个停滞的期间。在此期间,任何一国的政府或任何一种经济(除了美国以外)所能想象的最高目标就是恢复到战前状况,即恢复到原有水平。日益增长的政治上、社会上和经济上的紧张状态很快就使世界在意志和远见上都麻痹起来了.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努力
第一次管理热潮烟消云散了。崇高的希望变成了失望。但是,在表面的停滞之下仍有人在继续努力。正是在这些年代,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风起云涌的管理热潮打下了基础。二十年代早期,杜邦公司的皮埃尔·杜邦(P1erre S.Du Pont,1870—1954)及以后的通用汽车公司的艾尔弗雷德·斯隆(1875—1966)首先为新的“大企业”提出了一种组织原则——分权的原则。杜邦,尤其是斯隆还首先提出了企业目标、企业战略、战略规划的系统方法。也是在美国,首先在朱列叶斯·罗森沃德(Julius Rosenwald,1862—1932)领导之下,以后在罗伯特·伍德(Robert E.Wood,1879—1969)领导之下,西尔—罗贝克公司首先建立起了一种以市场推销为基础的企业。稍迟一些,欧洲的英、荷两国的公司合并组成了尤尼莱佛公司,并为多国公司设计出了一套直到目前还是最先进的结构,并着手处理多国公司的计划和销售等问题。管理学科也进一步发展了。在美国出现了泰罗的一些继承者,弗兰克·吉尔布雷思(Frank Gilbretk,1868—1924)与莉莲·吉尔布雷思(Lillian Gilbreth,1878—1972)夫妇和亨利·甘恃(Henry Gantt,1861—1919)。在美国,伊恩·哈密尔顿(1an Hamilton,1853—1947)基于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军官的经验,认识到必须在正式结构和赋予组织以“灵魂”的政策之间取得平衡。两位美国人,玛丽·派克·福莱特(Mary Parker Follett,1868——1933)和切斯特·巴纳德(Cheste Barnard,1886—1961)首先对组织中的决策过程、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的关系,以及经理人员的作用和职能进行了研究。英国的西里尔·伯特(Cyril Burt,1883—1972)和在美国哈佛大学工作的澳大利亚人埃尔顿·梅奥(E1tonMayo,1880—1949)分别发展了工业心理学和人际关系理论,并把它们应用于企业和管理。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里,管理作为一门学科开始被讲授。哈佛工商学院在三十年代第一次开设管理方面的课程——虽然主要仍属于生产管理的领域。而麻省理工学院则在同一时期开始对年青的经理人员进行高级管理训练。美国人詹姆斯·麦金赛(James Mckinsey,1889—1937)和英国人林戴尔·厄威克(Lyndall F.Urwick,生于1891年)开始从事管理咨询工作,即不限于在技术问题上进行咨询,而是处理有关企业政策和管理组织这样一些基本的管理问题。厄威克还把到那时为止的组织结构和经理人员的职能作了分类整理。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