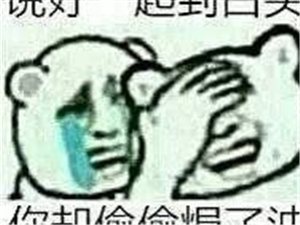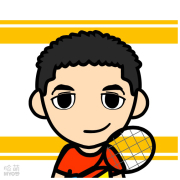我国的自然村十年间由360万个,锐减到只剩270万个。这意味着,每一天中国都有80个到100个村庄消失。这个消息引起轩然大波,很多人都在为村庄的消失而惋惜。 这则消息,本是民俗学家、作家冯骥才从有关方面获悉并透露的。作为民俗学家,冯骥才当然非常留恋充满田园牧歌情调的村庄民情风俗,他对于村庄的消失多有惋惜之情,可以理解。但是,乡村变迁,情况不尽相同,有些是农民自愿选择的结果,有些则是地方征地或其他手段引导造成的,具体情况需要具体对待和评价。 一些村庄的消失,是政府行为造成的。比如城市扩张,占地拆迁,一些村庄被拆除了。农民转化为市民,可是难于就业,也难于融入城市,形成一系列问题;另外,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农民进城,强行裁撤农村小学,迫使农民带孩子进城读书打工。这种情况也造成农村孩子上学难等问题。由于政府政策导致的村庄的消失,有利有弊,不可一概而论。 而更多村庄的消失,其实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是广大农民自我选择的结果。无论从媒体的报道,还是笔者的调查都证明,农村大量年富力强的劳动者,到城市打工挣钱的收入,数倍于种田务农的收入。他们进入城市打工,不但能够多赚钱,而且能够接触在农村所无法想象的现代生活。他们不愿意再回到单调的、寂寞的农村,从事繁重而低收益的农作,宁愿挈妇将雏在城里租房或买房,争取成为城市居民,过上与祖辈不同的生活。显然,这种选择,这种选择带来的村庄的消失,并不是什么值得惋惜的坏事,恰恰相反,倒是一个值得称道的历史进步。 在中国历史上,甚至在近二十年前,中国农民绝没有根据自己的意愿和努力而摆脱农民身份,自由迁徙进入城市的权利。历史上,中国实行“重农抑商”“重本抑末”的政策,为了使此政策能够落到实处,政府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禁止农民改换职业,禁止农民自由迁徙,禁止农民进入城市。 中国传统上是农业社会,但在历史上,一旦有长期的和平,农村一定会出现劳动力的剩余和农产品的剩余。劳动力的剩余必然迫使农民改变职业身份,从事工商业,离开乡村进入城市;而产品的剩余,必然会促进产品的交换,带动贸易,促进商业流通和繁荣。比如在汉朝时期,曾经不断出现农民放弃农业生产而从事工商业(所谓末业),促进工商业繁荣发展的现象。而对于这种现象,思想家如贾谊、晁错等都大声疾呼,要求重农抑商,“殴民归农”。如贾谊建议皇帝重视积贮,说:“今殴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于南亩,则蓄积足而人乐其所矣!”晁错也说,“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 ,犹不能禁也”。与贾谊要求“殴民归农”不同的是,晁错建议建议皇帝“入粟拜爵”,就是说,农民如果给国家交纳很多粮食的话就可以给他增加爵位。皇帝采纳了晁错“入粟拜爵”的建议,并且通过亲自“籍田”,并且奖励“力田”的办法,鼓励农民从事农业生产。 为了将农民限制在土地上,从事农业生产,后世的统治者则不像汉朝那样文明,那样采取奖励农业生产的办法,而是使用更为严酷的户籍制度。在“里甲制”和“保甲制”下,农民职业“役皆永充”,农民的身份是世袭的,世世代代不能改变,而且严格禁止农民自由迁徙,自由流动,农民被严格地束缚在土地上,禁锢在乡村里,甚至连去集市赶集还得凭借“路引”。这种禁止农民自由选择和改变职业身份,禁止农民自由迁徙的做法,在上世纪的人民公社运动中登峰造极。其后果是,在中国形成城乡隔绝的二元社会结构,形成城乡两种权利义务截然不同的社会身份。

通过上述考察,可以清晰看到,近二十年来中国农民可以在在家务农与进城打工之间做出选择,大批农民毅然进城务工并且选择在城市艰难立足。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次巨大的进步。这种进步可能带来乡村的衰落,村庄的消失。但是,对此不必过于惋惜。对于众多诸如处于环境险恶,交通闭塞,公共服务无法到位的村落而言,那里并无什么田园牧歌!这等不宜于人居的村落的消失,有什么可惋惜的呢? 大量农民进城,一些村庄消失,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这种情况下需要警惕的是政府的两种倾向。一种是企图为了保卫村庄,使其不致消亡,继续将农民禁锢在土地和乡村之中;而另一种倾向则是借口城镇化,借口促进农民进城,政府积极“殴民入城”,放弃对于农民和农村本来已经严重不足的公共服务,放弃对于尚且留守农村的农民的扶持和帮助,使农村更为衰败,使留守农民陷入绝境。显然,在农民大量进城的情况下,政府尤其应该坚持均等化财政服务为目标,努力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农村的发展。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