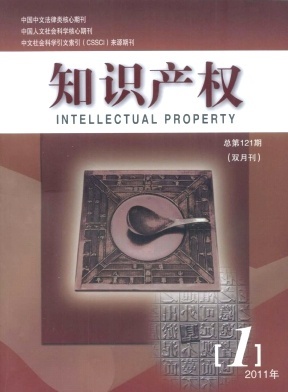陈久霖拿了公款去“豪赌”,赌赢了陈名利双收,赌输了也不用自掏腰包。要限制这种“冒险活动”,就必须倚靠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而这一点恰恰是国有企业的“命门”,其中不乏产权的原因,也有法律制度欠完善的缘故。
十年赌徒一轮回
1995年2月26日,巴林银行传出的消息震惊了国际金融界:由于在日经指数期货和期权交易中亏损4亿英镑,这个英国金融巨头被迫宣布破产,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就是巴林银行新加坡分行的经理兼交易负责人尼克.里森。巧合的是,2004年年底,巴林银行的翻版在同一地点“现身”了,那就是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因为其董事总经理陈久霖在石油期权和期货投机中判断失误,至今已累积至少5.5亿美元的亏损,并于11月30日向新加坡高等法院申请破产保护。
在这两桩相隔近十年的事件中,“前人”尼克.里森曾被誉为巴林银行的“王牌交易员”,一度为巴林银行贡献了利润总和的10%;而陈久霖,一个拿着2350万人民币年薪的国有公司“一把手”,被认为是中航油发展壮大的“功臣”、“传奇总裁”。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两人的共同败笔就在于进行了与市场趋势相反的操作。最终,尼克.里森因伪造交易文件而锒铛入狱,陈久霖也因涉嫌内幕交易而遭新加坡警方逮捕(现获保释)。
十年前,一个人搞垮了一家老牌投资银行。十年后的中航油不仅没有吸取前人的教训,反而“青出于蓝”,亏得更多。而之所以陈久霖可以让自己参与投机的“手气”好坏直接决定中航油的命运,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国有企业的内控机制在高风险的衍生品交易面前变得羸弱不堪。
无论是制度经济学家所指出的“产权界定不明”、“所有权人缺位”的原因,还是郎咸平教授所认为的“经理人信托义务不健全“的原因,中国的国有企业毫无疑问由于实际上的内部人控制而暴露在巨大的道德风险之中。国企的经理人在“软约束预算”条件下,往往倾向于盲目对外扩张或进行“冒险活动”。陈久霖拿了公款去“豪赌”,赌赢了陈名利双收,赌输了陈也不用自掏腰包。要限制这种“冒险活动”,就必须倚靠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而这一点恰恰是国有企业的“命门”,其中不乏产权的原因,也有法律制度欠完善的缘故。由于垄断地位给中航油带来的丰厚利润,眩目的光环不可避免地掩盖了健全公司治理结构的急迫性,直到东窗事发。
法律监管的真空地带
在期货行业内,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做期货风险大,不做期货风险更大。意思就是期货交易可以通过杠杆效应放大价格波动给投资者带来的不确定性;但另一方面,期货具有的套期保值功能使产品的需求或供给方可以提前锁定成本或收益,从而达到转嫁风险的目的。由于中国国内期货市场不发达,一些拥有重要能源进出口权的国有企业需要借助国外期货市场进行套期保值交易。但与此同时,风险控制又是监管当局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问题,尤其是1997年株洲锌厂在伦敦金交所进行期货投机交易导致亏损14亿人民币的事件,更引发了人们对国有企业自身风险控制能力薄弱的担忧。
2001年5月,中国证监会和国家经贸委等五机关联合颁布了《国有企业境外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办法》。该办法规定了国有企业从事境外期货业务必须经国务院批准,并取得中国证监会颁发的境外期货业务许可证。到2004年6月,全国只有包括中国有色、中国粮油、联合石油、联合石化、中远等17家企业获得了从事境外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资格。其中,中航油新加坡公司的母公司中航油集团公司在2003年取得该资格。
但事实情况是,中航油集团公司并未直接在境外从事套期保值业务,牵涉到这次事件的是其在新加坡注册的子公司——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一家没有得到任何来自中国官方进行期货操作授权的上市公司。不过,并不能就此得出结论:中航油新加坡公司进行境外期货业务活动违反了上述《国有企业境外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办法》,因为该《管理办法》的第二条明确了其适用范围,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国有企业(包括国有资产占控股地位或主导地位的企业)。显然,作为一家在境外注册的公司,中航油新加坡公司是不受《管理办法》约束的,因此无需事先取得许可证即可从事期货交易。
所以,这样就出问题了。根据《管理办法》,取得许可证的企业不得从事投机交易,并实行额度管理、备案、核准、报告、年检等制度以控制期货交易的风险。然而,这些制度无法适用在中航油新加坡公司身上,它既不需要取得许可证,也不会受到国内当局的监管和处罚。事实也证明了,陈久霖在期权和期货市场的所有操作都不是为了转嫁现货交易的风险,而是纯粹的投机,也就是“赌油价”。
尤其应该注意的是,中航油所参与的期权交易并非是通过新加坡的交易所进行的,而是一种场外交易(OTC市场上的交易)。必须指出的是场外交易的风险远远超过交易所场内交易,因为场外交易没有保证金制度,因而不存在强制平仓的问题,也没有持仓限额要求,只要参与交易的一方没有进行相反方向的操作,风险将始终暴露在外,与此同时也没有交易所来作为对方履约的保证,加之金融巨头操纵市场的机会也更大。针对这一点,《国有企业境外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办法》定义的境外期货业务是指境内企业从事境外期货交易所上市标准化合约交易的经营活动,因而就确认了国企在境外从事场外期货交易活动的非法性。
但是,在国外注册的中航油新加坡公司却不受这条规定“束缚手脚”。陈久霖在不受交易所成套规则体系约束的场外衍生品交易中,大量卖出石油产品看涨期权,而当市场变化趋势与陈久霖的判断相背离时(在此过程中,原油价格从40美元涨至50美元以上),由于“赌性”使然,他并没有进行对冲操作以及时止损,最终导致中航油被迫向法院请求破产保护。如果假设陈久霖的交易是在交易所场内完成,毫无疑问的是交易所规则出于控制风险的目的会极大地限制交易的投机性,陈久霖的“赌性”就不会“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因为通常而言,场内交易的最大亏损额只是保证金,而不像场外交易那样,亏损可能是无限大的。
问题归结起来,可以说是《国有企业境外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办法》确立的监管范围不够宽,或者说是手伸得还不够远。现行的《管理办法》把监管对象局限在国内注册的国企,而将国外注册,但由中国国有资产控股的企业排除在外。从国际法的角度分析,中国的法律只行使了“属人管辖权”,放弃了“保护性管辖权”。站在中国的位置,中航油新加坡公司是一家外国公司,但由于被中资控股,它经营活动的后果直接影响到中国国内。在这次事件中,中航油集团公司为帮助中航油新加坡公司还债,部分出售其持有的后者股权,为此还惹上了内幕交易丑闻的麻烦。
保护性管辖已被欧美发达国家成熟运用,最常见的就是在反垄断调查领域。故而,在规制境外期货交易活动时,中国不妨也把手伸得远一点,对于像中航油新加坡公司这样的境外“红筹”企业,不能使其活动处于法律监管的真空之中。
法网中的陈久霖作为商事主体的公司具有法律上的独立人格,但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必须依靠董事、经理以及其他高管人员这些自然人来完成。从公司和股东的角度来说,这些高管人员代表或代理公司的各项行为理应符合公司和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但是,这些高管人员并不是圣徒,他们也有自己的利益和偏好。如果有机会,他们也可能“损公肥私”,他们也会偷懒,也会疏忽大意,也会头脑发热。
因此,在公司法法理上,高管人员“背负”了两大义务:一是“忠实”,二是“注意”。前者要求公司高管人员在遇有利益冲突事项时,不得自我交易、竞业禁止、保守秘密、不滥用公司财产等,以解决经济学家所称的“代理问题”。“注意义务”又称“善管义务”,它要求公司高管人员勤勉尽职,不鲁莽行事。
在这次中航油事件中,陈久霖在进行衍生产品交易活动过程中犯了和十年前尼克.里森同样的错误,没有进行对冲交易,因而最终导致了“一泻千里”的亏损。理论上说,经营的亏损或投资的失败并不必然构成公司高管人员对其法定义务的违反,但是陈久霖的“大冒险”行为是完完全全地对期货、期权交易过程中控制风险原则的极大背离,根本就是对公司资产安全性的彻底漠视。不容置疑的是,作为中航油新加坡公司的董事总经理,陈久霖在支配巨额公司资产时具有重大过失,确确实实违反了“注意义务”。
公司法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规划健全的公司治理法律结构,而公司治理的两大目标就是实现公司利益最大化和保护中小股东。通常来说,这方面的具体制度安排包括公司内部组织结构设置,股东知情权保障,累积投票、类别表决,独立董事等,这些制度在预防内部人控制以及大股东剥削中小股东方面可以发挥积极作用。在具体的操作层面,董事、经理能有多大的权限还取决于股东大会、董事会的授权。
话说回来,法律的规定是一回事,法律能否得到执行又是另一回事。中航油新加坡公司并不缺乏相互制约的机制设计,高管人员可支配的资金也不是没有上限的,否则它也不会成为新加坡的上市公司了。因而就不得不说到“产权”这一话题了。中航油新加坡公司60%的股权控制在中航油集团公司手中,作为一家国有资产控股企业,天生的“产权虚置”所必然导致的内部人控制以及由此而来的道德风险往往使表面上华丽的公司治理结构“形备而神不至”。
对于这种道德风险,法律并非是无所作为的,事后的司法介入即是强化公司高管人员义务的一种威慑。中航油事件发生后,陈久霖由于涉嫌内幕交易而受到新加坡政府的刑事调查。然而,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来看,陈久霖除了要接受新加坡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可能有的行政处罚外,预计他还将面临高额的民事索赔。在英美法国家(包括新加坡),针对违反“注意义务”的董事、经理以及其他高管人员,股东可以提起对公司的衍生诉讼。此时,公司虽然是名义上的被告,但最终的赔偿责任由侵权者承担。不出意料的话,陈久霖就将是“期待”之中的“中航油新加坡公司社会公众股东诉中航油新加坡公司”一案或多案中的侵权者和最终损害赔偿责任的承担者。
如果我们假设一下,这起案件发生在中国境内,会有什么样的法律效果?可以肯定的是,“国家干部”陈久霖会遭受行政处分。但是,股东能把陈久霖送上民事法庭吗?答案是否定的。查找一下中国《公司法》的条文,我们也可以发现关于董事、经理民事法律责任的内容(63条),但这只是董事、经理对公司承担的赔偿义务,股东被完全排除在外了。
而现实状况是,两大因素导致董事、经理连对公司承担赔偿义务都很难实现。一方面,国内公司高管的收入不足以承担巨额的赔偿责任;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民事诉讼强调“不告不理”,“民不举则官不究”,所有权人缺位的国有企业在被内部人控制的情形下,除非存在高管之间的利益冲突,否则怎么能指望公司去向控制它的人索赔呢?
因而,赋予股东诉权就十分必要,此时无论公司是否有意愿起诉它的高管,股东都可以救济他们的权利。欣喜的是,正在修订过程中的中国《公司法》将弥补这一不足,明确规定,若因董事、经理的恶意或者重大过失而给公司造成损失的,股东可以提起诉讼,公司和董事、经理承担连带责任。
若陈久霖真被告上新加坡的法庭,那倒也成了在离人们愈来愈近的新《公司法》颁布之前的一次“进口”普法教育和“实战观摩”。至少可以让国内公司的头头脑脑们开始知道什么是公司高管的“忠实义务”和“注意义务”,让他们意识到股东们正擦亮眼睛盯着呢。

学费不能白交
纵观中国期货市场的发展历程,一直处于促进行业发展与控制系统风险的两难矛盾之中。而监管者也如同救火队员一般,哪儿有了“火情”,就去哪儿“灭火”,这就难免导致“一管就死”,打击了市场的活力,限制了期货工具积极功能的发挥。
总结这次事件,错不在于衍生工具本身,而是在于风险控制机制的缺位。从期货市场监管者的角度,制定并维护一个能保证衍生品市场在较低系统风险中运行的游戏规则远比“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成本低得多。对于境外期货交易的监管,假如早已制定了能够延伸至国外注册的中国国有企业的法规并确立常态监管的思路,相信中航油新加坡公司不会最终走向申请破产的窘境。
如果说以上所说是这次事件的第一个启示的话,中航油这个反面教材同时给予了完善国有企业治理结构路径探索的另一个启示。对于正处在改革关键时刻的国有企业而言,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绝对不单单是挂上“公司”的名号或者让党委书记担任董事长,厂长改叫总经理,工会主席兼任监事长就可以轻易实现的,而是一个牵涉到产权、公司法律制度、公正和高效司法体系建设的系统问题。
产权是一个敏感而又不可回避的议题,学术界在此问题上所持见解时有分歧。但不容回避的是,公司治理结构的不健全对于国有企业的存在和发展是一个巨大的障碍,而要从解决产权问题的方面移走这个障碍物就取决于经济学家的智慧了。
至于公司治理的法律问题,我们正期待着新《公司法》的出台。届时,无论是事前的预防制度还是事后的权利救济制度都会比现行《公司法》有一个大突破。当然,司法制度在多大程度上保障法律的运行也会直接影响到公司治理结构的有效性。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是一个综合性大课题,它决非只是产权问题,也不仅仅是制定法律的问题。
十年前巴林倒闭的事件给全世界的投资者和监管者上了一课。在1995年10月17日新加坡财政部发布的对巴林事件的调查报告中,把内部管理的严重缺陷认定为导致巴林垮台的主要原因。1997年的株洲锌厂在伦敦金交所进行期货投机交易导致亏损14亿人民币的事件又提供了本土的案例。但遗憾的是,中航油没有上好这几节“免费培训课程”,以至中航油不得不为中国的企业、政府、法律人缴纳了昂贵的学费,但愿这学费不会白交,更不希望学费交了一次又一次。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