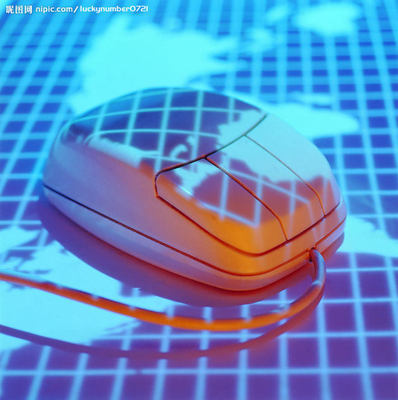中国目前最大的危险 如果由于现在的激进主义势力对威权政治的挑战引起的是使得后者日益走向保守,并通过一种刚性维稳的方式来应付挑战,那就会形成一种激进与保守之间的相互强化。 《中国经营报》:是什么使你从新权威主义代表学者,现在转向强调中道理性?如何理解中道理性?

萧功秦:从学理层面来说,我们的确是一种从革命体制转变为一种政府导向的威权政治体制。新权威主义所具有的社会整合能力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新权威主义本身的一些问题也开始暴露出来,主要表现就是导致了强国家和弱社会的格局,社会缺乏对政府的有效制衡,由于这种制衡的缺失,使得我们陷入了五种困境:第一个是威权政治自利化的倾向,第二个是利益垄断下的贫富两极化,第三个是国富民穷,第四个是国有病,第五个是人文教育的缺失、社会价值的劣质化与创新能力弱化的困境。 而要走出这些困境,已经不能简单地再强化现有的权威主义的刚性维稳方式了,必须要发育公民社会,同时也能为未来的中国民主政治软着陆提供一些有利的条件。 我说的中道理性不是在左右两个极中取一个中间点,而是既要超越左的激进主义,即文革激进主义,又要超越右的激进主义,即所谓茉莉花式的革命的激进主义。另外,还要反对保守专制和保守的威权政治。如果由于现在的激进主义势力对威权政治的挑战引起的是使得后者日益走向保守,并通过一种刚性维稳的方式来应付挑战,那就会形成一种激进与保守之间的相互强化,其后果必将导致我们失去改革时机,最终形成保守与激进之间的两极震荡,这才是中国目前最大的危险。 中道理性的具体含义就是要有序地发展公民社会,通过走小步、走稳步、不停步的方式避免巨大的社会震荡,避免所谓一揽子解决,使改革比较温和地进行下去。 要真正实现这一点就要允许各个地方、各个单位、各个组织、个人通过不断试错的方式,来找到克服困境的办法。 《中国经营报》:你提出要走出焦虑感,前些日子在反日游行中发生的打砸烧抢事件,是不是显示了整个社会的焦虑感,你怎么看最近发生的这些事情? 萧功秦:从这些事情来看,我们的民族主义还需要有一个自我改造。我们似乎更多地还是停留在一个弱国救亡时期的民族主义,这实际上是一种缺乏自信心的表现,是一种深层心理中的焦虑感的表现,也是对世界形势不太了解的一个表现,我们许多人对日本并没有很深入的认识。我们对日本的认识还停留在文革时期,看看网上那些“宁愿只长草”式过激的言辞就会发现,我们对国际问题的反应方式还停留在那种“有你无我”的阶段,没有共赢意识。这和中央一直提倡的和谐社会、和平崛起完全背道而驰。我们现在的这种表现,实际上还是一个弱国在长期受到欺负以后,形成的一种历史心理积淀,这种心理积淀中还残存着很多我们民族的“劣根性”。一个民族如果对这种劣根性没有反思精神的话,就永远不可能走向现代化。 另一方面,我觉得政府也有责任把日本的情况、国际变化,更多地在我们的教科书、在我们的有关宣传中体现出来。民间一旦形成一种紧张对立,政府就很难有回旋余地,再进行理智的决策就非常困难。 《中国经营报》:有学者比如崔卫平就说,其实现在政府的一些做法才是最激进的。她举例说,一些千年古镇政府说改造就改造没了,千百年来政府都没有像现在这么激进。 萧功秦:这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了,超出了政治学概念,指的是那种大跃进式的建设性破坏,确实是相当“雷厉风行”的,对此我也有深切的体会。例如,我去年去过贵州的镇远古镇,原来的黔贵风格的木质古建筑全被推土机推掉了,变成一大片砖石的徽派马头墙。那确实是一种令人忧虑的“激进”。 不过,那是一个另外的具体话题。这里谈的激进是与保守相对的一个概念。未来要极力避免的不是左与右两种激进主义的震荡,而是拒绝改革的保守力量和激进之间的一种震荡,通过走小步走稳步,温和坚定地改革,来逐渐摆脱目前出现的五种困境。而我们最后的目标是走向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 不断改革符合执政党利益 老百姓气顺,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公民社会就不会变成挑战政府的平台。 《中国经营报》:你强调走小步走稳步推进改革。但后革命时代的威权体制的控制力不可避免地逐渐弱化,动员能力减弱,加上决策者自利化倾向,改革的积极性成疑,如何保证改革继续推进? 萧功秦:决策者应该明白,只有创新才能真正的保守,或者说要维护现有体制,维护中国共产党的权威领导地位,只能不断地通过理性有序的改革,使社会不断地获得进步,在进步过程当中,执政党的权威就会越来越高,或者说其在民众当中的威信就会越来越高。所以共产党的执政者地位,实际上是通过创新而不断巩固的。真正有效的创新不但不会造成所谓的不稳定,相反是会带来更大的、更长远的稳定。 具体来说,通过改革,这个社会的中产阶层逐渐成长起来,公民社会发展起来,民主的政治文化在民间逐渐成熟,那么一种社会主义民主就在我们这里实现了软着陆。这个软着陆比起所谓的革命,给社会造成的阵痛要小得多。也就是说,我们在改革过程中,会不断地创造出民主的载体,即公民社会、中等收入阶层及民主文化,所有这些因素都有利于避免革命的震荡。换句话说,不是改革或民主化了,我们就会陷入一种震荡,恰恰相反,我们在走向有序改革的过程中,革命的震荡会被逐渐消解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不断地推动改革,既符合执政党的根本利益,也符合整合社会的最大利益。 《中国经营报》:你一直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的道路一直没有走偏,正常走下去,就会走到公民社会,你乐观的基础是什么? 萧功秦:我们可以把一个后发国家发展到宪政民主国家的历史进程分为五步,这五步前后之间有相应的因果关系:只有改革者掌权才能进一步进行经济转型和经济建设,只有经济起飞了才能积累巨大的社会财富来进行民生建设,而民生建设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在经济起飞阶段会出现两极分化,而这一矛盾如何解决?社会财富积累起来之后,国家可以通过动用经济杠杆,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来造成社会财富更公平的分配,包括民生建设的大力扩展,通过这种方式来化解两极化趋势,也只有贫富分化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才有可能建立公民社会,由于社会财富分配比较均衡,老百姓气顺,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公民社会就不会变成挑战政府的平台,而是一个公民自我管理的平台,也就是宪政民主的基础。 如果从这个五步来看的话,客观地说,我们现在还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一开始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改革派的掌权,然后拨乱反正,开启改革开放,然后是江泽民和朱 基这一代领导推动经济转型和经济起飞,而以胡锦涛和温家宝为代表的这一代领导人,在近十年内将很大的政策力度放在民生建设和均衡发展上。当然,我们的道路没有走偏,并不是说我们没有问题。 《中国经营报》:你觉得在这几步中出现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萧功秦:我们在第二步和第三步之间,现有威权体制出现了我前面说到的五种困境。也就是我们在前三步路没有走歪的同时,出现了困境。因此要解决这个困境的办法,不是简单的维稳,不是走向保守、倒退,或者退到文革去,也不是简单的把西方的那套茉莉花的方式移到中国来解决这些问题,而是通过渐进的改革来化解这些社会问题和矛盾。 《中国经营报》:你所设计的改革路线还是要在一定的威权控制下自上而下地进行,但是你提出改革下一步的公民社会建设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这其中有没有矛盾? 萧功秦:我在如何在中国发展公民社会这点上,特别提到过法团主义模式。具体来说,当社会出现了多元化,政府为了适应这种状态,会设置一些派出机构,通过这些机构反映多元的利益诉求,让它们和政府之间形成一种谈判机制,这实际上就是法团主义模式。法团主义这个概念,中国人不是太熟悉,有人把它称作合作主义,在中国台湾地区将其称为统合主义。这种模式有自上而下的特点。但它的好处是政府始终处于一个有效控制的状态中,政府可以比较放心一点,不用担心社会团体一下子变成脱缰的野马。但同时公民社会建设的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走小步走稳步的方式,放开民间团体,让它们自己逐渐成长起来。我们未来也要两条腿走路,不能只是法团主义自上而下一条道路,其他的比如IT工作者协会、中小企业家协会、各类商会等等,也要给它们空间自发生长。时机成熟的时候,农民协会也可以建立起来,还有教育协会等等,我想这些都是可以逐步去做的,不能再把公民社会看做是帝国主义安排给中国的一个陷阱,不能再停留在这个僵化思维阶段上。 中道理性与助推社会组织发展 政府面对越来越多的愤青式的挑战,恰恰是我们现在的教育制度所造成的。 《中国经营报》:但毕竟政府本来就很强势,自上而下搞到最后会不会跟现有的工青妇组织一样了? 萧功秦:我们的工青妇组织是有点像法团主义,但我把它称为“超法团主义”,它其实是国家的派出机构,并不具备自治性,主要还是发挥政府自上而下地组织社会、管控社会的工具的功能,而真正的法团主义组织是要具有自治组织的性质,要充分反映多元化的社会利益的需求的,它要充当民间与政府之间的沟通、协商的功能。 当然,实现自治的法团主义也要有个过程,还是要允许我前面说的试错,即在一个制度的创设过程中,很可能会面对不同的情况,有可能会复旧,以致雷同于原有的工青妇组织,当然,也有可能会变成一个挑战政府的平台,如何防止这两种不太好的倾向,这些都不是在办公室拍脑袋可以解决的,而是要在实践中发挥各个地区的党组织、执政精英官员以及民间的智慧,找到平衡点不断推进。所以必须要鼓励多元的尝试,否则这些问题放在办公室里一万年都不能解决。 据我所知,有些地区已经在考虑对工青妇组织进行改革尝试,让这些组织发挥更大的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作用,提出政府与社会力量互联、互补、互动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网络。力求通过公众参与,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发展。这种改革尝试可以看做是,把过去的完全隶属于国家的、派出性的“超法团主义”组织,改造为半自治的“国家法团主义”,如果再进一步改革,就会变成自治的“社会法团主义”。那就离真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不远了。 《中国经营报》:这需要决策者的勇气,也需要形成上下的改革共识,你觉得现在形成共识是不是更难了? 萧功秦:恰恰相反,我认为只要把道理说清楚,中国未来绝对不能回到文革路线上去,也不能通过所谓茉莉花革命解决问题,再也不能寄希望于通过保守大维稳的方式来解决矛盾,剩下来只有一条路,就是渐进有序的改革道路。我想这个中道理性可以作为一个社会共识的新的基础。因为前面两条路大家都看到,走不通的。因此我对于在中道理性的基础上重建社会共识还是抱有很大信心的。 《中国经营报》:你提出要迎来再改革时代,更具体点来说的话,你认为中国未来最重要、最迫切的改革是哪一项? 萧功秦:还是社会改革。十八大以后,党内民主当然可以搞下去,但是我不认为我们可以马上搞所谓的全民普选,全民普选无论在哪一个层面上,都是要比较慎重的东西。因为,全民普选非常容易导致民粹化,谁喊的响、谁许诺的漂亮谁就能当选,这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我认为未来最重要、最迫切的是社会改革,是助推社会组织的发展。 另外,我想强调人文教育的改革。我们的大学、中学、小学教科书都要做大幅度的调整,要加强人文教育、公民教育,其中也包括我们的国学,我们自己传统文化中那些美好的东西。否则,我们现在的教育只能不断制造出越来越多的愤青。其实这也不是政府希望的,恰恰是因为我们的教育体系没有改革,却不断地制造出越来越多的分歧,我作为一个大学老师,觉得这个问题已经越来越严重了。最开始,我们教育体制不改革是为了应付激进自由派的挑战,我们当政者要在文化上严防死守。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当改革已经行进了34年,仍然用这种思维,就会造成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政府面对越来越多的愤青式的挑战,恰恰是我们现在的教育制度所造成的。也就是说,现行教育存在的问题其实是造成社会上激进主义思潮的根源之一。 《中国经营报》:你对中国下一个十年政经周期,最大的期待是什么? 萧功秦:在这方面我比较保守。我只是希望要进入渐进改革的轨道上来,我们这十年里由于改革延迟,形成激进主义思潮膨胀,以及所谓刚性维稳机制与激进主义之间的互动与强化,我希望能通过中道理性的方式,逐渐克服与化解前面提到的五大困境,形成从威权体制向宪政民主良性发展的趋势,能做到这些,我就十分满足了,我希望十年之后,从上到下,大家的心态都变得比较平和。 《中国经营报》:你认为紧张感、焦虑感需要十年来化解? 萧功秦:在十年时间里,人文教育、公民教育扎实推进,公民社会组织健康发展,并能够达到一定的规模,我认为就是最大的成果了。至于宪政民主问题,在我看来是二十年以后的事情。我这样说,很多人难以接受,他们说,难道我们还要等二十年吗?但是由于我们已经失去了那么多的机会了,我们补课的时间就必须那么长。 链接:人物素描 “子孙会因此感谢我们” 尽管新书名字是《超越左右激进主义——走出中国转型的困局》,但在出版座谈会上,萧功秦还是同时收到了来自左右两派知识分子的批评。这样的场面对于这位一直活跃在思想一线的学者不算陌生。 上世纪80年代末的新权威主义论战,是内地知识界自1949年以来第一次完全自发的有关中国现代化命运的学术大讨论。而作为南方新权威主义的代表人物,萧功秦当时就处于论战的中心。 彼时,激进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占据了主流,很多人甚至开始讨论“球籍问题”,也即中国如果再不追随西方进行大的改变,甚至可能被“开除球籍”。以《河殇》为代表的文艺作品,就是这类激进的反思在文化上的反映。自由派知识分子尤其不能理解的是,刚刚经历了文革那样一个极端高压的政治体制之后,为何我们还要在萧功秦他们提出的一个新权威的开明专制下逐步完成经济社会转型。 尽管这一新权威主义的提法从未得到主流政治语系的接纳,但其实践行进的现实还是让自由派知识分子警惕。 在一次讨论会上,与会学者几乎一边倒地批判新权威主义,而没有得到反驳机会的萧功秦感觉就像参加了一场针对自己的批判会。 “当我回到家里时,含着眼泪抚摸着刚从学校放学回家的八岁女儿的头,心想:如果近代史上的激进主义由于我们这一代的过错而在中国重演,如果中国再次出现乱世与反复,这些孩子将经受怎样的苦难?难道我们不应该为他们的未来想一想?” 新权威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分野其实也意味着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新启蒙运动的终结。而由于这次分裂带来的争论影响至今。 到了90年代初期,尤其是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萧功秦开始更深入地关注“激进的自由主义思想和威权政治之间的悲剧性冲突”。这时他从中国近代先哲,尤其是严复那里得到了批判的武器。严复提出,“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强调新和旧之间应该有一种辩证的统一。在这个意义上,萧功秦举起了新保守主义的大旗。 但萧功秦虽然提出了新权威主义经由经济腾飞、公民社会逐步迈向中国特色宪政民主的现实路径,却不能保证现有政治体系一定会按部就班地完成这样的转型。而历史的行进似乎也在验证着他的担忧,威权体制下政府力量逐步强化,而社会发育却极其缓慢,甚至陷于停滞,强政府弱社会的结构使得新权威体制向宪政民主转型的路径有被锁定的危险。 今年年初,萧功秦在一次媒体访谈中提出,要摆脱锁定的路径,就必须重新启动改革。改革的方向就是逐渐走向公民社会,实现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均衡状态,即强国的同时强社会。“强国加强社会就不是新权威主义了。”他说,从世界各国现代化历史来看,好的新权威主义与劣质的新权威主义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通过发展公民社会走向宪政民主,后者拒绝变革而走向封闭的官僚利己主义,并最后导致激进革命的灾难。 萧功秦也开始尽量避免再使用新保守主义这个词汇,他担心引起别人守旧固执、为体制辩护的联想。 今天,面对同样激烈的批评和质疑,萧功秦更看重的是争论背后的改革共识。他认为,只有超越激进与保守,坚持中道理性与渐进改良,中国才有真正美好的未来。他坦言,形成改革共识,通过共同努力来使中国走出困局,是包括知识分子、普通的民众、官员在内的所有社会成员的共同事业,“未来的子孙会因此感谢我们。”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