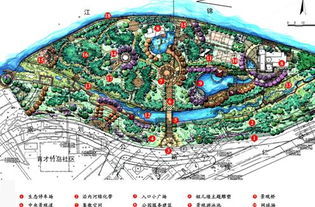●改革要尊重既得利益,改革总是需要妥协的,妥协是改革的一个原则,但改革的原则是不能妥协的;●制度都只能针对通例和一般情况,因此必然有其缺陷;但我们可以针对特例设计特殊规定减少缺陷。
1.全球化的大学改革浪潮
赵晓:你谈到欧洲大学的管理体制也存在许多问题。他们是否也在改革? 张维迎:其实,全世界的大学都在改革。比如日本,这几年大学改革的步伐非常快,日本国会通过议案,国立大学法人化。就是要通过改革,让大学变成一个自主性的单位,破除政府对大学统一的控制:预算上的控制、教员的控制、教学标准的控制等等。在教员筛选方面,日本要求你在这里做几年,不优秀就得走,并大力废除“近亲繁殖”。 同样,欧洲的大学也在改。像牛津大学,最近改革的步骤非常大。经济系新上任的系主任———著名的计量经济学家DavidHendry———上任开始,就大刀阔斧地改革。其中之一,是他把两个只教书不做研究的教员“开”了。结果这两个人把他告到法院,他就上法院应诉。最后是这两人软了下来,“私”了。 今天,全世界的大学都在改革。其关键是,全球化时代各国大学之间的竞争日益充分,社会的发展也对大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像欧洲大学教员那种养尊处优的日子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赵晓:全球化影响深远。无论是企业、政府还是大学,或者在竞争中落伍,或者主动改革迎接挑战。全球化的竞争是否也是北大改革的一个背景考虑? 张维迎:全球化对我们、对各国的大学形成了压力。全球化浪潮来临,人才流动、信息流动更容易了,教育模式、大学的好坏慢慢出现了一个相对一致的标准。你是不是一个优秀的大学,再也不能封闭起来自己说了算。你有没有能力吸引优秀的教员和优秀的学生、做出一流的研究成果?跟其他国家的大学相比,你是不是最优秀的?是不是学科最前沿的?这成为每个研究型大学都必须考虑、必须面对的问题。否则,不进则退,就只能在全球化竞争中败下阵来。2.原则、妥协与公平:大学改革的智慧
龙希成:就北大方案来说,为什么不把副教授都一次性地转成终身教职?为什么要设计这么一个有限次申请有限次晋升的更复杂的方案?而对于一些人文学科,有的长达18年,人的半辈子都过去了,是否给的时间太长了? 张维迎:这个问题问得好。首先,要解决大学的治理问题,特别是大学教师的招聘和晋升制度。我们讲大学的逻辑和理念,就在于大学要为人类创造知识、传授知识、服务社会,那么什么样的体制才能保证达到这个目的?教师的聘任和晋升是关键的制度。因为创造知识需要特殊的人才,并非每一个人都可以胜任。 好多人可以循序渐进、按部就班地做事,但可能并不具有那种兴趣、激情和才智来创造知识。所以,大学设计的体制,并非给所有人设计的,而只是给最能够实现大学功能的那一小部分人设计的,他们只占总人口的1%~2%,甚至更少。大学要按自己的逻辑运行,要最佳地创造知识,就要把最优秀的人聚集起来。 这就有个选人的问题。你怎么能够选到最优秀的人?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大学的选人体制,但是应该说美国这种Tenure-track(终身教职制度)明显成为主流的制度,包括欧洲、日本的大学现在都在学它。我们要借鉴这样一种制度,不能因为它是“美国式”的就认为不适合中国。 大学选教授要冒很大的风险。你不可能看一次两次,看一篇文章,就判断一个人是否达到了教授的水准,因为一个人在知识上的创造力,要有一个实际表现的过程。所以大学制度设计上要有一个试用期制度。 为什么试用期是六七年?这与知识的生产特点有关。试用一个搬运工需要多长时间你就能确定他是否合格?可能是一天两天;试用一个保姆呢?大概一个月;试用一个秘书呢?可能是三个月。但是,试用一个合格的大学教员,一年两年的时间都太短了。从国际经验看,一般需要六七年,一个人拿到博士学位后,六七年内应该表现出他的才华,显示出他够不够做一个合格的教员。 我想大学改革设计的体制,在基本的目标模式上,主要应借鉴美国Tenure-track体制。为什么不学欧洲的大学?因为欧洲大学的模式失败了。我本人是牛津留学回来的,牛津现在的试用期是四年,有的是三年,太短了。现在有些学术刊物发表文章的周期都要两三年。试用期太短,大学没有办法看出一个人的能力。我们设置的一般标准是6至7年,比较适中。 在六七年内的时间内,不等于说我对你就不闻不问,到六七年后再看你行不行,不行再让你走人。事实上,3年会有一个评估(Review),这个评估并不特别要求你已经拿出来非常好的文章,而是看你的基本表现,看你在学术上是不是还有希望。如果确实没有希望了,那就该走人。 有些人说方案既然学美国,你为什么要有这个3年的评估?其实在美国,好多大学是2年一个评估,并非让你6年后拿Tenure(终身教职)、6年内对你没有任何约束。对于有些人,可能2年就发现他根本不是做学问的料,那就早点让他走,不必耽误他那么长的时间。 赵晓:也就是说,确定一个保姆行也许需要一个月;但确定她不行,可能一件事、一天之内甚至一个小时就OK了。 张维迎:是这样。所以,六七年只是大体上的时间。有人2年可能就走了,而特别优秀的可能三四年就拿到了终身教职。 赵晓:有人说,如果我是一个讲师,我在讲师位置上干好自己的事情就行了,我不升副教授、教授,你干吗要我走呢?我做一个合格的讲师不就行了吗? 张维迎:这个说法完全错误。大学选讲师、副教授的时候,并不是为了选讲师、副教授,而是要选一个优秀的学者,一个能成为最优秀教授的人。从讲师、副教授到教授,只是整个选择过程的一个环节和必要的激励机制。我找搬运工,就是为了找一个搬运工,他无需升任车间主任。但选大学教师不同。大学选人就是要选能成为最优秀教授的人,其他的位置都只是作为一个试用、选择的中间过程。 所以,讲师和副教授们不能说,我只停在中间过程当“半成品”行不行?这是误解。我当初早知你只有当讲师的潜力,就不会要你。一旦明确你没有潜力成为优秀的教授,就等于宣布你的失败,你就应该走人。 赵晓:设想这样一种情况:我永远做讲师,我在这个大学做完讲师后,再到另一个大学做讲师。可以吗? 张维迎:这很有趣。其实,我们就是试图找到一种能够适应长期变化的相对稳定的制度,同时又能迁就现实情况的改革办法。因为改革并非一个从零开始的过程,而是要把现有的体制进行变革,所以我们设计的多少多少年只是一个过渡,最终目标是以后大体上六七年就能确定一个人究竟适合不适合在北大。 但在现有的体制下,你要一下子走到那一步,提副教授做Tenure的话,副教授的标准就要大幅度提高。这不现实。所以,只能逐步地,先把Tenure定在教授这一级。然后,提副教授的标准逐步提高。现在博士毕业2年后表现不错的话,可能拿到副教授,以后就变成三四年,再以后就变成五六年,标准越来越高。 并非一定要让你待上十几年,那是给你一个最宽的期限,但目标不在这里。给宽限是为了照顾现实,否则,现在有人已经呆了好些年了,他怎么办?有人说我讲师呆6年,再副教授呆12年,总共18年;18年后你再不要我了,那我去哪里?其实,没人想让你呆18年,最好是六七年见分晓,不行你就应该走了。 赵晓:是给一个最宽的底限,但底限并非平均线,更非目标线。
张维迎:对。举例来说,好比盖大楼,大楼内有些是“承重墙”,这是不能动的;还有些是“非承重墙”——隔离板,这是可以动的。我们的方案既有承重墙也有隔离板。 什么是承重墙?就是在这六七年的试用期,你最多只能申请两次晋升,不行你就走。其他的过渡时间都是隔离板,要视情况而变化。但方案既要实行于新招的人,又要实行于已有的人。这个矛盾比较大。所以限度现在放得比较宽一些。就像吃饭,有的人可以吃5个馒头,有的人可以吃1个馒头,现在的方案定的是你可以吃1至5个馒头。 龙希成:是否有一个对中青年教师与老年教授之间的不公平的问题?也就是说,要么把现有的副教授、教授都转成终身教职,要么大家都“就地卧倒”、重新评聘谁够不够格获得终身教职。 张维迎:任何改革都要考虑尊重既得利益;既得利益越多,考虑也应该越多。这是一点。另外,从文化上讲,中国人讲尊老爱幼,你不能说年龄那么大的人要先让他走,这不人道。老年人与年轻人不同,年轻人毕竟有更多的选择机会,为什么要和年龄大的攀比? 其他领域的改革也是这样。国企改革,年龄大的可以让他提前退休,但不能让他下岗;而三四十岁的年轻人就不一样。你不能说这不公平。 而且,照顾年龄大的符合效率原则。行为经济学的研究表明,一个人占有某个位置的时间越长,他失去该位置的痛苦就越大。所以,法律上也有“先占原则”:把有争议的财产判给占有者。 改革不是革命。革命是推倒重来,而改革要靠现有的人去做。如果把副教授、教授都“就地卧倒”,那马上就有一个问题:从长远看,教授一定是Tenure(终身教职)的,但如果他们现在就统统“卧倒”,那么谁来评谁够不够格拿到Tenure呢?没有人来评。那就只好请外面的教授来评了。这不现实! 总得有一部分人来评另外一部分人。教授中是有一些不合格,但总体上还能控制。因此目前的选择是现实的选择,是合理的选择。 大学评聘教员要靠现有的人力来完成。所以,“就地卧倒”的做法是不负责任的,也不可能成功。 我们评价任何一个改革方案,都应该看它的alternative(备择方案)是什么?是不是比现有的更好?如果不是,那么现有方案的就是更优的方案。 你要指出方案的毛病可以,但你应该要提出合理的备择方案。无论是从公平的角度、人道的角度还是从效率的角度,我相信还是现有的方案更好。 龙希成:是否也要尊重副教授的既得利益:把现有的副教授、教授都转成终身教职,以后Tenure就定在副教授这一级上? 张维迎:我在《说明》中讲过,为什么副教授不能都变成终身教职?因为北大的编制已经快满了,这是一个现实的约束。我们现有800多个副教授,如果教授、副教授都定成终身的,就没有回旋余地了。副教授、教授已经把位置都占完了,你要招新人,还可能吗?如果北大像中山大学那样,名额大量缺编,那么这种提议是可以的。北大的某些学院像光华管理学院也可以,因为光华大量缺编,改革初始只有40多人,编制是120个。但是整个北大不行,因为没有回旋余地。 龙希成:编制是国家定的还是北大自己定的? 张维迎:国家按照学生数量给出一个编制的计算,学校按这个去做。 就算国家没有编制限制,学校也要有编制啊,因为你的预算是有限的。这就像一个房子,你的书架就那么大,过时的旧书已经占满了,你要买新书,怎么办?你只能把旧书挪走。但另外一个人的屋子若是特别大,现有的书只占了一个书架,还有许多个书架空着,那他自然可以先不理旧书。所以,这是一个不可一概而论、而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定的问题。 所以,改革要跟现实主义结合,在寻求长远的理想目标与现实的可行办法之间找到结合点,不能走极端。 我想说,改革总是需要妥协的。妥协是改革的一个原则,但改革的原则是不能妥协的。妥协是改革的一个原则,这包括对既得利益的照顾,其实我们对副教授也有照顾,好比50岁以上的人都不动,这也体现着人道。但最基本的原则——引入外部竞争,有限期有限次地晋升,原则上不留本校毕业生,这些原则都坚定不移!
3.大学改革与学术自主
龙希成:方案似乎强调引进国外培养的博士,而不留本校的博士。这是否涉及学术自主的问题? 张维迎:何谓“学术自主”? 龙希成:就是中国人自己办的大学,不能过多地依赖从国外留学归来、满腔“洋”味的博士。 张维迎:其实,如果真正开放以后,理论上,选人与你是哪儿毕业的无关,只要达到标准都可以,你只要经过评鉴程序、被认为是优秀的就行。像光华管理学院,我们在国内招人也在国外招人,国外回来的有特别优秀的,国内招的也有特别优秀的。 龙希成:如果是本校培养的博士呢? 张维迎:本校培养的当然有特别优秀的博士,但是我们为什么不能留?我早已讲得很清楚:因为你留下一个优秀的人,但可能带进三个不优秀的人。 赵晓:现状是:借着留优秀人才的机会留近亲的“搭车问题”无法解决。 张维迎:是这样。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考虑了一些灵活性,像对一些学科的特殊人才就有特殊的规定。但这只能是一个特例,而非通例。原则上我们不留本校毕业生;如果要留,那就要提出足够的理由。如果原则上就规定可以留,那他不提出理由就可以留了,就没有办法保证人才的质量了。 本校毕业出去的,其中很优秀的,我们可以把他再吸引回来,并不会造成人才流失。像光华这几年,从海外招来的几乎超过一半都是本科北大毕业的。为什么要将原则上不留本校毕业生与人才流失相提并论呢!4.通例与特例:大学改革的技术性设计
龙希成:通例与特例的分别很重要。像沈从文、钱穆和梁漱溟是典型的没有博士学位的文史哲的人才。而方案则要求有博士学位。其中的通例与特例的关系是什么? 张维迎:这个问题问得好。我想至少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 第一,社会本身在进步,科学在发展,今天的基本趋势就是越来越要求基本的知识积累,科学的进步已经越来越形成一些规范性的东西,学位要求实际上意味着后来者必须有前人的知识积累。所以,你不能因为历史上某人才没有博士,现在也不能要求有博士。孔子是大师,他没上过大学,那么我们评聘教员是否连大学文凭也不要求呢? 不能简单地用历史套现实!华罗庚是大数学家,没上过大学;但今天,一个没上过大学的人要成为华罗庚恐怕难有希望了。我们不能再让数学家从一麻袋一麻袋的业余数学爱好者的来信中挑选哥德巴赫猜想的证明了。 第二,特殊人才要靠特殊手段去发现。特殊手段一定要与通常手段不一样。但是,假如说首先没有通常手段,那我们怎么去选人?每年申请到北大教书的可能成千上万,谁有那么多的时间精力来评鉴这些人?所以学位要求只是一个初选,把范围限定到一定程度后,选人的工作量就大大减少。至于特殊人才,他会有特殊的办法冒出来,但特殊人才要拿得出特殊的东西来。你说我没有博士学位也会有大成就,那你拿出你的大成就来;如果拿不出,只是嘴上自认为有这种可能,那不行! 赵晓:制度通常适应于一般情况;特殊情况需要特殊制度。 张维迎:可以这样来思考通例与特例的问题。在统计学上,有“第一类错误”与“第二类错误”之分:第一类错误就是我们可能接受一个错误的东西,第二类错误是我们可能拒绝一个正确的东西。这两者都意味着犯错误。那我们就对这两者进行权衡。 现在的方案,包括对学位的要求,可能会拒绝一些优秀人才,但是犯这个错误的可能性,远比没有这个要求之后、接受庸才的可能性要小得多。所以,现在的方案是合理的。对特殊人才,我们只能用特殊手段去选拔,但这些特殊手段也只能作为通常手段的补充而非主流。 法律上,一种主张叫“无罪推定”。按此规则,有时候一些罪犯你没有办法证明他的罪,结果就成了漏网之鱼。但这个制度比“有罪推定”好。因为“有罪推定”先假定你有罪,除非你证明无罪才会被释放。但你证明起来很困难,这样很多的人会受冤枉。相对而言,还是“无罪推定”的制度为优。这样的智慧也应该是我们考虑通例与特例时的智慧。 从来没有一项制度是完美无缺的,人类的智慧就在于懂得选择相对更优的制度。相比于把特例当通例的做法,现在的方案更优。 制度都只能针对通常情况,因此必然有其缺陷;但我们可以通过针对特例制定专门条文的办法减少缺陷。像对特殊人才,方案规定特别优秀的人可以不受学历、年限的限制破格录用、提拔。这意味着对于无博士学位的人,方案并未一概排除。方案把这个写成例外,是为了在执行起来严格要求,免得把太多不合格的庸才当人才。 你说你就是只有小学毕业的钱穆,那好!我相信钱穆按现在的方案,一定能当北大教授。但是,有太多的人自以为是钱穆了。遗憾得很,钱穆在一个小学校教书,都能做出那么大的成就,我们许多人在大学那么多年都做不出像样的成就来,那你有什么资格跟钱先生攀比?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