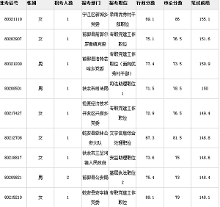莫言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国内舆论几乎已经到了“疯癫”状态,瑞典学院院士马悦然和谢尔·埃斯普马克又在此时来到中国,更让诺奖话题发酵成漫长的传话口水战。10月27日,埃斯普马克造访南京,讲述了诺奖诞生的前后故事,评委会是怎样构成的,老先生们又是怎样工作的。至于各种猜测和流言—他说,院士们不愿意闹出任何丑闻,那是真的会被瑞典学院开除的。 口水仗和贿选风波 此番马悦然和埃斯普马克前往中国,所有行程几乎都和上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Tomas Transtromer)有关:马悦然为特朗斯特罗姆的诗集做了中文版的翻译,定名《巨大的谜语,记忆看见我》;埃斯普马克除了宣传自己的作品《失忆》之外,则以特朗斯特罗姆好友的身份和译者万之一同推广《航空信》—特朗斯特罗姆和美国诗人罗伯特·布莱(Robert Bly)的通信集。 尽管如此,可以早早预想到的是,因为莫言刚刚获奖,两位院士的中国行都没法不谈诺奖,他们要推广的书籍反而成了次要话题。埃斯普马克甚至特地澄清,自己不是为了诺奖而来,中国行早就是既定路程,自己上半年就要来中国宣传另一位瑞典诗人哈瑞·马丁松(Harry Martlnson)的《阿尼阿拉号》,只是被耽搁了。 马悦然一句闲话提到了“山东文化干部”给他邮寄书画以图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当媒体们再去追问埃斯普马克,写出的报道却成了“这完全是胡说”。但是埃斯普马克说他的本意其实是:“瑞典学院的院士是不可能接受贿赂的。如果有接受贿赂这种说法,一定是胡说(nonsense)。” 因为翻译和理解的问题,埃斯普马克的意思被曲解了,耸人听闻的标题干脆说“埃斯普马克表示马悦然是胡说”,而更多的人则要求马悦然说清楚“到底是谁”。山东作协主席张炜干脆写了公开信要求“说清真相”。 埃斯普马克再次谈到“贿选”问题的时候,非常明确地说:“我也愿意跟你们说,我们是不可贿赂的。谁要被发现接受贿赂是要被开除的。”他举例说,在瑞典学院的历史上,确实曾有院士被开除的先例。1881年一个院士伪造签名陷入赌博的丑闻而被开除。“我们不愿意闹出任何丑闻来。对院士的道德方面有两个要求,一个就是不能泄密,另一个是你不能做有损名誉的事情。”埃斯普马克说。 中国媒体的传话和误会,埃斯普马克本人并不清楚,和埃斯普马克同行的作家、译者万之(他也是莫言作品的瑞典译者陈安娜的丈夫)则回应了外界追问“到底是谁”的问题:“我觉得很无聊。有些记者,咄咄逼人,简直像‘文革’的红卫兵,我觉得是非常讨厌的。比如说我说一个事,曾经有个作家找陈安娜翻译,你就说,非要把名字说出来,不说出来就是造谣。你说这个荒谬吗?我要保护人家的隐私。”至于张炜的公开信,万之说:“张主席大概是被人误会了,有人造他的谣。张主席的作品《古船》安娜在翻译,是我让她翻译的。” 因为陈安娜是莫言的瑞典译者,又是马悦然的学生,也有人猜想,是否找陈安娜翻译有便捷,是否陈安娜是某种渠道。万之对此也一并回应:“你们经常说贿赂,是对人的污蔑。有人造谣莫言贿赂了谁,莫言没有贿赂任何人。我作为安娜的丈夫可以告诉你,我们出版《生死疲劳》,一分钱稿费都没有。我们家穷得很,洗衣机都没有,我们俩轮流刷盘子。我们跟作家的关系是君子之交,我喜欢你的作品就给你翻译。也有作家让我们翻译,这也没什么,就像翻译公司一样,这是商业不是文学。我们不是院士,我们没有权决定什么。” 万之还补充,在瑞典出版中国作家的作品并不容易,很多老板都赔钱,陈安娜翻译苏童,也是征得了苏童版权上的同意,完全无偿给出版社,一分钱没拿:“翻译就是我们业余爱好,我们是靠工作维持生活,不是靠翻译。” 瑞典学院的院士们对所有涉及到钱的事情都非常谨慎,万之说,自己陪同埃斯普马克到南京,是瑞典学院出的费用,而不是出版社:“瑞典学院让我们来的,这是一个瑞典作家,我们有责任为他而来,所以我们才来。” 谁有权提名诺贝尔文学奖 此番莫言得奖,埃斯普马克在多个场合表明了自己对莫言水准的肯定。但是当被问及对其他中国作家的看法,他只是说:“我带着兴趣在追踪他们的创作。我认为当代的中国文学已经像中国的古代文学一样在瑞典引起了人们很大的兴趣、很被人了解。”进一步的评论他则只能“笑而不语”:“在我们这个圈子里,我们不太愿意谈一些还没有得过奖的作家,或者做仔细的评论。” 让别人知道瑞典学院的院士最近在读什么书、看什么作家,这是很“敏感”的。埃斯普马克说,他在飞机上看书,不能让别人看到自己在看哪位作家,经常把一本地理教科书的封面套在一本文学书的上面。 外界对分量极重的诺贝尔文学奖总是充满了诸多疑问,此前埃斯普马克还曾专门著书《诺贝尔文学奖内幕》一本,解释这个奖项的诞生前后,也毫不留情地说诺奖遗漏了一大批重要的作家。

中国读者总是在问,为什么现在才轮到中国作家,谁在负责提名?埃斯普马克解释,只有四种人有提名权:第一种是院士本人;第二种是得过奖的诺奖得主,例如大江健三郎有权提名莫言,现在莫言就有权提名别人;第三种是文学教授,而且是正教授(full professor);第四类是各国的笔会主席、作协主席,所以过去的巴金、现在的铁凝都有提名权。埃斯普马克还强调了两种不能提名的人:“你们要注意,重要的是出版商不能提名,文学批评家不能提名。” 种种“贿选”的传闻不少跟马悦然有关,但是埃斯普马克澄清,马悦然不在五个人组成的诺贝尔评选委员会里面,他只是18个院士之一。而五人小组和18位院士则各有分工。五人小组负责提名的工作,将提名缩小到20人(俗称“半长名单”),然后将提名人的简介和作品交给其他人,到5月底这个名单缩小到五个人的“短名单”,学院所有人整个夏天的工作就是去读这五个人的作品。在整个学院的阅读“暑假作业”完成之后,最终的决定还是要由18名院士共同作出:“任何一种关于某一个人可以决定诺奖评选的说法都是不成立的。如果你见过这18个院士,你会知道他们都是很有智慧、很有主见的人,你就会知道关于其中一个人能说了算的说法是多么荒谬。” “我们不要再提文学现代性吧” 邀请央视不是剧透 时代周报:本届诺贝尔文学奖邀请了中央电视台去报道,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剧透”? 埃斯普马克:负责文学奖的瑞典学院根本没有邀请过CCTV,也许是上面的总基金会为了扩大媒体的范围而邀请了他们。每年总基金会都会邀请不同的媒体,可能今年邀请,明年也会邀请,有中国媒体并不是说今年中国人得奖了。 总基金会对今年的结果无权干涉,我们做决定他们并不知道。邀请央视,我都不知道是不是邀请,这是一种传言,这跟我们的颁奖毫无关系。 时代周报:每年大家都会关心Unibet和Ladsbrokes的赔率表,你怎么看赔率表的猜测? 埃斯普马克:赌博公司的这些东西是毫无意义的。 时代周报:有一种意见是,文学奖有“少数派倾向”,不管是语言、族裔还是政治立场,奖项都倾向于颁给“少数派”? 埃斯普马克:诺贝尔奖并不是一个给国家的奖,小国还是大国,小语种还是大语种,都不是我们考虑的范围。我们考虑的是,颁给作为个人的伟大的优秀的作家。而且政治在我们的讨论中也没有任何的作用。 诺贝尔的遗嘱说:“要褒奖对人类有利的文学。”历史上对遗嘱也有不同的解释和标准。上世纪30年代,那些老院士们认为对人类有利就是卖得很多的大众文学,那时候就选了那些很流行的卖得好的作家。这样的标准就不利于那些喜欢创新的小众的作家。“二战”之后他们就比较注重那些创新的、有先锋性的作家。到了70年代以后又有新的标准,开始关注那些在世界上相对没有名气而优秀出色的作家,这样利用诺贝尔奖让他们得到更多的关注。 在今天,越是很畅销的作家可能越是没有希望,当然好作家能够卖得很多很畅销,这也不会是他得奖的障碍。但是诺贝尔奖会起到这样一个作用,无名又出色优秀的作家,可以通过得奖扩大他们的读者群。 我可以给你一个例子。1978年,要在英国作家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和一个很不出名的犹太作家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Isaac Bashevis Singer)中挑选一个,辛格是用意第绪语写作的,几乎没有人知道他。我们给辛格颁奖,使他的作品被翻译成了5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都有读者,那就是我们很好地利用了诺贝尔奖。 时代周报:对,人们都说诺奖是出版商的风向标。 埃斯普马克:但是任何人不能预见这个风向。我们不会让你预见风向,不让你想到接下来会朝哪个方向,院士们会有自己的想法。 时代周报:你觉得瑞典学院和诺奖在文学上的权威性来自哪里? 埃斯普马克:我们这么多年的选择经常是比较明智的。不过也不是一直如此,尤其是“二战”之前的选择,在我看来也就是如此而已,有些还不太明智。“二战”之后我们的政策越来越强越明显,有我们自己的想法。这么多年的明智的选择建立了我们的权威性。 我们也努力地扩大了我们选择的范围,比如在战后尤其是近期,有尼日利亚作家沃莱·索因卡(Wole Soyinka),埃及作家纳吉布·马哈富兹(Naguib Mahfouz),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因为我们的范围扩大了,权威性就扩大了。 时代周报:其他文学大奖获奖作品是否纳入瑞典学院的阅读范畴? 埃斯普马克:我们对任何其他的奖项不在乎,也不考虑。 说诗歌边缘化的人是“短视” 时代周报:你本人也是诗人,你怎么看待中国诗人北岛?他在中文读者中呼声很高。 埃斯普马克:我和北岛是朋友,我们认识很多年了。相遇交往过很多次。北岛还是我诗歌的第一个中文译者,我对他的诗歌很欣赏。 我甚至因为和北岛的交往创作了一首诗。我有首诗叫《西安兵马俑》,北岛到我家里做客,带给我一个礼物就是兵马俑,结果一打开全碎了,我就觉得碎的兵马俑也启发了我,又写了一首新的诗。 时代周报:在中国,诗歌的读者群越来越小,在瑞典这方面情况如何? 埃斯普马克:你们不要小看诗歌的重要性。如果我问你波德莱尔是谁,《恶之花》是什么,很多人知道。如果我问你,今天谁是法国最富有的人,或者谁曾经是法国的总理,你能记得吗?人们记得的都是波德莱尔的《恶之花》是名作,1895年出版,但是那些富人、权贵,谁记得? 如果不了解诗歌的意义,觉得它很边缘,是因为这些人“短视”,看得太近。土耳其诺奖得主帕慕克曾经说过诗歌是没有前途的。可是他真的忘记了,他的那些小说语言是建立在诗歌的基础上的。所以有很多作家意识到诗歌艺术的重要性。 在瑞典,诗歌是很被大众热爱的,而不是被大家遗忘的。瑞典诗歌从1930年以来经历了一个黄金时代,有好几个大诗人。比如说197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哈瑞·马丁松,5月刚出版了他的中文版诗集《阿尼阿拉号》。当然还有去年的诺奖得主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瑞典诗歌有很多名字可以说。 时代周报:汉学家顾彬最近谈到,中国的当代文学可能都不够现代性,不知道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埃斯普马克:中国当代文学确实是在非常光辉的时代,有很多很优秀的小说家、作家。我们不要再提那些现代性吧,我们已经超过了现代性的问题。现在的文学是有多种可能性多样性的,不需要用现代性作为标准。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