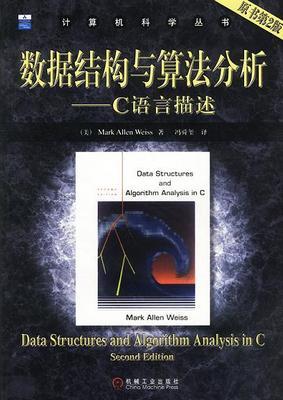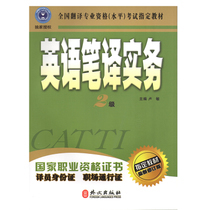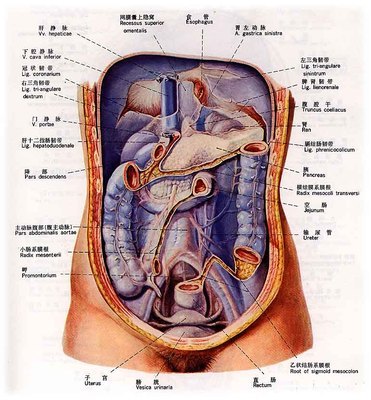梁实秋本打算用20年译完《莎士比亚全集》,而实际上用了30年。译完后朋友们为他举行“庆功会”,他在会上发表演讲:要译《莎士比亚全集》,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必须不是学者,若是学者就搞研究去了;二是必须不是天才,若是天才就搞创作去了;三是必须活得相当久。“很侥幸,这三个条件我都具备。”众人听了,开怀大笑,气氛顿时活跃起来。作为我,当然不能同梁实秋相比,但他说的这三个条件,我想我也大体具备。我不是像样的学者,更不是天才。即使同作为本职工作的教书匠相比,最为人知晓的也仍是翻译匠。

其实,即使这最为人知晓的翻译匠,也纯属歪打正着。过去有名的翻译家,如林琴南、苏曼殊、朱生豪、梁实秋、周作人、鲁迅、郭沫若、丰子恺、冰心、杨绛、傅雷、王道乾、查良铮、汝龙等人,大多出身名门望族或书香门第,自幼熟读经史,长成游学海外。故家学(国学)西学熔于一炉,中文外文得心应手。翻译之余搞创作,创作之余搞翻译,或翻译创作之余做学问,往往兼翻译家、作家甚至学者于一身,如开头说的梁实秋实即完全如此,也是众人开怀大笑的缘由。而我截然有别。上个世纪50年代初,我出生在东北平原一个至少上查五代皆躬耕田垅的“闯关东”农户之家—林姓以文功武略彪炳青史者比比皆是,但我们这一支大体无可攀附—出生不久举家迁出,随着在县供销社、乡镇机关当小干部的父亲辗转于县城和半山区村落之间。从我上小学三年级开始定居在一个叫小北沟的仅五户人家的小山村。小山村很穷,借用韩国前总统卢武铉的话说,穷得连乌鸦都会哭着飞走。任何人都不会想到,那样的小山沟会走出一个据说有些影响的翻译家。说白了,简直像个笑话。 回想起来,这要首先感谢我的母亲。上世纪60年代三年困难时期如果母亲不把自己稀粥碗底的饭粒拨到我的饭盒里并不时瞒着弟妹们往里放一个咸鸡蛋,我恐怕很难好好读完小学;其次要感谢我的父亲。爱看书的父亲有个书箱,里面有《三国》、《水浒》和《青春之歌》、《战斗的青春》等许多新旧小说,使我从小有机会看书和接触文学。同时我还想感谢我自己—感谢自己对看书毫不含糊的痴迷。我确实喜欢看书。不喜欢说话,不喜欢和同伴嬉闹,只喜欢一个人躲在那里静静看书。小时所有快乐的记忆、所有刻骨铭心的记忆几乎都和书有关。现在都好像能嗅到在煤油灯下看书摘抄漂亮句子时灯火苗突然烧着额前头发的特殊焦糊味儿。 这么着,最喜欢上的就是语文课,成绩也最好。至于外语,毕竟那个时代的乡村小学,没有外语课,连外语这个词儿都没听说过。升上初中—因“文革”关系,只上到初一就停课了—也没学外语。由外语翻译过来的小说固然看过两三本,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个真正的人》以及《贵族之家》,但没有意识到那是翻译作品。别说译者,连作者名字都不曾留意。这就是说,我的少年时代是在完全没有外语意识和翻译意识的意识中度过的。由于语文和作文成绩好,作为将来的职业,作家、诗人甚至记者之类倒是偶尔模模糊糊设想过,但翻译二字从未出现在脑海,压根儿不晓得存在翻译这种活计。一如今天的孩子不晓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革的是什么命。 阴差阳错,上大学学的是外语日语。不怕你见笑,学日语之前我不知晓天底下竟有日本语这个玩艺儿。以为日本人就像不知看过多少遍的《地道战》、《地雷战》里的鬼子兵一样讲半生不熟的汉语:张口“你的死啦死啦的”,闭口“你的八路的干活?八格牙路!”入学申请书上专业志愿那栏也是有的,但正值“文革”,又是贫下中农推荐的“工农兵大学生”,所以那一栏填的是“一切听从党安排”。结果,不知什么缘故—至今也不知道,完全一个谜—党安排我学了日语。假如安排我学自己喜欢和得意的中文,今天我未必成为同样有些影响的作家;而若安排我学兽医,在农业基本机械化的今天,我十有八九失业或开宠物诊所给哈巴狗打绝育针。但作为事实,反正我被安排学了日语,并在结果上成了日本文学与翻译方向的研究生导师,成了大体像那么回事间或满世界忽悠的翻译家。 不过,我没有受过专门翻译训练。既没有上过翻译专业学位研究生班,又没有攻读有关学术学位。那么,这是否意味翻译不必做这方面的努力呢?回答是否定的。就此我想说两点。一是—上面我说过了—我自小喜欢看书,喜欢文学,这培养了我的文学悟性、写作能力和修辞自觉;二是大量文本阅读。即使在批判“白专道路”的“文革”工农兵大学生时期,我也读了多卷本《人墙》、《没有太阳的街》等日本无产阶级作家的作品。读研三年又至少通读了漱石全集。这打磨了我的日文语感,扩大了词汇量。我教翻译课也教三十年了,深感如今的大学生、研究生缺少的恰恰是这两点。而若无此两点,那么,哪怕攻读十个翻译专业学位,哪怕再歪打正着,恐怕也是不大可能成为翻译家尤其文学翻译家的。在这个意义上,我成为翻译家,既是歪打正着,又是水到渠成的结果。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