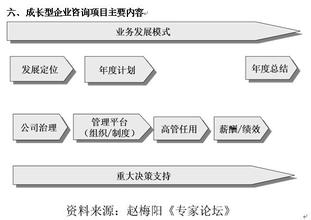科龙再次易帜,在民企格林柯尔没能拯救起科龙之后,科龙带着复兴的愿望选择了来自山东的国企海信集团。回溯到2001年,作为顺德最后一个“待字闺中”的“靓女”,历经磨难的科龙“出嫁”给在香港创业版上市的格林柯尔企业发展有限公司,此次科龙股权的转让实际上标志着顺德十年改制终于走完最后一步。
我们还可以把目光投射到更早些时候的顺德改制:万家乐重组、神州联姻、美的MBO、华宝外嫁等等,为国有(公有)资本的出路,顺德设计了种种的操作路径,这场声势浩大的产权变革实践中,顺德已经进行了很多开拓性的实践。
但告别的时代已然来临,从早期的华宝到万家乐再到现在的科龙,那些一度在政府主导时代辉煌的大企业,在如今的资本时代开始突然显现出资产的黑洞和资质的虚弱。像科龙改制这个被尊为中国产权制度改革大潮中的“旗帜”在不到4年的时间内却轰然倒掉,有人甚至由此还提升到“产权改革从理论到实践的破产”的高度。是产权革命惹的祸?是企业运营机制问题?还是其它?这些无疑值得我们去探讨,去对顺德十年改制的重新认识。
无可否认,由政府主导和推动的产业发展模式发展到由资本、市场和经营者所主导和推动的产业发展模式,顺德用了十年时间。但在十年的时间跨度中,顺德当年在“敢为天下先”的勇气下,许多先行先试的开拓性实践开始呈现出时间考验的“后遗症”,科龙也只是一个例证而已。
行政手段下的快速断奶
顺德的经济发展主要是两种思路,一方面是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由少变多,由小到大,再进行大集团发展的裂变式模式,主要代表是美的、科龙;另一思路是实现对所属的公有制企业进行改制整合,采取聚变模式,万家乐就是这一模式的典型。无论是哪一种思路,当年都是以“市(县)、镇两级政府向银行担保,以负债经营方式”发展起来的,“用钱银行贷,还贷下一届,经理用钱,厂长负盈,政府负债”,就是当时顺德企业的真实写照。
在这种大环境的推动下,企业为了取得快速的发展,通过政府信用担保的“保驾”,采取了高风险、高负债、高速度的发展模式。随着那个著名的题为“触目的成果、惊心的包袱”的调查结果出来,顺德才开始觉醒,才走上改制之路。
一手缔造出“神州”品牌名声在外的原神州热水器副总博锋认为:“以目前来看,许多企业的行政断奶期太早、太急,过早地将企业放到背水一战的地步,许多逐渐走向成熟的企业因此而走向颓废。而且,当时的客观市场环境和秩序并不成熟悉,顺德的改制是用‘小市场’的眼光来看中国的大环境,颇有点堂吉诃德的改革精神,随着90年代中期税改和宏观调控,许多企业发展不如意,并进一步发展到资金断裂。”
正是这种存在问题的改制过程,让这些企业带着问题上了路,为日后埋下隐患,而对于改制后的企业,有关部门也采取“一卖了之”的态度,不再关注企业的发展,导致问题暴露的时候,就已经是情况严重恶化的时候。
政府的不完全退出
另一个极端是,虽然众多企业名义上完成了转制,但政府继续在干预转制企业的经营,因为大部分转制企业政府占的股份还是绝对比例的。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赴科龙调研组的研究,以前的改革叫“稀释型”产权改革,并不是“退出型”产权改革,即直接把公有性质的产权出售给非公有制企业或个人。由此,政府财政负担的加重相应的转化到转制企业中,使得转制企业经营步履维艰,加上整个经济大环境的疲软,转制企业的出路不明。
像科龙,科龙是镇办企业,但创业者和中层骨干与当地重要政经人员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即便有强势人物潘宁的引领,科龙亦不能幸免世纪之交中国乡镇企业遭遇的普遍掣肘,即政府对企业的主导乃至干预。在容奇镇,镇政府通过容声集团控股科龙,集团与政府实为一体,集团董事会即为镇政府领导班子,既在政府领薪,又在上市公司获利。同时,由政府官员和企业内部中高层衍生大批裙带企业挂在集团公司名下,向上市公司供货,包揽上市公司销售,导致科龙成本高企,冗员繁多。
以政府掣肘来说,决不是只有科龙一家,当年神州转制时也遭遇政府的强烈主导,一是转为民营,同时又强迫与德国博世联姻。万家乐与东芝的合作也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可以说,这些企业的亏损与低迷都是与政府的不完全退出有莫大的关系。
《大道苍茫——顺德产权改革解读报告》一书的作者徐南铁也指出:“政府是不可能完全退出,掌管企业的行为太久了,不是说退就能退的。”
徐南铁还认为:“改革肯定是有成本的,但政府的不完全退出肯定会产生成本,这也说明原有的利益集团并没有打破,改革还不彻底,还需要深化。”
改革成本由企业负担?
卖地还债是今年万家乐为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而进行的动作。20年前,万家乐以“政府担保,负债经营”的方式开始起家,随后进行了大量的关联债务担保,财务状况日渐恶化,顺德政府的做法是给予万家乐大量商住用地折抵债务。
“万家乐今时今日的局面主要原因都可以归根于顺德政府改制的必然社会成本,万家乐的主要精力之一就是解决历史遗留债务问题,”但让万家乐郁闷的是,这些债务是由于万家乐为政府主导下的集团公司作了大量的关联债务担保并且直接占用大量的资金。“进行产权改革政府不能够把包袱留给企业。这个代价不应该由企业、不应该由股东、由投资者来承担,政府既然来搞改革,你有责任也必须承担这个改革的代价。”
在顺德政府大楼的原来有一个叫顺德市公有资产管理办公室的机构,成立之初,它的主要职责是管理顺德庞大的集体资产,但后来它们的主要精力放在了处理顺德企业、政府和银行之间债权、债务纠纷之中。
顺糖集团是顺德第一家转制的国有企业,但转制八年后,仍然有一些历史债务没有解决。债务产生的原因是,原顺德市华宝陶瓷厂欠顺德糖厂下属发电厂电费,由于华宝陶瓷厂是市属国有企业,现已倒闭,所欠的债务也就挪到了顺德政府头上。
银行的债务悬空是另一个表现。政府成立一家转制的控股公司,来负责转制后企业和银行之间债务的衔接,结果是企业有钱赚也不用归还银行的借款,这种现象却普遍存在。
转制中的共产主义思想
转制十年中,顺德打造出了科龙、华宝、容声、格兰仕、万家乐等驰名商标,但同时,神州、希贵、爱德等当年风光无限的品牌也在沉沦之中。
造成这些品牌变化的背后是产权的改革和环境的变化,从企业家角度来说,当初如日中天的企业家是时代的“英雄”,是在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历史条件在特定企业中拼杀出来的英雄,他们的成功首先得益于广东的改革风气之先,但后来在心态上过多迷恋于自我成功的膨胀,过分自信使得他们忽视了市场境的变化,而没有成为“成熟的企业家”,因此,在产权改革后,企业运作经验不灵了。
同时,当时的决策者并没有站在企业家的高度,在企业转制后行为有点矫枉过正,即从转制前的冒进到转制后的保守,缺乏企业家的大气和长远规划。比如品牌宣传方面,因为自己投资的钱,使用时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使得一些正在成长的品牌夭折和优秀品牌的老化。
曾任三洋科龙营销总监的沈关学也深有同感:“成功的惯性让当初那批企业家很少从成功走向卓越。”
锋还分析到:“以今天的眼光来看,顺德当初的转制多少还带有共产主义和‘大锅饭’的成分,如全员持股,从员工心态上来看,还是和转制前一样,都是企业的主人,同时,又因为自己拿了钱去持股投资,趋利心态下不免有点急功近利,并作出些不轨行为。”
从顺德企业用人的因素来说,当初顺德企业对人才的重视并不是发自内心的,很大程度上是利用而不是重用,90年代初,外地人常被称为“山佬”。所以,转制时有条件给予股份的也是很少的份量,而且,十年前,懂得品牌运营的经理人阶层并未成为一种新势力,而进入到顺德企业的决策层中,因此,很多企业因为没有新鲜的血液的冲击而就此消失。
从姓“资”姓“社”到姓“国”姓“民”
历史总在跨越,从最初华宝的“靓女先嫁”时,争议放在了姓资还是姓社的立场,而今天科龙的改制,目光对准的却是国有资本还是民营资本的问题。曾在华宝、科龙都做过中高层管理的胡启志就很鲜明地指出:“说白了就是卖给谁的问题。”
随着十五大的召开,全国各地的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纷纷加快了产权改革的进程,许多地方政府都非常重视推动公有资本从一些竞争性行业的企业实现有序退出,鼓励合适的民营企业以及外商购买那些公有资本拟退出的企业。从产权改革的角度来讲,内容远不止此,它还包括政府在什么样的企业拥有股权,以什么样的方式拥有股权,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建立产权明晰的现代企业制度。
在顺德,活得较为滋润的转制企业中,美的、格兰仕是典型。美的是最早实行改制的顺德上市企业,1997年,美的经营遇到了严重困难,镇政府决定对美的实行改制。设计了一个方案:成立一个控股公司,把多余的一些东西放控股里头,让它度过难关后,通过它的发展反过来把剥离出来的那些东西逐步逐步加以消化。后来,美的又成功实现了MBO。而格兰仕的转制则是政府反复调整所持的股份后,全面地一次转制成民营。

但从目前来看,民营资本并没有拯救起科龙,万家乐民营化之后没有复兴、神州也没有重振,科龙此次选择海信,会不会又是一次伟大的尝试还不得而知,但对于姓“国”和姓“民”的两种国内资本来说,选择冲突将有可能日益激烈,而各种力量都在不断演化之中。
欢迎与aihuau(爱华网)专栏作者肖南方探讨您的观点和看法,电子邮件:[email protected]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