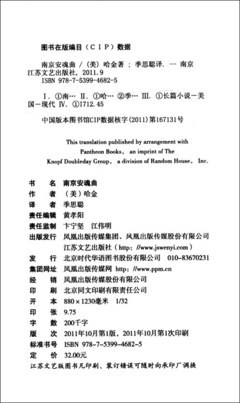想象一下,2012年底,当纸版《新闻周刊》推出自己的最后一期,封面将会是什么?像《世界新闻报》那样,一行悲情大字“ThankYou&Goodbye”?还是“MerryChristmas(forthelasttime)”?我想,也许总编辑TinaBrown会拷贝这本杂志在2007年11月26日的做法。那一期的封面是“Booksaren’tdead.They’rejustgoingdigital”(《书本不死—他们只是数字化了》)。现在,她只需要改几个字就行了,“Newsweekisn’tdead.We’rejustgoingdigital”(《新闻周刊》不死—我们只是数字化了)。这比较符合她一贯嘴硬、死不认输的风格。在宣布停止出版纸刊时,TinaBrown对媒体说,杂志将“拥抱全数字化的未来”,“我们正在让《新闻周刊》转型,而不是向它说再见”。

2007年的《新闻周刊》封面探讨了数字技术的话题、新媒体的冲击之下,印刷书籍的未来在哪里,是否会像很多人预言的那样“死去”。五年前,周刊给出的预言是书籍不会死,只是改变了自己的存在方式,将变身为电子书。不过,他们没有预言到的是,五年后,他们就将“身先士卒”,率先数字化了。 不过,这种转变看起来并不是那么主动和心甘情愿。事实上,《新闻周刊》并不想放弃纸质版,一直在苦苦挣扎求生存。从2007年开始,杂志连年亏损。近2009年,亏损大约280万美元,广告收入下降37%。 已经经营了《新闻周刊》近半个世纪的华盛顿邮报公司“无力回天”,于2010年5月开始为周刊寻找新东家。当时,中国的博瑞传播与南方报业集团联合参与对《新闻周刊》的竞购,但其收购意向第一轮就被华盛顿邮报公司拒绝。当时的中方负责人声称,竞购失败主要是因为华盛顿邮报公司“不真正了解中国有理想的媒体人、媒体机构的愿望”。最终,周刊以一个离奇的价格卖给了一个离奇的买主。2010年8月,华盛顿邮报公司宣布把《新闻周刊》以1美元的象征价格出售给音响大亨悉尼?哈曼。3个月后,哈曼国际工业集团宣布把《新闻周刊》与成立仅两年的新兴新闻网站Dailybeast合并,成立NewsweekDailybeast公司。当时的Dailybeast总编辑TinaBrown也就顺理成章地同时成了《新闻周刊》的掌门。 TinaBrown曾被《哥伦比亚新闻评论》评为“当代最伟大的杂志编辑”。她在2011年3月对杂志进行改版,比如把“视角”(Perspectives)移到杂志前面,并在杂志前面部分给了专栏、编辑和特约作者更多的版面,同时整合了Dailybeast网站的内容。但曾经主政《名利场》、《纽约客》等著名杂志的“杂志女王”,最终并未能拯救《新闻周刊》。2011年,哈曼去世后,他的家人决定不再资助《新闻周刊》,周刊遂归Dailybeast所属的美国互联网巨头IAC公司所有。而IAC的掌门人最近爆料,周刊最近仍然未能走出亏损泥潭。 纸版《新闻周刊》的结局确实让人伤感。1933年当托马斯?马丁决定创办这本杂志时,信心满满地说,除了《时代》外,一定还有另外一本新闻类周刊生存的空间。80年后,马丁的后来人却让这本杂志失去了生存空间。 不得不承认,从长远来看数字化的潮流是不可逆转的。但是我们不能武断下一个否定的结论。在2011年出版的热门书“TheMasterSwitch”(《大变迁:信息帝国的兴衰》)回顾了美国历史上的媒介技术变迁史。从电话、广播、电视到互联网,每一次新技术革命出现的时候,都引起了无数人的恐慌—旧媒介将死去。但当过了一段时间,我们会发现,旧媒介并没有被新媒介全面取代,甚至重又焕发青春。最典型的例子是广播,以中国为例,随着中产的兴起带动汽车消费热,如今广播和广播媒体的影响力完全超乎想象。同样的道理,纸质印刷和纸质媒体也许不会在数字技术的冲击下一败涂地,完全消失,只是可能会换一种生存方式。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