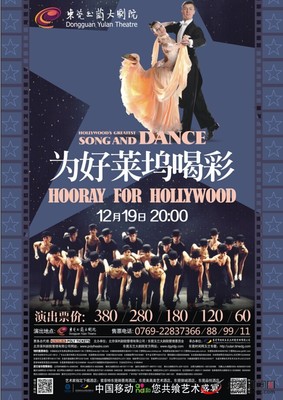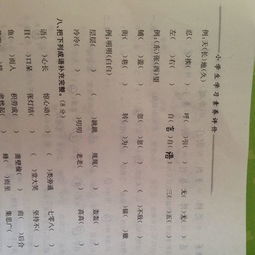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文余智骁/译
创新是低效的。创新行为通常都是无章可循、触犯众怒的,并要求打破旧习;疑惑和矛盾是滋生它的沃土。简而言之,进行创新公然违背了几乎所有的父母对孩子的期望,违背大多数CEO对公司的期待,违背国家领导人对国家的希望。主张创新的人就如屁股上的伤痛,让人厌烦。
然而,如果没有创新,我们注定要因为厌倦和单调而退化。创新如何发生?新想法源自何方?最通常的答案是:提供良好的教育体制,鼓励不同的观点,培养协作精神——这一切都不足为奇。而且,美国已经从满足以上几项标准中受益匪浅。但是为了保证新想法源源不断地产生,还有一些东西必须改变(高等教育的性质就是要改变的东西之一)。
良好创新系统的基本要素之一就是多样化。从某种意义上说,一种文化的自身力量越强(无论是国家的、制度的、代际的还是其他类型的文化),它就越不可能孵化出创新精神。习以为常和根深蒂固的观念、广为流传的规范,以及各种行为标准都是产生新想法的敌人。任何以和谐以及均衡为骄傲的社会,几乎不可能诱发另类思想。扼杀创新精神不需要公然进行。它可以是非常简单的事情:比如人们散步时遵循默许的契约,人们对自己的社会状况非常满意。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非同一般的文化通过国民的品性孕育创新精神,而那些国民都从不同角度来看问题。美国(所谓的大熔炉),在很多人看来,没有什么“文化”传统可言。在上个世纪中,美国人大约获得了三分之一的诺贝尔奖,还制造了一股无人能敌的创新浪潮(从工厂自动化到集成电路到基因编码等),这股浪潮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关键。
我认为这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我们没有轻视那些不停尝试但没有成功的人。实际上,很多风险投资家更可能投资那些起步较早而且已经失败过的人,而不是那些第一次创建公司的人。真正可悲之处是,人们不从失败中学习。
另一个原因是,我们愿意听取年轻人的意见,这是我们特有的。在很多文化中,年龄所占分量太大了。经验比想象力更重要,尊敬异化成过度的谦卑恭顺。在一些文化中,人们根据年龄因素分配工作,这使得年轻人长期处在一种压抑的环境中。还记得下面这句话吗?“孩子是用来看的,而不是用来听取意见的。”好,那我们就来看看像比尔·盖茨和迈克尔·戴尔(我只是随便举两个人的名字而已)这样的“孩子”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情况。他们在那么年轻时就获得巨大成功,这绝对是好现象。然而,在教育年轻人方面,我们还应该做得更好。我尤其关心早期教育,不幸的是,它(通常)对创造力的培养产生消极影响。我们太热衷于为孩子们的成功而手舞足蹈了,以致我们没有真正去了解他们到底在学什么。其实,真正更应该让人激动的是孩子所犯的错误。甚至“错误”这个概念也应该引起注意。正如一些孩子们猜测的,风不是由树叶的颤动引起的。但这种猜想就很有意义,不应该被简单地忽略。实际上,消除对概念的误解是发现新想法的最好方法之一。这个过程和调试计算机程序相似,和作为学校教育基石的训练、实践行为几乎没有任何关系。
营造富有创新精神的文化的最大难题,在于找到能鼓励不同观点发表的途径。很多工程方面的难题都是被那些不是工程师的人破解的。这仅仅是因为观察问题的角度比智商更重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观察角度不能使孩子们考上大学,也无助于他们在那里出类拔萃。学术奖赏的是深度。专家意见是由专家得出的,而这些专家都和他们的同行一起工作。各个部门和实验室都将精力集中在各自领域和子领域中。研究生,更不要说长期聘用人员,需要的是挖掘事实真相,然后在很窄的领域中发表自己的观点。
治疗这种窄化和细化现象的药方是提倡跨学科研究,虽然“跨学科”这个词很老套,而且在一些前沿研究中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目标。跨学科实验室和研究项目最早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目的是解决横跨物理、社会科学、工程和艺术几个领域的重大问题。当时的想法是,利用各种知识的互补性,来研究跨越单一技能范畴的问题,非常好。但是最近,人们意识到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能够给一些非常小的问题带来巨大的价值,跨学科的学术环境也能够激发出创造力。如果把事物背景、文化、年龄等的差异性最大化,我们就更可能得到和原先设想不一样的结论。
孕育新想法还需要另外两个因素。两者都与将“偶然发现”发挥到极致有关。首先,我们需要鼓励冒险。冒险在事业发展过程中尤其困难,还会经常冒犯同事,并触犯团体发展的相关机制。这仅仅是因为冒险本身可能会显得相当愚蠢。面临困境的冒险者容易失败并遭到奚落,因此他们必须在身边找到支持,假如找不到,他们违反常理的想法将不被理解。
第二个因素是,鼓励心态的开放和观念的分享——这也是几乎不可能达到的老套的目标。在数字泡沫的高峰时期,对计算机专家来说,做到观念的开放尤其困难,因为他们看到财富来自于不分享彼此的想法。学生们会把好想法保留到毕业以后。一个人把自己的牌盖得很严,另一个人也学他,结果很多实验室的价值和效率都下降了。还好,谢天谢地,数字泡沫已经破灭了。

不多年以前,贝尔实验室开展了大量的研究活动,因而它能完成一些高风险的项目,包括一些所谓的“无价值”的理论研究。事实上,这些研究最终导致了信息理论的产生和宇宙电磁波的发现。而且整个世界都从中受益。AT&T也做过些类似的贡献。不过,现在的贝尔实验室只是以前的影子,从1984年与AT&T拆合,到后来与朗讯、NCR拆分,贝尔实验室分化了好几次。并不是贝尔实验室才有这种遭遇。随着经济滑坡、公司削减开支,首先被精简的是那些高风险、成果对世人公开的研究项目。即使研究预算不下降,项目的性质也更倾向于发展性而不是创新性。假如这种趋势继续下去,最终我们将遭受新思路匮乏之苦。现在,越来越少的大公司把精力集中在提出新思路上。开发新思路几乎陷入了停顿状态。
在新出现的“新经济”中,研究和创新工作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出现在那些有多个项目和多种支持的地方。适于开展跨学科研究的大学满足这一条件,因为大学除研究之外,另一“产品”是“人”。然而,边研究边学习,可能要冒更大的风险,新想法的产生也可能更低效。现在,只有少数几所美国大学可以属于这样的“研究型大学”之列。更多的大学应该加入这个行列。世界其他国家的大学也应该加入。
产业发展需要利用基础研究的成果,正如前者利用其他条件一样。这意味着,创新必须要有前瞻性。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就明白了这个道理,当时,日本国际贸易和产业部(现在的经济、贸易和产业部)资助了日本数家公司合作开展机器人、人工智能和半导体方面的研究。尽管这种方法并不始终有效,它的效率还是可能比大多数公司预计的要高得多。成本是分摊的,不同的观点是分享的,即使在最困难的经济时期,创新也有存在的理由和机会。
勇于创新的人的共同特征是,具有很强的跳跃思维的能力。通常这种能力只有那些有丰富背景知识、跨学科思维方式和丰富实践经验的人才会拥有。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