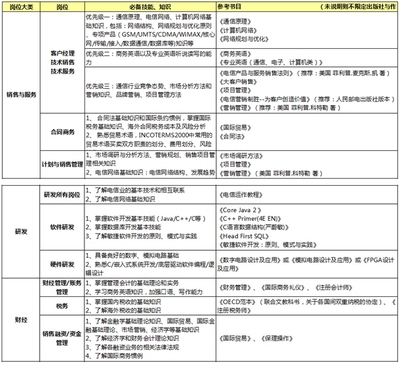在中国科技界,华为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高峰。这家低调而神秘的公司以匍匐前进的姿态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增长奇迹,成为了国内乃至全球科技界效仿的对象。军人出身的任正非被视为“经营之神”,偶尔流传出来的只言片语被无数经营者视为至宝,其2000年撰写的一篇文章《华为的冬天》至今仍是许多企业家争相学习的摹本。宗庆后之女宗馥莉说“娃哈哈减去宗庆后等于零”,任正非之于华为更是如此,在华为,任正非的股份只有1.4%,但他是华为的灵魂人物和精神支柱。
极致性价比的大客户营销2011年,在任正非的主导下,华为制定了未来十年年销售额突破1000亿美元的目标,并将华为分拆为“运营商”、“企业”、“消费者”三大业务集团。二十年来,华为习惯了面向运营商的那一套打法,而消费者市场却变幻莫测,很多著名手机企业都交了学费。比如,爱立信长期坐在电信设备供应商第一把交椅上,但面对消费市场却束手无策,眼看着苹果、三星等后来者风光无限。
电信工程市场要求在拥有同等技术的前提下,将价格降到最低。华为客户战略的第一条就是:“不卖最贵,只卖最好;不仅低价,更为优质。”2008年中国电信CDMA招标大战中,中兴、加拿大北电、阿朗等报价都在70亿元以上,而华为报价仅7亿元,痛痛快快地秒杀对手。华为内部流传一个“王小二卖豆腐”的段子:王小二开了家豆腐店,卖两块钱一斤。有人看见王小二赚钱,便在王小二对面开店,王小二不得不降价到一块五。竞争者的豆腐店越开越多,王小二不得不将价格降到八毛。最终,王小二豆腐店倒闭。华为的做法是直接将价格降到八毛钱,让所有想开豆腐店的人看不到“钱景”,没有竞争对手,华为自然就能生存下来。

与竞争对手不同,华为的产品定价有着自己的商业逻辑。摩尔定律揭示了IT技术的曲线规律,在华为所在的电信设备市场,也有着类似的规律,随着技术更新换代越来越快,一项新的技术到量产阶段后,成本就会大幅下降。华为洞悉这一规律,并以两三年后量产的价格作为现在的定价,即便头两三年亏损,但量产之后,华为就能保持合理的利润。1998年,UT斯康达在接入网上每线报价1800元,华为报出800元的超低价,此后UT斯康达消失,华为垄断70%的市场份额。华为用独特的低价定价法则,在全球市场攻城略地,消灭对手。这种打法看起来与传统行业的价格战类似,实际上有着本质的不同。在消费者市场,品牌是生存的根本,而在工程市场,价格才是王道。比如,空调行业的价格战都是以强大的品牌号召力为基础,杂牌军参与价格战游戏只有死路一条。
移动互联网的爆发让电信运营商的核心业务—语音通话业务严重受损,巨额的设备投资正在迅速贬值。市场的巨大变化以及日趋白热化的价格竞争,致使电信行业一片愁云惨雾:2012年,爱立信净利润仅录得9.3亿美元,下滑53%;阿尔卡特朗讯亏损13.7亿欧元;中兴通讯巨亏人民币25亿元。华为是唯一逆市增长的巨头,2012年其净利润高达人民币153.8亿元,同比增长33%。尽管华为有着华丽的报表,但要在电信设备市场上保持这样的高增长,将越来越困难。在北美这个占了全球1/3的市场上,它的竞争对手爱立信、阿尔卡特朗讯、三星做得风生水起,由于政治原因,华为等中国企业一直被排挤在外。
十年来,全球电信设备市场规模维持在1200亿美元上下,华为占据了大约20%的市场份额。据此计算,华为要达到千亿美元的年销售目标,即便拿下全球电信设备市场的半壁江山也无法实现。电信设备市场的天花板触手可及,迫使它必须在企业及消费者市场寻找新的增长点。这不仅是战略层面的转型,更是思维意识的大改变,也意味着华为要转变过去的工程市场思维模式,学会与单个消费者打交道。
但消费者市场是一个新的战场,产品、品牌、营销、渠道都是新的玩法,华为能适应吗?工程师主导的华为能建立一套以消费者为中心的营销体系吗?华为追求极致性价比的大客户营销玩得转消费者市场吗?二十多年来,狼性文化让华为攻无不克,而这一次华为面对的是新的堡垒,在苹果、三星、联想等世界级竞争者的包围下,华为还能像以往一样战无不胜吗?回答这些问题,就要从华为的基因说起。
全员持股的负面效应
有人曾用两个字总结华为超常规发展的原因:分享。在中国科技界,华为无疑是最善于分享的企业。
任正非的思维逻辑很简单:既有利益共同体又有利益驱动机制,就能激活整个组织。在一次讲话中他对激励机制有过精彩的论述:“华为的快速成长主要是在竞争驱动下不断改善管理,完善激励机制和治理机制,使高素质的劳动者的创造力得到极大的发挥,形成良性循环。”在这一思路指导下,华为形成了一种“不让雷锋吃亏”的奋斗文化,也就是说只要员工肯拼搏、肯努力,就一定能获得高回报。无论是员工还是客户,华为都将他们视为利益共同体,把单纯的雇佣关系和商务关系变成共命运、同呼吸的合作伙伴关系。
早在草莽创业的1993年,华为就通过“利益共同体”这一新型的合作方式,度过了艰难时刻。当时,通信高科技产品属于典型的高风险投入,研发投人大,多则上亿,少则几百万元;产品周期长,多则三年,少则一年;产品和技术更新换代快,一个产品和技术刚刚开发出来,还没有应用可能就已经被淘汰;客户分布广泛、客户的需求多样化使得产品的升级维护成本居高不下。1992年,华为的销售额仅为1亿元,任正非要进入运营商系统,仅靠这点资金是远远不够的,唯一的办法是与客户建立“利益共同体”。经任正非多方游说,17个省市的邮电管理局下属电信公司出资3900万元,与华为共同成立了莫贝克公司,承诺每年定额投资回报33%。此后,华为迎来了高增长时代—连续十年,每年增长率高达100%。2001年10月,莫贝克(后改名为安圣电气)以7.5亿美元的价格卖给美国爱默生,是当年国内最大的并购案。华为从此迅速成长,最终成为中国科技界无可争议的王者。
不仅如此,华为还将员工视为利益共同体,并以全员持股的方式将企业的命运和员工的命运捆绑在一起。华为现有15万员工,其中7万人拥有股票。此外,华为员工还拿着业界最高的薪水和奖金。但是,作为公司的创始人,任正非只有1.4%的股份,其余股份为高管和员工持有。华为全员持股计划和高薪激励政策,让许多员工走上了“致富之路”。
虽然全员持股能起到了巨大的激励作用,但随着员工越来越多,这一体制的缺陷逐渐暴露出来:在华为高速增长期,华为每年的分红水涨船高,一旦加速引擎慢下来,变成富翁后的员工还能持续保持创业时的激情和奋斗精神吗?
每年4月,是华为的分红期,这是一个几家欢喜几家愁的月份。2012年,华为净利润153.8亿元,但仅分红就分掉了125亿元,相当于每股1.41元。消息公布后,老员工和新骨干心理感受大不一样:老员工喜,不怎么卖力就得到了不菲的分红;新骨干忧,自己干的是牛一样的活,花高价买来的股票,净收益却少得可怜。
产业观察者张云辉认为:“华为在最初发展的十几年里,股票分红激励的人群和干活的骨干人群基本一致,随着员工的老去和新增,分红激励人群和骨干开始逐渐错位。股票分红激励的是有10年工龄以上的老员工,而真正需要被激励的新鲜血液——那些真正干活的骨干,却很难从分红中受益。”此外,华为内部有近8万人没有持股,这部分员工只能通过奖金等进行激励,无形之中把华为分成了两个阶层。在高速发展期,这三个群体的矛盾无法显现,可是一旦公司处于危机时期,其负面效应就会显现出来,如果解决不好,甚至出现灾难性的后果。
尴尬的“空降兵”
从创办以来,华为一直有着深刻的任正非烙印。任正非军人出身,他强调集体主义,提倡艰苦奋斗的作风,要求团队有很强的执行力。华为文化特别强调“没有任何借口”。任正非眼中的优秀员工是像《把信送给加西亚》一书描述的那样,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克服阻力完成任务。这一企业文化往往能将不可能变成可能,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华为的年度KPI考核指标定得很高,公布出来的时候大多数员工都觉得完不成,但通过一年努力,当初定下的目标神奇般地完成了。
华为举世闻名的是它的快速响应,华为就像是一个万能机,只要提出需求,就能在短时间内实现。“一没有成熟的敏捷开发模式可以支撑,二总部跟大部分销售地都有时差,华为怎么能够做到快速响应?那就是它的工程师可以24小时倒班支撑,修改版本。”一位在华为工作多年的员工抱怨,华为崇尚以奋斗者为本,但到最后奋斗者往往变成了一个个“无限制的透支自己体力与青春的人”。
在高薪和高压的双重作用下,华为人往往发挥出惊人的能量,但是对空降兵却是一种煎熬。每一个新入职的员工都要进行军训和为期半个月的企业文化学习,这种训练新兵的做法让很多“空降兵”难以适应。“空降兵”要取到好的业绩,就必须在华为内部拿到足够的资源,但华为部门林立,没有广泛的人脉就很难调动内部资源,而没有足够的资源,就很难做出业绩,做不出业绩自然得不到认可。曾被任正非视为接班人的副总裁李一男在2000年离开华为创办港湾网络,2006年华为收购港湾网络,李一男回到华为出任副总裁、首席科学家,但此时的华为不再是过去的华为,没多久李一男再次离开华为。备受器重的李一男尚且如此,更何况其他“空降兵”?
华为的高级管理者很少有外国人,一是华为面向的是几百个大客户,涉及数以亿计的大项目招标时,自然而然会对外国人有一种防范心理,二是外国人很难适应华为无休止加班的工作方式。“在提交标书前一天晚上,部门领导要求将标书结构推倒重来,中方员工哪怕熬通宵、不吃不睡都会完成,但外籍员工就不会这样。”一位曾在海外工作过的华为人说,“在华为,工作第一、生活第二,但外国人不这样想。”由于价值观不同和对待工作、生活的迥异态度,外籍员工很难在华为呆得长久。
在华为,高层管理者经常转岗“锻炼”,例如华为终端董事长兼CEO余承东曾负责欧洲市场开拓,而华为俄罗斯市场负责人万彪曾是华为终端总裁。华为试图通过高管转岗锻炼的方式破除大企业普遍存在的“山头”现象,但由于全员持股带来的心理优势,老员工的地位很难被撼动。
自我纠错机制
某种意义上,成为华为人,就必须接受华为企业文化。华为不会受到外界影响,它的改变只能来自于自我纠错机制和自我反省能力。华为终端或许是最不像“华为”的业务板块,它像是一个独立的存在。
2011年余承东接手华为终端时,就试图将华为终端打造成一个真正面向消费者的手机企业,但让他感到苦恼的是许多“终端老兵”摆脱不了原来的运营商思维,不愿意自我革命。2012年,余承东开始对人事进行大调整,一批中高层管理者转岗或离职,一批来自三星、摩托罗拉、诺基亚的“空降兵”被高薪挖来。余承东大量聘请“空降兵”,使华为的血液里有了更多的外来基因。http://china.aihuau.com/与此同时,他强力砍掉3000万部功能手机,主导了与名声不佳的奇虎360特供机合作,还打破低调传统在微博上高声吆喝卖手机、抨击对手。余承东种种出格的行为差点让他“下了课”,所幸的是,任正非的宽容和谅解让他度过了信任危机。
作为华人商界的传奇人物,自我批评是任正非最醒目的标签。华为是一个有着近15万人的庞大组织,其复杂性远非外界所能想象,任正非以近70岁的高龄领导华为与时俱进、高速成长,靠的就是自我批评、自我纠错能力。任正非是一个具有危机感的人。2012年,华为的销售额达到2202亿元,超过爱立信成为全球最大的电信设备供应商。但这对任正非来说,并不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人在巅峰常常忘记悬崖的危险,“自我批评”、“不断改良”让任时刻保持着一种危机感。二十多年来,华为很少犯大错,正是源于任正非的这种恐惧感。
余承东锐意变革华为终端,与任正非的危机感、恐惧感以及华为肌体内与生俱来的自我纠错能力是分不开的。虽然华为的基因并非完美无瑕,但在任正非强烈的危机感驱使下,华为具备了强大的自我纠错能力,能够及时弥补基因缺陷,促使自己适时进化成一个更趋完美的企业。
只是,如果有朝一日任正非从华为退休,华为的自我纠错机制还能发挥作用吗?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