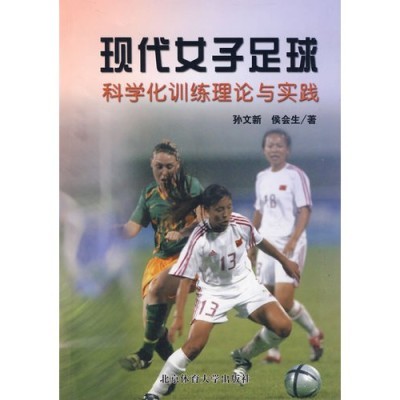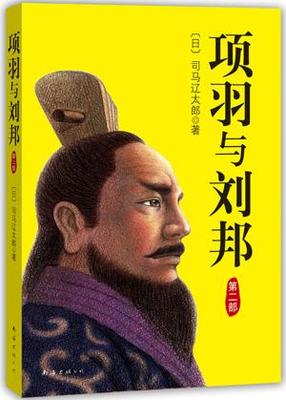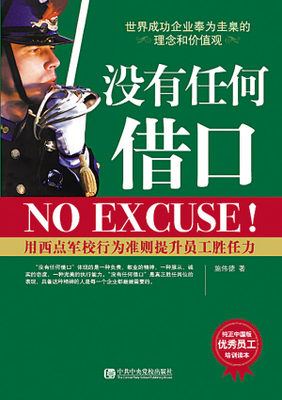伦敦奥运会是本月和同事们谈论的焦点话题。在这届盛会上,16岁小将叶诗文在女子400米混合泳比赛的最后50米冲刺中劈波斩浪,以比男子奥运冠军罗切特还要快0.17秒的成绩夺冠,并将该项比赛的原世界纪录提高了1秒多。接着叶诗文又在女子200米混合泳接力比赛中二度上演了最后50米的“逆天”冲刺。在排除任何高科技手段影响比赛成绩可能性的前提下,叶诗文此番表现可谓惊世骇俗。 接下来的故事早已被传得沸沸扬扬,中国反兴奋剂协司司长蒋志学称中国泳者自从抵达伦敦之后已经接受了近百次药物检测。“表现太好”的叶诗文夺冠后迅速被西方媒体的质疑声和爱国人士的支援声包围。纵观整个事件的始末,我们不难发现我们国内爱国人士特别是叶诗文的家乡人对于叶诗文充满人情味的维护。而更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西方社会对于规则的遵守和信任。而这种巨大的差别正是来自东西方思维方式的不同。 西方的基督教哲学认为人有原罪,因为“人性本恶”,所以主张以制度和法律来约束人,并认为有了好的制度,坏人也会做好事,没有好的制度,好人也会做坏事。 中国人则认为人性本善,通过道德教育,“人人皆可为尧舜”。制度是不管用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制度也是由人来制订和实施的,人如果学坏了,制度与法律也只不过是一纸空文而已。所以中国人讲究伦理教化,从人心这个根本上解决问题,儒学就是教人们如何做一个“君子”的学问。

两种思维方式带来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国民性格,我们很难简单地判断出孰优孰劣。这就如同美国人很难理解一群素不相识的中国人一见面的就能热热闹闹地打成一片,人声鼎沸的“人情文化”。中国人也很难理解西方法律的泛化、琐碎和复杂到了普通人根本搞不懂的地步,凡事都得咨询律师。 二种文化也各有各的弊病所在。亚里士多德曾说:“法律是没有感情的智慧。”法律主宰的社会,把人们隔离成一个个礼貌、有距离的个体。而同样在这些明确的规则下,人们能够享有高度的信任和自由。所以西方人的自由是以孤独为代价的。 在人性本善的前提假设下,社会对个人道德教化的重视高于社会制度的构建,把社会的长治久安寄托于个人修养。另一方面,在儒家观念中“礼缘人情”,“礼许变通”,人们在执行规则的时候才能充分地考虑到具体情况,人与人之间更能体会到温暖。但是事实上,由于重视“善”的培养的同时缺乏刚性的法制规范,所以中国人在是非面前比较情绪化,对于哪些应该做,哪些不应该做的界限十分模糊,“恶”的方面得不到应有的遏制,因此中国人处理事情更加地灵活变通,而这种灵活变通也极容易演变成为肆无忌惮、为所欲为。中国式的“人情”社会被人们诟病最多的地方也在于此。 于是在伦敦奥运会出现了这样的一幕,西方抱着对东方文化的“不信任”对中国的运动员“惊艳”成绩提出质疑。而东方人的“人情”观念让人们不加思考地群起维护冠军叶诗文。而我们所共同向往的社会、企业和组织的构建者们一定早已把眼光从两者的比较中挪开,转向如何依据社会现状来协调两种文化的平衡上来。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