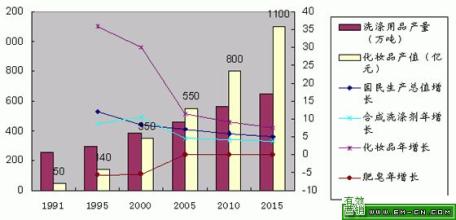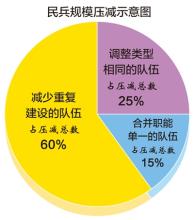今年3月,我受邀杭州讲学,绕道先去了一趟南京。到南京,是为了看朋友。马鞍山诗人杨键是老朋友,去年春天,本有一见,可惜未果;这回,总算弥补了遗憾。新朋友则有罗家明与老克,后又有文化记者罗拉拉;他们三人,都是昆迷,不时会相聚唱曲;昆曲虽说是小众,在南京却有一群这样子的票友。 罗拉拉是金陵名记,当然访问过许多的文化名人。她赠我一本小册子,剪裁了过去采访的某些印象。里头的文字清简,有兴味;常常寥寥数句,便把受访者的精神点了出来;偶尔又有闲笔宕开,颇见余韵,让我想起昆曲水磨腔的“一唱三叹”。这册子我先是读了一遍,返台后,偶尔想到,又翻了两三回;印象最深的,倒不是白先勇、陈丹青等名家,而是柯军。 柯军是谁? 且说,我平日行文,一向不喜大段地征引;但凡引用他人之语,经常才三四十个字,自己就不耐烦了。但这回,我愿意破个例。罗拉拉写柯军,有段采访稿是这么说的,“柯军至今难忘那些昆曲寥落的日子。1997年前后,他们随着团里的车子去常熟演出,到了之后,他们在装台,剧院的经理过来问:‘你们在做什么?’‘我们来演昆曲。’剧院经理不假思索地说:‘我们这里没人看昆曲的,上面答应给你们多少钱?’一台大戏,允诺的报酬是2000元,这个经理说:‘我给你们3000元,你们不用演了,走吧。’” 柯军是现任的江苏省昆剧院院长。1997年前后,那时,他还年轻,才三十来岁。 罗拉拉接着又写道,“再有一次去乡下演出,连乐队、演员一共几十人在台上演《风筝误》,台下只有三个观众,一个在睡觉,一个在游荡,还有一个在嗑瓜子。后来写《昆曲之路》的作家杨守松说:‘他把昆曲演员的心都嗑碎了’。” 这回之后,才隔一年,我就在台北看到了柯军。我看他演《夜奔》,初初几眼,很是讶异。完全不同于我很熟悉的裴艳玲的气愤冲天与满场火热,也迥异于侯少奎的高头大马且又声洪音亮,眼前的柯军,乍看之下,显得秀气,又过于文气,实在少了些热腾腾的血气。但隔了一会儿,我慢慢发现,这里头另有文章;柯军演出的内蕴,不仅有滋有味,且气韵绵长。看那台上的林冲,即使悲愤,即使煎熬,都不“洒”,不过度,不太甚;隐然间,还有些根柢之从容。我回头一想,恍然明白:柯军演的,其实是真正的昆曲。

1998年,江苏省昆剧院来台公演;此次,精锐尽出,连平常已不太登台的几位老演员,也都来了。迥异于在大陆的不堪与寂寥,这回,反应热烈、备受瞩目,诚为当年台湾之文化盛事也。台北的主办者,是位昆曲发烧友;办了一份《大雅》杂志,专门推广昆曲,一片痴心呐!台北有票文化人,面对省昆这群表演艺术家,既尊敬,又佩服。至于观众,那周齐聚“新舞台”,除极少数譬如我等这般粗枝大叶之外,其余个个衣衫端然、举止优雅;他们不仅看得津津有味,简直就已入了神。有别于早先登台的上海昆剧团或多或少仍有些通俗与外显,省昆这回的公演,其实让许多人开了眼界。亲见了这样的演出,大家才恍然明白:历史上所说的“雅部”,究竟雅到什么程度?而昆曲的水磨腔,又到底一唱三叹到何等地步?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