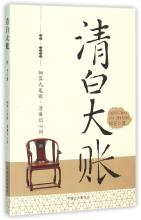在许多观察家看来,所有的社会分支都被1914 年8 月时那“燃烧的激情”所感染。社会民主党在帝国议会中首次投票赞成军事开支,公开接受德国是在为反抗专制主义而战的论点。在一次各教派于帝国议会前联合举行的礼拜仪式当中,众教徒一起颂唱新教和天主教的赞美诗;犹太教徒、女权主义者和同性恋者也没有感到受排斥。在汉堡,市议会通过决议,申明“商人和工人要携手并肩;团结一致,让每个人都能借助这种力量开始工作”;在整个战争期间,汉堡参议院盛赞当地社会民主党领导层“光辉”和“爱国”的举动。但是观察家们不可否认,早在1916 年甚至更早,参战国之间的休战协议就已经破产了。近来历史学家将其视为物质两极化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后果:战争导致阶级分化加剧,成了1918~1919 年革命的导火索。但迈内克的洞见似乎更有启发性,战争经济造成了个体自由和“以组织为核心的国家”权力之间的矛盾,后者追求“以技术主义、理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念分配定量配给卡”,这难免会导致强迫性。国家干预的加深—这是战争时期所必需的—带来了社会的进步,英国历史学家变得对这一观点深信不疑。简而言之,战争减少了英国社会的不平等。相比之下,德国在“一战”期间的干预措施却加剧了社会不平等,一些社会团体受到偏袒,另一些则遭到惩罚。战争期间,特定利益集团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比阶级关系更加重要。物质上的表现既反映了联邦官僚机构的日渐强大,也反映了经济集团的相对政治权力。 人力部署情况就完全展示了德国联邦的专制作风。显然,战争是很难让一个国家维持公平的,和那些留守在家里的人相比,那些被迫冒着生命危险在凄风苦雨的战场上厮杀的人牺牲了更多。一个国家的目标是在与敌军兵力相抗衡的同时,最大限度地提高国内食品和物资产量。以德国为例,战争头一个月的武装人员为290 万,而到了1915 年初,该数字升至440 万,到1918 年早期时更是达到了顶峰,增至700 多万。在1 300 万曾经在某个时间内“服过役”的人中,有240 万人丧生(占18%),430 万人受伤(其中有270 万人终生残疾);还有100 万人被俘。这批人的退出导致劳动大军出现缺口,虽然妇女(新增520 万)、战俘(90 万)和外来劳动人口(36 万)也加入了劳动力市场,但他们只能填补一部分空缺。当然,我们不用为每个阵亡的士兵贴个价格标签来说明战争带来的经济灾难。对比1910 年和1919年汉堡人口的年龄和性别结构,我们会发现人口损失空前惨重:战争不同于霍乱,死于战争的主要是男性。当然战争中一定程度的人员伤亡是不可避免的,但汉堡的人力损失高于平均水平:12 万被号召加入战斗的人中有34 519 人(28%)阵亡,13 482 人在战争结束7 年后作为战争伤员被登记在册。尽管女性雇员的数量增长了13%,汉堡的总就业人数在战争期间仍降低了28%。不仅如此,由于战争初期的军队动员相对缺少针对性,使得那些伤亡人员中包括不少熟练工人。 战争爆发伊始,德国的问题不是劳动力短缺,而是企业关闭造成的暂时性失业(见图2.10)。随着失业人口在8 月份逼近28 000 人(其中有9%的人来自“商业界”),汉堡参议院对这一问题表示忧虑,并进行了多次探讨—其诱因也许是帝国成立的中央职业介绍所,而不是群众的“起义、暴动、革命和一桩接一桩的入室盗窃案”带来的威胁。然而,较柏林受扰乱的程度(更不用说巴黎了)和随后的失业高峰而言,1914 年8 月的危机便微不足道了。码头是受影响最严重的区域,就业率在8 月期间下降了73%;但在9 月份,征兵的进行即刻解决了失业问题。汉堡– 美洲公司近一半的员工和40%的码头合同工应征服役。到1915 年1 月,博隆福斯等拥有大量军事订单的公司请求自8 月份被征召入伍的熟练工重回岗位;到1915 年12 月,该公司被迫首次雇用女性和战俘。 一方面,征兵的直接后果就是削弱了汉堡工会的力量,1915 年,工会总人数从142 799 人降至67 151 人,到1918 年则降至44 342 人,减少了70%。截至1916 年10 月,只有22%的船厂工人仍属于工会组织。工会支持者的缩减—1913 年那次未经工会同意的罢工以来,这个过程实际上就已经开始了—使得在国家层面出现的三方劳资关系体系在汉堡的有效性大大减弱了,德国最终于1916 年12 月颁布了《预备服务法案》。阿尔托纳的军方和参议院似乎都希望邦一级的调解和工会代表制能够减少码头区工人和雇主的争端,而且金属工人联盟代表科赫的妥协态度更让他们备受鼓舞。然而,码头区的对抗策略依然如故。就资方而言,博隆福斯企图通过延长工作时间和增加工作强度来弥补劳工的短缺,利用工会在这方面的弱势。初级管理者和工长有时会把这种对抗策略发挥到极致,以至于不得不在1916 年3 月出台相关规则反对对不顺从的员工使用某些言语,例如“你该被送到战壕里”等;一年后又规定一天24 小时的轮班工作强度过大。工人的反应则不尽相同,但大多是个体自发的行动,而不是诉诸集体罢工。博隆福斯船厂反复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工人缺乏纪律:延长午餐时间,工作三心二意,旷工现象普遍,此外还经常盗窃工具和适于做燃料的木材。最重要的是,由于工人从事的服务有很高的需求量,他们便借此频繁跳槽,劳工传统的高流动率创历史新高,以至于在1916 年10 月以后的一年之内博隆福斯不得不重新招聘10 000 名员工—《预备服务法案》认可了工人为获取更高薪酬而换工作的权利,使得这个问题更加严重。最终1914 年8 月达成的无罢工协议终于逐渐作废,很多工业区都是如此。1916 年10 月,博隆福斯船厂拒绝了工人涨工资的要求,引发了战争期间的第一次大罢工,4 个月后伏尔铿船厂也发生了大罢工,1917 年5 月,罢工事件重演;1918 年1 月的全国罢工潮在汉萨同盟城市也得到响应。 另一方面,战争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似乎能让社会更加公平。一些战略部门的劳动力短缺使一些原来的低收入群体(例如船厂的非熟练工)有了谈判筹码。无论是通过罢工还是换工作,金属工人的名义工资都能够显著增加;他们的报酬比许多受薪雇员还要多,那些认为战争造成了工人阶级贫困化的历史学家忽略了这一事实。1914 年7 月到1918 年10 月,博隆福斯船厂一般男性员工的时薪提高了113%(从64 芬尼增加到了136 芬尼);同样是这家船厂,其未成年工的收入比和平时期增加了85%,纺织厂工人则多收入74%。相比之下,初级文员的收入只涨了62%,图书管理员的收入涨了37%,而出纳的收入仅涨了30%。由此可见,所有群体的实际收入都有所下降,但体力工作者的情况略好于白领雇员(见图2.11 和图2.12)。在用工需求高涨,并且工人阶级的疏离引发了政治焦虑的情况下,这种成功证明了那些自发或“民间”的有组织行动的有效性。 然而,我们需要对这种社会“调平”的征象加以限定。战争经济的一个特点就是名义收入水平被严重扭曲,其差别取决于联邦对特定集团的态度。金属工人的工资要求之所以得到满足,主要是因为军方不希望潜艇等船舶的建造中止。政府愿意补偿某些集团因战争而导致的物质损失,这也导致了一些偏袒的现象。例如,那些海外资产受损的公司希望能即刻从公共资金中得到补偿,但成功与否取决于其是否能够成功游说柏林当局。这些是商行所没有的机构资源①。而阿尔伯特· 巴林则发起了为船东申请赔偿的运动,其策略展现出战时公司游说能力的进步。在阿恩特· 冯· 霍尔岑多夫(海军上将冯· 霍尔岑多夫的兄弟)的指导下,巴林把汉堡– 美洲公司的柏林分公司改造成了游说部门。身为普鲁士人,阿恩特去游说和宴请官员及政客最合适不过了;在维多利亚街(与拉特瑙的宅邸相邻)定期举行的“绅士之夜”,成为战时柏林沙龙活动的一部分,各大部长(包括黑尔费利里希、德尔布吕克、齐默尔曼和勒德恩)和政客们对此趋之若鹜,并且毫无顾忌②。与此同时,巴林委托德国船主协会秘书和帝国议会议员彼得· 斯图布曼动员议会支持赔偿船主的法案, 并且拉拢德意志官员,尤其是财政部官员维尔海姆· 古诺,并最终导致古诺离开政府机构,任职于汉堡– 美洲公司。柏林勉强接受了巴林提出的赔偿理由—船运公司是德国经济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它们在战争中的损失尤为惨重,政府对此负有一部分责任,而由于造船成本上升,仅靠保险金是不足够的。在漫长的争论过程中,船运公司的赔偿要求从5 000 万马克升至15 亿马克,之后政府最终同意按照战前价值对失去或被毁坏的所有船舶进行赔偿,对那些1914 年以来就被困在船坞里的船舶支付维修费,同时对于在战争结束后4 年内重建完成的船舶,政府要承担50%~70%增加的费用;如果完成期限再延后5 年,政府承担的比例则为20%~50%,充分反映出官方对通货膨胀的预期③。这笔资金会从1918 年开始预付给船公司(以新成立的帝国委员会发放贷款的形式进行)。④

帝国如此慷慨的援助实属罕见。然而,各联邦州显然也对小公司提供了类似的贷款和补贴。在开战后头几个月内,汉堡州联同汉堡几大银行共同成立了若干机构,旨在向小企业提供便捷贷款,以防止它们破产。1914 年8 月,汉堡用2 亿马克州立基金成立了按揭贷款银行,发行抵押债券(一种颇受汉堡小投资商欢迎的资产)担保贷款;但在战争年代该银行仅放贷3 000 万马克。为拯救处境艰难的贸易公司,1914 年成立了注册资本金为1 585 万马克(其中汉堡州政府提供了500 万马克)的汉堡银行,并在战争期间放贷近1 375 万马克。为援助那些业务“被战争破坏”的小制造商,汉堡用300 万马克的州立基金成立了手工匠援助银行;1914~1918 年,该银行共放贷259万马克,其中有42%的贷款在战争结束后仍未偿还。 这些贷款和补贴仅仅是战争期间的各种优待形式之一。同样,政府没能征收更高的直接税,这表明了经济活动具有极高的政治地位;经济活动—尤其是工业活动—对战时收入和财富的增加贡献最大。即使是在战时经济相对委靡的汉堡,各利益集团也成功抵制了税负的增加。汉堡的商业利益集团最极力反对的战时税收手段就是征收营业税,也就是从1916 年6月起对所有商业活动进行无息征税。由于商业贸易缺乏纵向整合,同时进口商品往往在市场上经过了多次交易,商业利益集团受到严重威胁。为了推卸战时的责任,马克斯· 沃伯格提出了一种替代方式,即向零售商和消费者征收成品销售税;在汉堡参议员的支持下,汉萨同盟商会最终对“中间贸易”作出重要让步,其中就包括豁免出口关税。最终营业税主要落在了从事小本生意的零售商、手工匠和制造商身上,而他们在商会中并没有代表。① 然而,州政府对“匮乏”问题的反应恰恰表明了这些缺乏组织的小型经济利益体的相对弱点。物资短缺,尤其是食物的短缺,最能威胁到战争期间的社会稳定;而当局对民众在这一问题上的不满反应迅速。1915 年3 月,Hammerbrook 因争抢食物而发生暴动,促使汉堡实施定量配给制度;1916 年8 月的Barmbek 骚乱催生了战争储备部;在1917 年2 月“靠芜菁甘蓝过冬”的悲惨境况迫使官方不得不增加土豆的定量供给。1918 年7 月,“尽管不缺工资”,伏尔铿船厂的工人还是因为“几乎吃不到土豆,(也)见不到水果蔬菜”而举行罢工。直到提供了额外供给,罢工事件才尘埃落定。增加供给显然是避免“那些被遗忘和剥夺了权利的人”—鉴于1905~1906 年爆发的事件,如此措辞意义重大—发生严重暴乱的最佳途径。然而,如果没有额外的供应,当局还有两种选择。正如社会民主党和消费者协会所要求的,可通过州政府统一采购和分配来补贴食品价格:在3.48 亿马克的战时总支出中,有8 000 万马克是战争储备部及相关前身机构的开支。另外,可以对批发商和零售商索要的价格进行管制。1914 年8 月,军方首次采取这一措施,限定某些商品的价格上限。但是,直到1915 年9 月联邦参议院颁布了成立物价监管委员会的法令,统一的价格管制政策才得以出台。1916 年10 月成立的物价监管委员会是由汉堡参议院为保护商业集团利益而精心筹划的。①但柏林对该委员会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要求其严格执行价格监管政策;尽管遭到连珠炮似的批判,但该机构并没有玩忽职守:仅在1917 年就成功起诉了1 538 起案件,导致5 551 家公司关闭,判处监禁共12 208 天,罚款共923亿马克。很多小企业主对此深感不满,纷纷在市议会上提出抗议;参议院发言人试图谴责缺乏经验的律师“对商业贸易的政治迫害”,但此举骗不了任何人。这个问题难以解决:柏林当局谴责商会对物价委员会施加压力;但实际上,委员会一直处于柏林的压力之下,商会的抗议信“由一个撒克逊裔的行政专员读完后就扔进垃圾桶了”。 为了取悦于广大消费者,通过实行价格管制,把商店主变成了替罪羊,以及物资短缺和货币扩张问题的罪魁祸首,但责任却根本不应由他们承担。战前曾是汉堡最有政治势力的集团—地产主—也被迫作出类似的牺牲。尽管大批人被赶上前线,但住房存量仍然供不应求,其原因则是战争导致的房产建筑业骤然下跌:1915~1918 年,汉堡的新建住房仅有1 923 套,而战前那两年的新增住房为17 780 套。由于战争时期要对房租进行一系列的管制,战争成了业主们的夙敌。地产所有者协会估计战争为其会员带来的损失可达8 000 万马克,其主要原因是强制要求战争期间汉堡一半以上的房屋租赁要降低租金。 总之,战争的重负要靠所有的德国人来承担。生活成本增长了240%,人均真实收入降低了24%,一般人均肉类消耗量减少了52%(见图2.13),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了每一个人。“一战”期间,德国的肺部疾病发病率增加,人口死亡率上升,生活日渐贫困。但名义工资差距缩小了,这也意味着船厂工人真实收入的缩减幅度(9%)远远不及高级公务员(52%)。换句话说,在1914 年,公务员的月薪大约是工人的5 倍;而到1918 年,这一差距最多不到3 倍。通过纳税申报单就可以证明这一“找平”的过程:1913~1916 年,前0.5%的纳税人收入的占比下降了。不仅如此,那些低收入人群也从基本食物和租金限价中的获益极少,而价格管制不够严格,未能抑制庞大黑市的发展,那些现金宽裕、在乡下又有熟人的城里人可以轻而易举地在黑市上进行买卖。最重要的是,战时管制对财富造成的影响千差万别。1913~1918 年,汉堡储蓄账户的数量上升了34%,而存款的平均实际价值却下降了69%。战争债券的发行也进一步扩大了债权人的范围。与此同时,政府管制也让某些现存的财富遭受损失。股票价值停滞不前,房地产市场也是如此。只有那些作为企业家直接为战争提供物资的资产阶级群体才似乎积累了一些财富:当然,沃伯格家族1917 年时在银行中的私人资产依然有2 280万马克,没有变贫困的迹象。 这些信息似乎都在指向一个结论,即战争使社会经济力量的平衡点发生了转移,从中产阶级转移到了工人阶级和大商业集团。借助物价和租赁管制就可以牺牲零售商和房产主的利益来为工人阶级提供生活补贴;或者限制公务员的工资,同时允许战略领域工人的名义工资增加。这使汉堡意识到其精英组织和工人组织之间的利益能够达成一致,早在1914 年之前就有迹象表明了这种可能性。军方显然看法相同: 上层社会的那一万人和待遇普遍提高的工人都能买到水果和新鲜蔬菜,他们没有必要担心高物价。形势对中产阶级和行政服务人员更加不利,他们承担的战争负担最重。 但我们不能错误地描绘战争的社会影响,即让那些处于资本家和劳工之间的小资产阶级受到挤压。战争经济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它对阶级内部各群体的影响各异。以施拉姆家族为例,这一位于汉堡金领阶层顶端的参议院家庭向世人证明,不只是中产阶级体会到了被剥夺的创伤。对露丝· 施拉姆来说,匮乏不仅仅是在物质上被剥夺,而且在精神和文化上是一种耻辱。“故作悲伤的冷漠的大众”、发战争财的投机商、1917 年的腐败和暴动—所有这些都是一种荒诞的嘲弄,嘲弄3 年前休战协议的理念。阿尔斯特湖上的天鹅成了餐盘里的肉饼,标志着汉堡的堕落;到黑市上买食物全然破坏了“我在1914 年以前为自己定下的原则”。当露丝的哥哥1918 年 12 月从前线战场回到家中,他发现父母在二楼收了房客,并且关闭了一楼,以节省取暖费。虽然他们仍用银汤匙吃饭,但他立刻意识到“大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结束了”。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