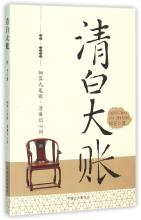与整个德意志帝国一样,19 世纪晚期的汉堡社会史似乎也是一部物质分配不平等和阶级斗争的历史。社会严重不平等的现象的确存在,对比汉堡旧城区贫民窟和沃伯格家族在白沙区如诗如画的避暑庄园的照片,我们很快就能发现码头工人和银行家之间的物质差距。虽然有组织的劳工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缩小了鸿沟,但我们不应过分夸大其历史意义,忽略其他社会力量。事实上,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驱动力同样重要。资本释放的经济能量使传统的城市社会发生转型;而要维持社会稳定,其关键与其说是其他阶级的态度,不如说是资产阶级自身的物质价值观和文化价值观之间的关联。 依赖阶级思想的危险之一在于,人们可能会无视19 世纪晚期城市社会非同寻常的流动性。1811 年,有132 000 人居住在汉堡;1913 年,这一数字增长了7 倍,汉堡成为德意志第二大城市。然而汉堡并不是人类繁衍的天堂:其人口出生率从19 世纪70 年代的高峰(39.4‰)跌落到1913 年的22.2‰;而死亡率仍在20‰以上,直到世纪之交才有所变化(见图1.3)。拥挤不堪的贫民窟、污浊的空气和落后的医疗卫生设备,使汉堡成了一个死亡之城,天花(1871 年)、斑疹伤寒(19 世纪80 年代)和霍乱(1892 年)等各种传染病肆虐。但汉堡经济的诱惑却让人难以抗拒。在1871~1910 年新增加人口的总数当中,有58%是外来移民,而在汉堡出生的人口比例不断下降,占不到一半。1907 年,制造业中只有35.6%的工人出生在汉堡,另外有1/3 来自北德,1/4 来自德国其余地区,还有5%来自国外。《Wanderlust》杂志认为劳动力的流动率一直偏高—只有1/3 的工人持续5 年以上从事同一份工作。 人们到汉堡是为了就业。1907 年汉堡人口中有46%的人就业,16~60 岁的人口的就业率为73%,70 岁以上男性的就业率为38%,未婚女性的就业率超过1/3;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工作就是体力劳动。1907年,近一半以上的工作人口(52%)被归类为“工人”;然而,这个标签过于宽泛,掩盖了工作本身的多样性。事实上最大的职业群体不是普通的工人阶级,而是家政服务人员,占工作人口的11.4%,且绝大多数为年轻未婚女性。由男性主导的体力工作包括修理工、建筑工人、海员和码头工人,也有相当数量的女性靠缝纫和洗衣度日。不仅如此,越来越多的就业者开始从事脑力劳动,而不是干体力活或手工活,由此也催生了更多的文案工作,以满足现代经济体和现代国家的需求。这些人就像艾本德的手艺人的儿子一样从事文职工作,当时的人这样描述他们:“每天早上戴着挺括的帽子,穿着白衬衫去到城里,他们不再是自给自足的小资产阶级—也就是那些有野心但是前途未卜的小资产阶级,这批人教育程度不高,日报是他们的主要知识来源。”最后还有一类能够“独立自主”的就业者:包括不动产所有人(约占工作人口的1/5),私营企业主和专家,还包括高级经理人(虽然有些不合逻辑,但却反映了他们与前者的地位相当)和公务员,其中人数最多的(近50%)是小商店店主或手工工匠—那时人们将这些群体视为传统的“旧”中产阶级的核心,就像他们把文职人员视为“新”中产阶级的主力一样。而“大”资本家则是极少数的职业精英,他们包括汉堡最大的公司所有人、董事和高级经理人,他们甚至比专业精英的地位还要高。 工作—是否有工作、难易程度和舒适程度、工作时长以及报酬—最能决定一个人的生活质量。从雇主的角度来说,劳动力市场的变动是双重的。一方面经济形势会影响到移民人数;另一方面,一些对季节波动敏感的行业,其雇佣情况也变动极大。这一点对于码头区来说尤其重要,相当一部分码头工人和造船工人都面临周期性失业。①与此相反,文员(尤其是在政府部门工作的13 000 人)的工作稳定程度较高。从工作环境来看,有极其恶劣的(锅炉清洗),有高危险的(铆焊),也有枯燥乏味的(图书管理);而每周的工作时间从53 至82 小时不等。人们最关心的还是薪水。汉堡是德意志帝国所有城市中人均收入最高的,1913 年比平均水平高72 个百分点。然而,汉堡的总增长相对缓慢,同时外来移民的比例较高,其人均实际收入其实在下降。①不仅如此,其收入分配也与柏林一样差异悬殊,贫富差距毫无缩小的迹象。所得税统计数字显示,1871 年,83%的底层纳税人的收入占可征税收入总额的32%,而顶端的1.5%所占额度为29%。1916 年,前者所占的份额升至35%,而收入占总额29%的那部分人却减少至1%。从绝对数量来看,贫富差距的确扩大了。如果把货币购买力的变化计算在内,那么收入最低的5 类纳税人所占比例从49%升至83%;而顶端纳税人群体则由0.1%降至0.02%—虽然只有44 个人,但其收入都在500 000 马克以上,并以此为基数缴税,这些人包括斯洛曼和贝伦斯之类的公司的所有人,或像巴林一样杰出的公司董事。普通的自主经营的小商店主和手工匠的收入大约在5000 马克左右,其中商界精英的收入则占1%左右。公共部门的收入差距相对不太悬殊:高级公务员(一级)的年收入为9 768 马克,二级公务员或普通白领的收入为这一数字的40%,三级公务员为25%,而一般的州政府办事员则为20%。私营部门普通文员的工资则较低,从721 马克到2 700 马克不等。工人的收入更难统计。1895 年,码头工人的日薪约为2~4.2 马克;但由于季节性失业问题,2/3 以上的码头工人年薪不足500 马克,只有5%的人超过1 500 马克。烘焙、木工或管道工等行当中的熟手收入则好很多,并且是按日或按周计酬。②由于大多数船厂工人都是计件工作制,根据具体任务的性质领取酬金,所以援引他们的薪酬数据并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船厂工人的工资等级体系非常复杂,再加上加班加点是常事,因此很难将这些数字转换为年收入。体力劳动者的平均年收入在战前约有1 800 马克;但一个顶尖的熟练工可以赚到近2 500 马克;而普通新手加上加班奖金也可以拿到2 170马克。③而在收入等级上端,也就是资产阶级内部,一般商店主、职员或小企业主之间的收入差距相对较小。 然而,我们需要对这些统计数据加以扩充和限定。尽管令人避之唯恐不及的通货膨胀时代在1914 年以后才出现,但物价在战前就已经发生波动。在1874~1887 年,生活成本平均每年下降1.5%~1.7%,但在此之后,一直到1913 年,物价每年都上涨0.9%~1.5%,而汉堡物价则高于平均物价,在大萧条之前才有所下降。①对大多数人来说,食品开支占生活费的一大部分。普通人大约一半的工资都花在了高脂肪、低蛋白的饮食上,如黑麦面包、土豆、鱼肉和猪肉,配以加糖咖啡和啤酒。房租是第二项主要开支。对于那些收入在1 200 马克以下的人群,房租大约要占到1/5。这些都扣除后,他们的工资已所剩无几:在诺伊储蓄银行中,工人的储蓄账户仅占7%,他们通常只有一些最基本的财产。如果有存款、有财产就可称为资产阶级,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其说社会差距体现在行业及其收入上,不如说体现在“赚取财富和继承财富”上。但即使在那些有产精英内部也有差距。近60 万人的总存款为3.9 亿马克,人均仅有600 多马克。相比之下,人均财产超过10 000 马克的仅有4 万人;②而这个城市的房地产—价值47.6 亿马克③—把持在20 000人手里,仅占总人口的2%。真正处于顶端的财富精英少之又少:1880 年,汉堡共有72 位百万富翁,其中仅有16 人拥有500 万马克以上的个人财富。战前汉堡最富裕的人为船主亨利· 斯洛曼,其身价据说有6 000 万马克。 住房的分布情况也许是财富和收入差距最直观的体现。随着对贝格道夫和库克斯港等周边地区的开发,汉堡的地理面积扩大了,但人口密度仍在上升,战前的每公里人数接近1 500 人。在汉堡,有相当一部分家庭住在地下公寓,他们或者和其他家庭合租,或者再将房间分租给房客。但汉堡并非到处都拥挤不堪。1892 年年中,旧城区和新城区中心的街边住宿区爆发霍乱,人们不禁感叹“这根本不是欧洲”,到1913 年,这些地区的人口减少了一部分;附近圣格奥尔格和圣保利的贫民区依然破败不堪;新兴的工薪阶层则住在汉堡东边简陋的“出租棚房”里,与哈维斯特胡德和罗森巴姆的别墅区仿佛两个世界,这些别墅位于阿尔斯特湖西部,阿姆辛克家族、巴林家族、布洛姆家族、贝伦贝格– 戈斯勒家族都居住在那里,其居民仅占汉堡总人口的5%,但整个汉堡可征税收入的1/5 和所得税税票的1/3 都来自这两个别墅区。“西区”和“城市中心”两地居民的死亡率更凸显了“隔离”的重要性。由于贫民区的卫生条件恶劣,缺乏抵御疾病的资源,因此穷人死于结核病、伤寒和霍乱的概率比富人高得多。银行家的儿子阿比· 沃伯格体质虚弱,极易感染传染病,但他还是小孩的时候就在伤寒中活了下来,这本身就能说明一些问题。他的弟弟马克斯在1892 年霍乱肆虐时,每天仍然坚持在市中心工作17 个小时,他说自己“有种对霍乱免疫的感觉”。收入在5 万马克以上的人群,其死亡率为4.8‰,而那些收入少于1 000 马克的人死亡率则高达61.9‰,是前者的近13 倍。 这就是处于世纪之交汉堡的资产阶级社会—一个经济迅猛发展,物质分配不公的社会。许多讨论1918~1919 年革命的专著提到它必将会被穷苦的无产阶级所推翻,这都传达了这样的观点,但答案不得而知。资产阶级社会有其自身的道德和文化价值观,这些观念即使无法将不平等的分配状况合理化,至少可以起到缓解作用。 家庭是凝聚社会的基础。大多数人都在20~30 岁成婚(女性往往结婚年龄更早),尽管离婚率已经开始上升(从1890~1894 年的4.7%升至1913 年的10.9%),但离婚人口的比例仍然很小(1910 年时占总人口的0.6%)。同样,虽然出生率也在下降,但得益于健康状况的改善,家庭的规模并未缩小。1910 年,42.5%的德国家庭有5 个以上的家庭成员;10.1%的家庭达到了8 个以上。以莫里茨· 沃伯格和夏洛特· 沃伯格为例,他们的7 个孩子中有6 个都活到了60 岁以上,这并非特例。大约在同一时期,阿尔布雷希特· 奥斯瓦尔德和妻子养育了6 个子女;而他们的上一代约翰内斯和埃米莉· 舒巴克则有12 个孩子,其中只有1 个孩子不幸夭折。在某个层面,家庭就是一个小经济单位,各个成员分工明确,丈夫外出工作,妻子照顾家庭,而孩子则为工作和结婚作准备。①在有产业的资产阶级内部,家庭的角色则更加复杂,它往往是公司的基础。资本的代际转移、家族的社会地位都要求对子女的教育和婚姻问题要慎之又慎。珀西· 施拉姆曾在1900 年回顾他显赫的社会背景:“一个人在家族内部的关系、父亲的公司名号、母亲的家世背景,这些是你一定要清楚的。”施拉姆家族与奥斯瓦尔德家族、鲁珀特家族、默克家族和阿姆辛克家族都有联姻关系,而阿姆辛克家族又与贝伦贝格– 戈斯勒家族、威林克和韦斯特法尔家族有关联。对一个资产阶级家庭来说,有效地划分兄弟之间的责任对于家族的成功至关重要。例如阿姆辛克家族就采取两分法的策略。每一代中都有一个儿子成为律师,其余全部从商。施拉姆家族和奥斯瓦尔德家族也有类似的区分模式,但布洛姆兄弟则全部投身商界。 沃伯格家族向我们展示了家族生活在19 世纪的演变过程。与萨拉和阿比· 沃伯格的子女通婚的全部来自商业世家;但在他们的下一代,莫里茨和夏洛特的7 个子女中只有3 个按家族传统成婚。婚姻作为整个家族的社会经济策略这一传统,受到了以情感为基础的婚姻的挑战。父母对儿子职业选择的控制权也在明显减弱。马克斯经过一番劝说后才放弃当军人的计划,本想投身科学研究的保罗也是如此;但他们的父母还是没能阻止阿比放弃对艺术史研究的热爱,这是他与生俱来的权利,而费利克斯享受生活,热衷慈善,并且执意从事这方面的事业。可以说,联系紧密的资产阶级家庭在19 世纪末已经走上了下坡路。阿比· 沃伯格批判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金融王朝,珀西· 施拉姆年迈的伯祖母把自己的家族混同于博基亚家族,这些都透露出一种自我否定的意味。托马斯· 曼在他1901 年出版的第一部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一个家庭的没落》中对这种情绪的刻画入木三分。布登勃洛克家族虽然主要以托马斯本人在吕贝克的家庭为原型,但它也是汉莎商业王朝的典型,在18 世纪时走向繁荣,但因为种种因素日渐式微,例如婚姻不幸、手足间明争暗斗,以及家族的开创精神衰退等,与朔彭豪尔和瓦格纳的往来更是雪上加霜。该书在汉堡读者甚众,甚至还被马克斯· 施拉姆那藏书颇富的图书馆所收藏,对施拉姆家族来说,这显然是一种不和谐音。珀西· 施拉姆会不自觉地拿自己母亲的家庭与布登勃洛克一家作对比;而沃伯格家族也很难忽视这本书的意义,他们对婚姻危机已经是见怪不怪,更别提还有个献身艺术的儿子差一点就死于伤寒。即使风暴尚未来临,那些大家族也已经意识到了自身的脆弱。

除了家庭关系,宗教也是由来已久的社会纽带。在整个19 世纪,汉堡有90%的人都是正式的路德教信徒,而且处处体现出独特的新教教义。然而,19 世纪初,汉堡的哥特式天主教堂和5 座其他教堂却被拆除了,以新建海堤和排水系统,这象征着宗教仪式的精神性似乎在向世俗工作让步。那些位于社会阶梯上层的人(例如银行家马克斯· 冯· 申克尔),似乎还保有对正统路德教的虔诚。但在世纪之交,圣职人员内部实行“自由化”改革的压力渐增,而改革是为了应对“大多数人”不再定期参加教会聚会的问题。相比之下,汉堡的犹太社区则接受了19 世纪初出现的类似的分化,允许犹太教堂保守派联盟和自由派庙宇联盟在当地教会的支持下分别修行。与信奉路德教的社区相比,犹太社区内部社会的两极化程度较轻,因此也较和谐。19世纪中期对于汉堡的犹太人来说是一段共同繁荣时期,法律逐渐放宽了对他们的限制,他们偏爱的经济活动(以自主经营为最)开始蓬勃发展。1871 年,75%的犹太人都住在旧城区、新城区、圣保利和圣格奥尔格等“市中心”地区;到1914 年,绝大多数人都定居“西区”,以罗森巴姆区为主,也有一部分在哈维斯特胡德。1897 年,27%的犹太人的所得税税率属于前两个等级,而总人口中这一比率仅有11%。但犹太社区在其他方面却走向了衰败。1811年,犹太人占汉堡总人口的4.87%,而到1910 年却降至1.87%,可见犹太人的出生率较低,同时汉堡缺少新的犹太移民。①不仅如此,社区内谨守教义并参加聚会的人开始减少。沃伯格五兄弟的父母和祖父母严格遵守诫命,守安息日,而他们的下一代(除了最小的儿子弗里茨)已经没那么虔诚了,马克斯去犹太教堂只是例行公事,并非出于虔敬;而阿比在大学时就放弃了合乎教规的饮食,之后还娶了异教徒为妻。阿尔伯特· 巴林也是如此。我们事后才知道,异族联姻的增加并不代表犹太人已融入经济精英(而非宗教精英),但在当时,有很多证据都支持这个想法。随着犹太人在形式上的解放,他们不仅成为了商业和专业领域的合作伙伴,而且还在行业协会和公共管理部门担任行政人员,并参加社交生活,结交朋友。然而,当出现群众暴动时,反犹势力就会抬头,而在社会精英内部也暗流涌动。这股潜在的顽固势力提醒我们,犹太人在19 世纪的成就可能会一夜之间不复存在。女儿玛蒂尔德在佛罗伦萨学习时,比格尔迈斯特· 约翰· 格奥尔格· 门克贝格并没有反对她与阿比· 沃伯格及其夫人住在一起,沃伯格家族还与参议员马克斯· 施拉姆保持着友谊;但施拉姆的母亲则把犹太人归入4 类不能接受的丈夫人选中。马克斯· 沃伯格深信汉堡有一种“潜藏的反犹情绪”。 有人认为,资产阶级的共同文化能超越19 世纪社会在职业、物质资料和宗教上的分化,它比任何事物都更有效。这种观点的核心是教育,是正式教育与个人修养的结合。然而,历史学家往往不把汉堡作为受过教育的资产阶级的聚集地;当然,19 世纪的汉堡的确以市井文化和物质主义著称。一位参观者在19 世纪40 年代曾评论道:通常,“在汉堡,艺术和商业的关系就如同罗马法和汉堡当地法律的关系一样:前者只有在汉堡没有相关法律或不与汉堡法律相违背时才适用”—19 世纪时,鹅市歌剧院的管理者也认为,汉堡市民是“我见过的文化层次最低的”。汉堡银行家萨洛蒙的侄子—诗人海涅—在1831 年逃离了这个“铜臭弥漫的窠臼”;勃拉姆斯也被比他资历浅的人取代,未能出任汉堡音乐厅总经理一职,并最终离开了这个地方;汉堡市立美术馆馆长阿尔弗雷德· 利希特瓦克则认为,汉堡对美术艺术缺乏支持,失望至极。上述这些论断或许有些误导性。19 世纪晚期,汉堡正规教育蓬勃发展。随着教会放松了对教育的控制,中等教育几乎被16 世纪的约翰纽姆文法学校垄断的状况终于被打破,到1913 年又新增了两所文法学校、约翰纽姆文理中学(成立于1837 年)、5 所九年制的文理中学和7 所实科中学。“一战”前,德国共有20 所公立中学,拥有630 多名教师,招收了11 200 多名学生。在初等教育方面,汉堡共有200 多所小学,拥有约3 500多名教师和112 000 名学生。此外还有两所公立女中,还有约20 所为天主教徒、犹太教徒和其他少数族群而设的私立中学。除此之外,虽然参议员维尔纳· 冯· 梅勒创办大学的提议在1913 年被否决了,但汉堡在高等教育方面还是迈出了关键的几步,在1895 年恢复了公开课的传统体制,在莫尔韦德修建了第一所大讲堂,并于1908 年建立了“殖民学院”。但无论怎样,当地虽然没有大学,但并不缺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像绝大多数德国大学生一样,汉堡学生可以漫步在德国的各大高校。 另一方面,美学价值要让位于物质价值,这毫无疑问是汉堡资产阶级文化的核心。典型的例子就是大多数汉堡商人更愿意资助职业院校而不是大学,此类职业院校约有37 所,当然,考虑到他们自己有在海外当“学徒”的传统,所以这种偏好倒也合情合理。换句话说,社会地位不取决于正统教育,而要看经济和职业上的独立性。同样,作为资产阶级最根本的价值观,法治的核心并非法学理论,而是经济利益。汉堡参议院曾于1857 年宣布:“债权人……也应当受到法律保护,否则法律作为立邦之本和我们独立自主的基础,会失信于民,甚至会使汉堡这个商业城市不复存在。”一个以履行合约和承兑票据为基础的社会必须维护平等和诚信。这些原则和工作、勤俭、收益等因素结合起来,构成了汉堡资产阶级的基本价值观,而且不只适用于工作领域。在18 世纪晚期和19 世纪新出现的“公共领域”中,民间组织被历史学家视为资产阶级独有的机构,储金会是汉堡为数最多的社团之一。 当然,汉堡商人也在有意识地营造一种与经济活动截然不同的氛围。他们不再以办公室的楼上为家,而是回归家庭生活,陪他们进餐的是毕恭毕敬的妻子、战战兢兢的孩子,旁边还有比德迈风格的家具。这种尊贵高雅与旧城区、新城区和圣保利区等地被监管的妓院和“(贩卖)成人用品的自由市场”截然不同。私人友谊与商业价值也可以区分开来。我们可以像马克斯· 施拉姆一样,在自己那藏书多达5 000 册的私人图书馆中寻找文献,而那些加注的图书编目便是洞悉上流社会的绝佳指南。已有的协会通过举办文化活动来进行社交,这一点尤为常见。18 世纪晚期的协会往往关注的是社会福利问题(尤其是贫困);然而,在19 世纪,以文化和体育等休闲活动为主的组织盛行起来:爱乐协会、五花八门的合唱团、艺术协会、文学社团,还有汉堡赛马俱乐部以及众多体操、射击和赛艇俱乐部。汉堡一些公共领域的机构已经相当普及,完全可以依靠市场经营下去,例如报业机构和8 所剧院。但是汉堡的慈善基金会等组织却要依赖富人资助。1908~1913 年,遗嘱捐赠为世俗慈善组织贡献了1 500 万马克,占所有货币遗产的9%左右。简言之,文化以物质为基础。珀西· 施拉姆的姑婆安娜· 亨克尔患有精神病,只能靠她父亲留下的30 万马克过日子,终日与海涅的诗歌、撞球游戏和俄罗斯香烟为伴。阿比· 沃伯格也埋首故纸堆,研究古典时期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各种细微象征(为他庞大的文化研究图书馆奠定了基础),但提供资助的却是他那些“满身铜臭”的兄弟们。当然,虽然阿比· 沃伯格本人把诞生了沃伯格和利希特瓦克的汉堡称为庸俗之地,但该结论确实太过草率。李斯特、约阿希姆和克拉拉· 舒曼都曾在汉堡演出,理查德· 施特劳斯和汉斯· 冯· 比洛也曾在那里担任过指挥。霍尔斯腾普拉茨的新音乐厅是由船东卡尔· 雷伊茨出资修建的,印象派画作也主要是靠银行世家贝伦斯家族的收藏才敲开了汉堡的大门。总而言之,在汉堡,一切都以金钱价值为基础。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