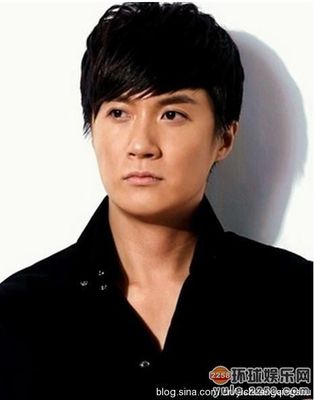每天虽没啥屁事,但必定会出门,且出外出到必至半夜才返家。单单想及这里,已自己觉得好笑。究竟怎么弄成这样一套过日子形态呢?噫,荒唐。 故我每日回抵住的地方,有一种“回家”的扎实感觉。我喜欢这种感觉。我甚至珍惜这样的感受;也就是说,若我回家太早,如晚上八点钟,便不叫“回家”,乃我太有可能不久又被朋友召出去或被自己的玩心再次拉着出发。

然近三五年我常忘了这“回家”的感受。或许我皆在家近处活动,即使走路来、走路去大半天下来也走上了五公里或八公里,却因为心中洞然家其实就在不远之处,正因如此,即使到了一天结束时走回家去,竟然不大像“回家”。 这几个月,我又想起了这件事。想起了回家这个心中兴奋的好感觉。怎么想起的呢? 我每次自南部或中部回到台北,下了火车,便不自禁加快脚步,一点时间也不愿浪费,冲着去搭捷运,为了一件一点也不紧要的事,回家。 但不知为何,它令我百般兴奋。同时,它以一种情态表现出来,便是我才下了捷运,已微微有想大便的感觉。然后自捷运站走往家的路上,更是愈来愈有便意,几乎都像是迫不及待如同要拉肚子似的。 当然,接着的十五分钟或四十分钟,便是极专注又极必定要做的事,开门,脱鞋脱裤坐马桶,冲水,开窗;接着打开背包,拿出在外所用的物事;然后倒一杯水什么的,便这么像是总算已到了家里。 即使是当日往返,自中部返北,亦令我抵家前产生便意。 于是,这想大便的感觉,使我想到了今天这篇《回家》的题目。 有时在台北,晚上接近家门,亦有这种感觉。可见未必要出远门方能达臻此效果。但是长距离与丰富的行程更可获得想大便的可能。 自国外回来,抵桃园机场,一出机门,我亦是快步前行,往往到了缴证的关口,竟是最先的几人之一。桃园机场的海关是全世界验证盖章最快的关口,我从来很少超过三十秒的。接着是领行李。再接着,是乘国光号。这一切流程,于我皆习常之极,我几乎要说桃园机场是回来最舒畅的一处地方。而国光号上偶放的某一两首国语庸俗流行歌曲,竟然如此醉人。抵台北车站,坐出租车,七八分钟后,回到家。行李才放下,第一件事,大便。 长途旅程后的回家,最能获得便意。 即使在台北,若是一天在外的时间颇长,办了好些事,经过了这城市好多不同区块,遇了好几撮人,最好还完成些文思的事,如看了好几页书或是写完一篇小稿,在那么多丰盈事体之后,心情满有些高昂下回往家门,常常会有便意。 故而我发现,人应该一天多做些令自己丰足并遂心之事,然后在一天收束时享受回家的美乐感受。大便或不大便,只是一项表征而已。 我们没有快快乐乐地回家,代表我们没有好好地出了这一趟门。我们很快就回家,也或许是我们这个城市不值得让人待得久,或我们的朋友都不见了吗?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