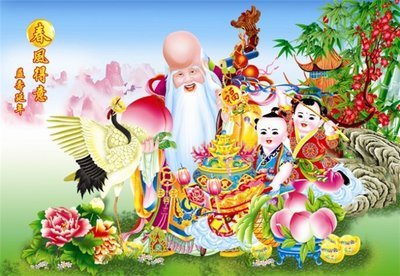一位曾在卢旺达当了好几年外交官的大学同窗曾对我感慨,她对卢旺达有一种特殊的情感:那里有黑非洲最优美的法语口音和最勤勉的劳动者,那个国家的幅员是如此的狭小,人口却又是如此的稠密,在矿藏丰富的非洲大地,它是为数不多的贫矿国家,而即便整个非洲在战后一直多灾多难,动荡不安,但恐怕没有第二个国家曾举国陷入过如1994年大屠杀那样的灭顶之灾。 18年过去了,今年2月7日,卢旺达总统卡加梅称,该国在脱贫方面取得长足进步,2006年贫困率高达57%,2011年则降至45%,有百万人脱贫。教育普及程度进步幅度更大,2006-2011年,卢旺达小学男生入学率从59%提高到79%,小学女生入学率从58%提升至82%,而中学入学率同比则翻了一番。在一份官方声明中,卢旺达财政部长自豪地宣称,即使是对祖国前途充满憧憬的卢旺达人,也很少有人能预测到“国家从普遍赤贫状态中脱贫致富的速度”。农业及动物资源部长则称,卢旺达2011年粮食产量“倍增”,预计节余30万吨玉米、20万吨豆类,这在饥馑遍地的黑非洲简直是个异数。 卢旺达的经济增长一直被IMF和世界银行所称道。据IMF的数据,自2003年起,该国GDP增速一直稳定在6%以上,近两年则出现了“井喷”现象:2010年GDP增速为7.5%,2011年可能达到8.8%。 自大屠杀发生后,卢旺达曾被认为是非洲最危险的投资环境之一,如今这一状况也得到显著改变。2010年8月,世界银行向卢旺达政府颁发奖杯,表彰该国在全球商业环境评估中的明显进步(排名从150名升至67名)。新加坡《联合早报》甚至预言,卢旺达首都基加利将成为“非洲的新加坡”。令人惊讶的是,今天的卢旺达号称“非洲女性天堂”,2008年立法选举中,女性议员比率高达56%,高居全球第一,许多卢旺达女政治家在政府中担任部长要职。 “非洲楷模”的崛起,首先和国家的政治转型有关。1994年,卡加梅(图西族)带领“爱国阵线”击败胡图族武装,结束了部族大屠杀(约80万图西族和胡图族温和派遭胡图族极端分子杀害)。此后,由爱国阵线组成的新政府致力于民族和解和战后重建工作,实现了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目标。2000年4月,卡加梅被推举为总统,2003年8月又以压倒性优势在卢旺达首次多党总统大选中获胜(任期七年),成为首位民选总统。2010年他又成功连任。 卡加梅陆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摆脱过去对法国的依附,包括定英语为官方语言,加入英联邦(卢旺达和英国在殖民时代无任何隶属渊源),重新推动经济多元化,拒绝加入法国倡导的“大湖区稳定计划”等,甚至一度和法国断交。通过这些努力,卢旺达基本摆脱了依附于法国的单一型经济,这种新的、多元化发展的经济虽然缺乏突出财源,却更加平稳,不易受国际市场波动的影响—而后者正是大部分非洲国家经济大起大落的症结所在。

卢旺达政府的这些努力尽管引来法国的不快,却受到国际社会普遍支持:美国宣布“非洲普惠制”适用于卢旺达;英联邦在2009年接纳卢旺达为正式会员国;南部非洲最大经济体南非和卢旺达的经贸关系稳步发展。不仅如此,近年来,卢旺达还积极与在非洲最活跃的两大新兴经济体—中国和印度发展经贸关系,一系列重要的基础建设项目正在这些“外力”帮助下稳步推开,而基础设施欠账太多,正是非洲各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最大制约所在。 卢旺达政府在发展方面有较长远的规划和较清醒的头脑,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更有潜力的方向上。2010年卢旺达还公布了《10年远景规划》,计划将服务业、软件外包业、教育产业和旅游产业等当作2020年前重点发展的经济突破方向,这些显然较一些单纯“靠天吃饭”或一味依赖“卖资源”发展的邻国高出一筹。 然而,隐忧依然存在。卢旺达人口仅900万,人口密度却高达每平方公里343.15人(世界第18位,非洲第1位),人均GDP不到300美元,仅凭农牧业,其发展已触及“瓶颈”,尽管《10年远景规划》雄心勃勃,但正如一些头脑清醒的观察家所指出的,卢旺达地处内陆,向东、向西都缺乏畅通的交通干线,能否一鸣惊人实在难以预估。 卢旺达最引为自豪的政治、社会稳定也并非没有问题。1994年的大屠杀,根源在于胡图族对图西族的歧视,而这种歧视又源于殖民时代图西族凌驾于胡图族之上的特权地位。如今图西族人再度“上位”,为避免民族裂痕拉大,卡加梅政府制订严格禁令,严禁谈论民族矛盾,围绕当年大屠杀的讨论也被设立重重禁区。然而这种强压的“民族和谐”却只能掩盖、不能从根本上弥合昔日的创伤。 卡加梅本身也是个争议性人物,在欧洲,一些人权组织、甚至一些国家政府指责他专权、压制民主。在2010年8月的所谓“多党制选举”中,卡加梅的执政党卢旺达爱国阵线(FPR)得票率高达93%,反对派指责称“谁都知道这么高的支持率是怎么来的”,而基加利政府对媒体、记者和持不同政见者的打压也引发普遍谴责。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