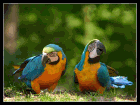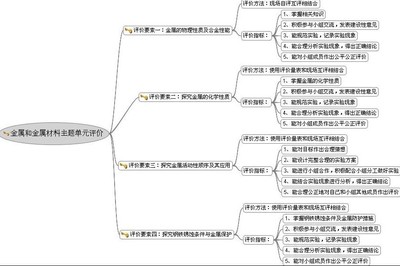鲁迅的《拿来主义》(1934),记得有行家译为“grabbism”。相对于“拿来”是“送去”。听鲁迅说来,自“海禁”给洋人的枪炮打开后,“送去主义”竟成时尚。古董古物等“学艺上”的东西,一批一批地送去巴黎伦敦等名都大邑去展览。送出去的除了物外,还有人呢。梅兰芳博士就是这样先“送”到苏联去催进“象征主义”,然后顺便到欧洲传道。
《拿来主义》尽见鲁迅杂文本色。听他口气,可以看出他对新兴的“发扬国光”的路数很不以为然。“我在这里也并不想对于‘送去’再说什么,否则太不‘摩登’了,”他说。但他觉得,我们不能光“送”不“拿”,要不然我们的子孙日后就变得家无恒产。东西得由我们自己“拿”,不能任由别人“送”给我们。为什么?因为我们要的,不是鸦片、人家早已作废的军火枪炮、法国人的脂粉和日本的印着“完全国货”的各种小玩意。“所以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
所谓“拿来”,就是自己动手精挑细选。“拿来主义”对国家的发展关系至大,鲁迅说因为“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
清末外交官郭嵩焘(1818-1891)1875年出使英国,主张向西方学习,支持洋务派的自强新政。他在《使西纪程》有此一说:西方在“格致”与“政事”的领域上高于中国,但“文章礼乐不逮中华远甚”。这种见识,正可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互相呼应。但从往后的历史发展看来,天朝要向番邦“拿来”的不单是枪炮水电弹药这些“奇技淫巧”,还有文章做法也得向西方取经。
要向西方取经,只能通过翻译。梁启超的话,说得斩钉截铁:“处今日之天下,则必以译西书为强国第一义……及今不速译书,则所谓变法者尽成空话,而国家将不能取一法之效。”

任公在其鸿文《译印政治小说序》鼓励国人发挥“拿来主义”功能,“采外国名儒所撰述,而有关中国时局者,次第译之”。任公突出了政治小说的地位,希望借此“改良群治”、“开导民智”,可幸后来域外作品翻译的种类五花八门,远远超乎他个人的指望。《译印政治小说序》发表于1898年。一年后林纾的《茶花女》上场,严复看了也不觉心动,赞曰:“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魂。”
《茶花女》是个多情妓女为了顾全爱郎前途不惜牺牲自己的故事。光以内容看,实难跟“富国强兵”拉上什么关系。但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看,林纾在翻译西方小说上所做的“拿来”工作,贡献至大。这位洋文半字不通的古文大家得友人之助译出了小仲马一个“哀情”故事,使他变成为胡适眼中的“介绍西洋近世文学的第一人。”《茶花女》因是“域外”作品,其叙事与言情模式自然有别于国人习知的才子佳人大团圆老套。继林纾后近百年的域外翻译工作,成了我们新文学的建设基础。鲁迅的话没错,“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
要是鲁迅时代的信息已“全球化”,知识产权受到国际法的保护,“拿来主义”恐怕不是grabbism这个意思了。版权不错是可以用钱买回来,但交易除了“银货两讫”外还有好些细则要遵守。就拿林译《茶花女》做例子好了。据陈平原在《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所说,林纾在《茶花女》删节颇多,主要集中在前四节,其中包括另一妓女的故事和叙事者对有关妓女的议论等枝节。这些在译者看来都是无关重要的闲笔,删去一点也不可惜。
西方国家为了保护作者的知识产权成立了《版权法》。要引用或翻译一本立了“案”的出版物,得跟作者和他的出版商或经理人洽商。原著内若需要任何改动得先征得“事主”同意。1976年美国修订了版权法,把作者权益受保的年份延至死后五十年。好让其子孙续享余荫。
拿今天的眼光来看,早年的域外小说翻译,没有几本够得上翻译标准的。林纾恣意删节《茶花女》叙事的“议论”,可说开了清末民初译者凭一己所“好”夺原作者之“志”的先河。后来“意译”或“改写”风气之形成,说不定与冷红生的先例有关。根据谢天振和查明建写的《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苏曼殊、陈独秀翻译雨果的《悲惨世界》,形式上采取传统小说的章回体。从第八回起,整整有六回的篇幅是译者凭空添加的情节,编造了一个与原著完全不相干的情节。小说人物之口,多数责备‘奴隶的支那人’的丑恶习俗,并以反对拿破仑称帝独裁为结尾,借此来宣传自己反满的民族革命的思想。”雨果的旷世名著《Les Misérables》就这样给我们“拿过来”炮制成为反清的“革命”小说。
事有凑巧,对我们思想影响至巨的严复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也是跟《茶花女》同年出版的。科学的著作,译者无由任自己的意气随意增删或改写的。幸亏我们从严复的译作学会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败”的道理。这道理给维新派诸子做了“新民”运动的基础,不然说不定我们今天还得在三呼万岁的日子过活。
更值得庆幸的是,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活跃的时期,英国的《版权法》还未成立,否则我们哪能得知“天演”这个概念的由来?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