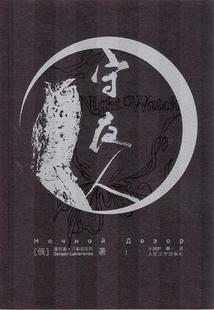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辛波丝卡去世,作品激发电影《红》,“二战”和极权主义牺牲品的守灵人
波兰诗人、199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维斯瓦娃·辛波丝卡,于2月1日在位于波兰克拉科夫的家中去世,享年88岁。这位害羞、说话轻声轻气、烟不离手的女诗人,去世前罹患肺癌已久。据她的私人秘书对媒体称,诗人“十分安详,在睡梦中离开了我们”。
诺贝尔奖委员会将辛波丝卡誉为“诗坛莫扎特”。她在诗歌中“对人性持微妙的讽刺和怀疑”,用一种令人出乎意料的方式运用幽默,被认为既具有深刻的政治性,同时又玩世不恭。看似简单的字里行间,却微妙、深刻,具备令人难以忘怀的美感。她擅长用简单的物体和细致入微的观察来反映宏大主题,常常是一些日常影像—比如一个洋葱、一只空房子里的猫、一把博物馆的古扇,折射出爱、死亡以及逝去的时光种种。 写诗60年,发表不到400首;出版过16本诗集。著名诗作有《一见钟情》、《回家》、《在一颗小星星底下》、《写履历表》、《对色情文学的看法》、《结束与开始》等,其中《一见钟情》激发波兰导演基耶斯洛夫斯基拍电影《红》。台湾漫画家几米也深受辛波丝卡诗歌影响,其成名作《向左走,向右走》的灵感同样来源于《一见钟情》。 “诺贝尔悲剧” 人们开始哀痛辛波丝卡的去世。 去年,波兰总统科摩罗夫斯基授予辛波丝卡波兰国家最高荣誉白鹰勋章,以表彰她对波兰文化的杰出贡献。对于辛波丝卡的去世,科摩罗夫斯基写道:“几十年来,她用乐观、对美和文字力量的信仰,鼓舞着波兰人。”他说,辛波丝卡是波兰精神的守护者。 波兰文化部长博格丹·兹德罗耶夫斯基在一份声明中说辛波丝卡是一个正直、忠诚、憎恶任何形式名誉的人。“她理解他人,理解弱者,对他人怀有极大的宽容。”声明中说,“另一方面,她只期望自己谦虚地活着。”而波兰外交部长西科尔斯基则在Twitter上说,辛波丝卡的去世“对波兰文化界而言是一个无法弥补的损失”。 诗人生前的经纪人成为媒体采访的热门人选,并借机为辛波丝卡新书的出版以及旧作的再版作了提前“热身”。“身体状况允许的情况下,辛波丝卡一直没有间断新诗创作。她没来得及将新作编成一本诗集出版,虽然她一直都有此意。不过这本诗集一定会在今年出版……”而她诗歌的翻译者,如中国台湾的诗人陈黎,在婉言拒绝了时代周报记者就辛波丝卡去世一事采访的同时,在邮件里竟出现了“诗集再版真是好消息”的感慨。 媒体开始大幅报道诗人去世的消息。而在赞美辛波丝卡诗歌的同时,没有一家媒体忘记强调她多年吸烟,患有肺癌,这尤其在《纽约客》个人化的报道风格中被发挥得淋漓尽致,并自然让读者联想到自身的健康:“就在前天早晨,我太太偶然翻出了辛波丝卡最近的诗集《在这里》,看着封面上80多岁的波兰诗人的照片,她的眼睛微微眯着,手里拿着香烟。‘你知道吗?我挺担心辛波丝卡。我希望她别再抽烟了。’” 为逝者哀痛的声音里,尽是生者的喧哗。这也不是辛波丝卡生命里第一次喧哗。早在1996年,有关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否实至名归”的争论打破了这位长期过着几乎“隐居”般生活的老太太的平静,她甚至罕见地接受了《纽约时报》和《洛杉矶时报》的长篇采访。后来为了躲避记者,辛波丝卡搬到了一个记者找不到、甚至连电话都没有的偏僻地方居住。 “她那时好像有些被吓坏了。”辛波丝卡诗歌的英文版译者、美国西北大学文学教授克莱尔·卡瓦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她为数不多的朋友将那次事件称为‘诺贝尔悲剧’,她自此停笔了好几年,才写出一首新诗。” “不管怎样你都在谈及政治” 有别于上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波兰诗人切斯拉夫·米沃什,辛波丝卡并非一位共产主义时代英勇大胆的异见分子。也不像与她同一年被提名并成为热门候选人的波兰诗人兹比格涅夫·赫伯特,辛波丝卡诗句中最让人欣赏的是其“精确的用语”,而非政治隐喻。 但这并不意味着辛波丝卡在长达60年的诗歌生涯里从未涉及政治。事实上,政治在她的职业生涯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她曾一度以“社会现实主义”的风格写作,并信仰共产主义。她曾热烈歌颂共产主义—她后来声称那是“黑暗时期”而拒绝承认—但在其诗歌生涯的后半段,她站在反对共产主义的阵营里,用自由主义的思维方式洗刷过往。这无论是在1996年获奖,还是现如今去世,都成为人们热烈谈论的话题。不过,鲜有人提及辛波丝卡早期的“社会现实主义”写作风格,是遭遇批判后,重新调整态度迎合官方的结果。 事实上,作为一个“二战”幸存的脆弱女性,辛波丝卡早期诗作表达的是自己对民族的负疚感,以及对满目疮痍的祖国的忧患。这些色彩阴郁的诗歌单独发表时并没有引起评论界的注意,但就在1949年,当她想结集出版她的处女作时,编辑们发现她的诗作全然没有歌颂社会主义建设的作品,而其低沉的情调更令人委靡不振,因此遭到了官方批评界的严厉批评。像苏联和东欧各国对言论文字实行大批判式的全民检查一样,据说当年在波兰连中学生都卷入了批判辛波丝卡的行列。 辛波丝卡自我调整后开始发表一些政治正确的诗歌,主要收录于《我们活着的理由》(1952)和《问我自己》(1954)两本诗集中。诗的主题主要是反对波兰的西化倾向,为和平而斗争,积极投入社会主义建设中。在这些诗歌中,她以脸谱化的模式写叙事诗,“叙好人完全是好人,叙坏人完全是坏人”。 “现在的人很难理解当时的情境,这一点我难以解释清楚。我怀着拯救人类的热情,却选了一种最坏的方式。但我那么做的确是出于对人类的爱。我后来逐渐明白,我们应该做的不是热爱人类,而是热爱一个个具体的人。我们可以尝试理解他人,却无法拯救他们。”辛波丝卡在一次接受《洛杉矶时报》采访时吐露心声。 这或许是她后来坚称“我的诗歌跟政治没有半点关系,它们写的是人和生活”的原因,她的诗歌《时代的孩子》更是控诉了政治对日常生活的渗透。 “那对我来说真是一个深刻的教训。我年轻时候犯下了一个错。尽管是出于善的信仰,很不幸,许多诗人都和我一样犯了同样的错误。后来他们因改变意识形态而身陷囹圄。我很幸运能够幸免于难,这或许是因为我本质上并非一个真正的政治活动家。” “一见钟情” 一位瑞典评论家说,在瑞典打黑工的波兰清洁工和采草莓的移民,对于辛波丝卡的诗歌耳熟能详,她的诗歌《无法重来》(NothingTwice)还被波兰摇滚歌手Kora改编成了流行歌。这首歌是1994年波兰的大热金曲,当年仿佛全波兰都在唱:“没有什么事会发生两次/结局往往遗憾的是:/我们来到这里时毫无准备/离去了就没有机会再试……” 但辛波丝卡诗歌的流行度显然不广。199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对辛波丝卡是否“实至名归”的质疑之一,便是她在全世界几乎默默无闻—这成了大众媒体对每一个获奖诗人的指控。即便如今,美国民众对第一个报道辛波丝卡去世新闻的《纽约时报》表示费解的大有人在:那个女人到底是谁? 但或许全世界都知道那首《一见钟情》: 他们两人都相信 是一股突发的热情让他俩交会。 这样的笃定是美丽的, 但变化无常更是美丽。 既然从未见过面,所以他们确定 彼此并无任何瓜葛。 但是听听自街道、楼梯、走廊传出的话语—— 他俩或许擦肩而过一百万次了吧? 我想问他们 是否记不得了—— 在旋转门 面对面那一刻? 或者在人群中喃喃说出的“对不起”? 或者在听筒截获的唐突的“打错了”? …… 1994年,波兰导演基耶斯洛夫斯基《蓝白红》三部曲的第三部《红》问世,其拍摄灵感便来自于《一见钟情》。巧合、错失的机会、令人无法忍受的视觉线索以及奇怪到令人困扰的似曾相识:所有的一切逐渐营造出命运感,在结尾处的海难场面,三部影片的主角均再度出场,并且又是以偶发事件串联在一起,令人嗟叹人生的无常。 中国读者认识辛波丝卡,则是在电影《向左走,向右走》里,梁咏琪念着的感人诗句。这部改编自台湾绘本作家几米作品的电影,几乎照搬了辛波丝卡诗歌中的全部细节。当然,几米绘本在大陆的流行,也让更多人开始关注辛波丝卡的其他作品—他的《向左走,向右走》、《地下铁》、《履历表》三本书灵感均来自女诗人的诗。 几米在接受台湾《联合报》采访时表示,自己“年轻时读过《辛波丝卡诗选》,看完就忘了”。等到画完了《向左走,向右走》后重读辛波丝卡,才发现“原来辛波丝卡一直在心里”。 相比较电影、漫画对辛波丝卡传播的贡献,诗集的翻译出版在中国已久远—仅有社科院老翻译家林洪亮翻译出版过《呼唤雪人》和《一见钟情》两本,而有关辛波丝卡诗歌的研究,仅有旅居瑞典的作家傅正明在1998年出版的《在波兰的废墟上:辛波丝卡的诗歌艺术和文化传统》。 不过随着女诗人的逝去,或许新一轮的诗歌即将到来。 本文引用辛波丝卡诗歌均来自:《辛波丝卡诗选》,陈黎、张芬龄译,桂冠出版社,1998年。 我们都是时代的孩子, 这是个政治化的时代。 整日、彻夜, 一切事—你们的、我们的、他们的— 都是政治化的事件。 无论你乐意与否, 你的基因已有了政治背景, 你的皮肤,政治铸件, 你的眼睛,政治视角。 你的任何语言都产生反响, 你的任何沉默都显示含义, 不管怎样你都在谈及政治。 …… ——《时代的孩子》 诗人在旋律里燃尽,而余音不绝 维斯瓦娃·辛波丝卡 1923-2012 出身于波兰小镇布宁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31年全家迁往克拉科夫。1945年开始到波兰最古老的雅盖沃大学哲学系就读。1945年发表第一首诗作《我追寻文字》,1952年出版第一本诗集《存活的理由》。1976年之前出版了180首诗,199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2001年成为美国文学艺术学院名誉会员。2012年2月1日,在克拉科夫逝世,享年88岁。 本报记者 赵妍 发自上海 辛波丝卡诗歌研究者傅正明的《在波兰的废墟上:辛波丝卡的诗歌艺术和文化传统》是现今在中国大陆能找到的唯一研究辛波丝卡诗歌的专著。随着辛波丝卡去世的消息传出,该书也成为人们讨论的话题之一。 “她的伟大,在于她像特朗斯特罗姆(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瑞典诗人)一样,堪称‘二战’和极权主义牺牲品的诗的守灵人。”时代周报记者辗转联系到身在斯德哥尔摩的傅正明,这位刚刚在台湾出版了《百年桂冠—诺贝尔文学奖世纪评说》的作家如是评价。 时代周报:你第一次读到辛波丝卡的诗歌是什么时候? 傅正明:我第一次读到辛波丝卡,是在1996年瑞典文学院宣布颁奖给她以后。当时,我明显地感到她的诗歌中有东方智慧,瑞典评论家也有类似的评论。瑞典女诗人普勒耶尔在《为辛波丝卡题照》一诗中说:辛波丝卡“嘴角像佛陀一样:/一种专注庄重的微笑。//尽管谨守中庸仍然充满魅力。”我向来对比较文学感兴趣,从那时起开始研究辛波丝卡。那时,我认识一个喜爱辛波丝卡诗歌的波兰移民,遇到难题可以向她请教。于是就大胆开始译介和评论辛波丝卡的诗歌。 时代周报:你在书中有一章写辛波丝卡的写作风格“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到犬儒主义”,并在开头就说明了“对于曾经有过颇为类似创作经验的中国作家,是富于启发意义的”。能否具体谈谈这种意义? 傅正明:首先应当明白的是,“犬儒主义”一词,词义复杂,原义有归真返璞的一面,后来词义发生变化。我采用这个概念,指的是对正统意识形态的“犬儒主义的嬉笑怒骂式的艺术风格”。 借用西方评论家评论米沃什的观点来看辛波丝卡,我发现米沃什与辛波丝卡有类似的一面。例如,米沃什在《欧洲的孩子》中劝人“不要爱祖国:祖国将很快消亡。/不要爱城市:城市将成为瓦砾。”这里面其实包含深刻沉痛的反讽,饱含诗人对波兰真挚的爱。勒维尼指出:这首诗中的犬儒主义,“宛如在一盏聚光灯的强光之下,展示了诗人被撕裂的灵魂”。这与中国作家的“苦恋”的体验颇为类似。 这种犬儒主义,在中国作家中也可以看到,但并没有得到健康发展。今天我们在中国看到的,是大行其道的嘲笑英雄的犬儒主义。在论述辛波丝卡的“诗的悲剧”时,我分析了她这类诗的一枚硬币的两面:中庸之道与英雄崇拜。辛波丝卡对英雄始终怀有敬意。她的犬儒主义和悲剧精神,对于当今中国作家仍然富于启迪意义。 时代周报:你在文中多次提到中国诗人北岛,并将他与辛波丝卡相提并论。有人认为你这是过分吹捧北岛。 傅正明:我喜欢北岛早期的一些诗歌,尽管他的佳作很少,后来的诗歌每况愈下,令人失望。我不认识北岛,从来没有个人接触,那时并没有刻意要吹捧他的意思。 时代周报:1996年辛波丝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评论界也是褒贬不一,这几乎是每年诺奖的常态,你个人如何评价她的诗歌? 傅正明:现在看来,辛波丝卡不愧为一位杰出的伟大诗人。“杰出”和“伟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T.S.艾略特是个杰出诗人,但不是伟大诗人,他甚至有隐蔽的法西斯倾向。金斯堡是个伟大诗人,但算不上杰出诗人。辛波丝卡的杰出,主要在于她的反讽(irony)艺术,我在《在波兰的废墟上》有专章论述。她的伟大,在于她像特朗斯特罗姆一样,堪称二战和极权主义牺牲品的诗的守灵人。 时代周报:据说在波兰国内,普通的民众对辛波丝卡的诗歌也是耳熟能详。而在中国,普通民众对“辛波丝卡”的名字可能并不熟悉,但对她的诗歌或多或少都是有了解,因为台湾的漫画家几米深受辛波丝卡诗歌的影响,成名作《向左走,向右走》也是因《一见钟情》的启发。你认为辛波丝卡诗歌的流行性,是否与她诗歌中的某些元素相关? 傅正明:一位瑞典评论家这样评论特兰斯特罗姆:“以日常语言写日常体验却能创造出伟大的诗。”这也是辛波丝卡的特征。诗歌要能流行,这一点很重要,尤其是在后现代的西方。辛波丝卡和特兰斯特罗姆的许多诗歌都是朗朗上口的。 同时,还需要把握好“诗的破格”(poeticlicense)的分寸。没有这种适当的打破常规语法的诗的语法,就容易散文化,滥用就会导致晦涩。中国当代诗人,总是想为出新而出新,想在西方诗歌中猎奇,把“诗的破格”糟蹋了。这样的诗,是对汉语的一种伤害,绝不可能流行。 时代周报:诗歌经过翻译之后,在多大程度上仍然是原来的它?或者说,诗歌翻译在多大程度上是可信的?在《在波兰的废墟上》一书里,你评价了英译版,你对辛波丝卡诗歌的中译版是否了解? 傅正明:我的诗歌翻译观点,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两头鹦鹉,一心创造。这种观点,体现在我将于今年4月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译著《英美抒情诗新译》及其导论中。我认为,译诗既要摹仿他民族原作的语言、句法结构、修辞手法等各种因素,又要摹仿本民族传统诗歌的美质和诗语,同时要有译者创造性的传神之笔。译诗能在多大程度保留原作的成分,很难量化。同时,不能说,保留原作的成分愈多,与原诗愈“形似”,译诗就愈好。理想的译诗,应当与原诗形神俱似。 我当时尽可能收集辛波丝卡诗作的别的中译,例如陈黎、张芬龄的部分译文。我觉得他们的译笔是流畅的。但我手头没有他们译的《辛波丝卡诗选》全本。我必须承认,我不懂波兰文,隔一种语言来转译并研究一个作家,评论转译,都是一件很难的事。 时代周报:纽约书评早年发过有关辛波丝卡和201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的比较文章,认为两者有相同之处。你刚刚也多次提到了特朗斯特罗姆,你认为两者的相同之处在哪些地方? 傅正明:我认为辛波丝卡与特朗斯特罗姆在精神上比较接近。两人都避免激进和极端,诗中都有智慧和理性的声音,都有不动声色的冷静的一面。但这种冷静不等于冷漠,可以说是富于人文关怀的外冷内热。不同之处在于,辛波丝卡的诗歌少一些神秘主义因素,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有些神秘体验。 死亡是辛波丝卡和特朗斯特罗姆的一个共同的诗歌主题。这是一个黑色主题,但是,在他们笔下,死亡并不那么可怕,也许两人都有禅宗的圆融,参透了生死。特朗斯特罗姆在一个博物馆的西藏和日本面具中发现了“一种不叫痛苦的痛苦”。他和辛波丝卡一样,发现了一种不叫死亡的死亡—这就是佛家所说的“往生”。辛波丝卡的助理告诉我们:辛波丝卡是在家里于睡梦中安详离世的。作为诗人,她在旋律里燃尽了,但是,她留下的优美的诗歌旋律,将在我们这里余音不绝。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