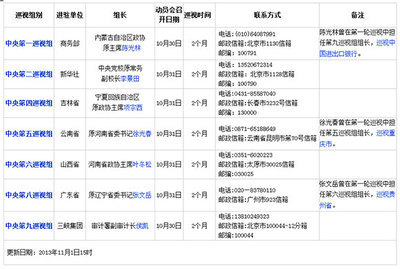在中国极为重要的“十八大”即将召开之际,一场几十年来最大的风暴,正在降临到改革开放头上——那就是欧元区濒临解体。 正如《金融时报》社评所说,由于欧元制度本身的缺陷,以及成员国政府未能兑现其动听的承诺,曾被视为不堪设想,因而被人不屑一顾的欧元区解体这个构想,现已作为一种可能性被各方公开地谈论。如果现在不能遏制欧洲债务危机,救助代价就可能开始扶摇直上,超出掌控范围。 对欧元区来说,最好的结果无疑是各国达成共识,拯救欧元;差一点的结果将是稳定的分离,回到统一货币之前的共同体概念。但同样不能不谈的是,欧洲一些比较边缘化的国家,包括西班牙和意大利,都有可能在这场危机中跟欧元一起破产,从而造成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发生在西方的最大危机。 哪怕仅仅从经济的角度来说,中国也难以对这样的事情保持冷静。中国政府拥有据说价值达11万亿元人民币的国有企业,因此中国的各级官员对“赚钱”这一概念的敏感度高于外国同行。意大利的官员也许认为国家面临破产风险,或者干脆直接破产了都没有什么,但中国人理解的破产却似乎是失去一切财富和荣誉。 如果意大利脱离欧元区,靠大量印钱来偿还国债,那么不仅仅是官员,整个中国都会把意大利当成上世纪90年代初的俄罗斯,把欧盟解体和苏联解体当成一回事。绝大多数并不太熟悉世界经济的官员将把这样的国家视为Loser(失败者)国家,对于往这个方向走感到恐惧。据我所知,这种看法在官员中绝非一种预言,而是早已流传开来的想法。如果欧元区解体得足够快,那么,中国在“十八大”之前就会把这一事件的检讨变为全党共识,而这对改革开放无疑是没有任何好处的。 急之国?稳之国? 政治上的改革也一样。从2003年我来中国一直到2010年,政治体制改革在中国都是一个热门的词汇,官方媒体不断宣扬“积极稳妥”推进政改。而在一年后的今天,大家已经看到“稳妥”开始排在了“积极”的前面。 中国官员在政治领域跟经济领域一样,基本以实用主义为出发点。中国既然会在苏联解体之后迅速抛弃计划经济模式,那么,在欧洲出了问题之后,中国也完全可能会对西方模式进行反思和批判,最终得出类似这样的结论:“欧元区解体的原因就是欧盟缺乏统一的领导”,“意大利的悲剧根源在于对德国资本过于开放”。 这样的虚拟结论或许有些可笑,但从官员整体的利益上看,即使对欧元区进行更有深度的思考,恐怕结论也不会有什么不一样。政府支持改革的根本动机和他们做任何事的动机一样,来自于确保他们主导的体制稳定。而确保政治稳定就需要保持经济的发展速度,需要外部的市场、投资和技术。

过去中国因融入世界而获得的奖品是WTO,而现在的情况是,世界好像并不像过去想象的那样能容纳这么多工业国,中美欧之间的矛盾正在变得越来越突出,WTO所代表的全球竞争被更加传统的地区竞争所取代。欧盟正在夺回自己对地中海和非洲的影响力,美国和亚太国家谈论的合作框架是TPP(环太平洋经济战略合作协议),中国人对此毫不热心——不是因为它威胁中国的利益,而恰恰是因为一旦中国加入的话就会威胁美国的利益。无论怎么改革,中国再也不会得到奖品了。在此背景下,采取一些赤裸裸的保守措施反而有利于中国得到西方的认可。 假如欧元区的分裂使中国在2012年告别改革,那么,从长期来看,改革会彻底地“被稳妥”吗?告别了改革的中国还能稳定吗?这个问题,恐怕无人能回答。因为谁也说不清改革到底是怎么回事,开放到底意味着什么。 邓小平先生作为总设计师所制定并推行的改革开放其实并不是一种设计,它只规定了一个方向性的目标而已——在21世纪中期成为中等发达国家,却没有规划好该怎么做到。人们甚至说不清改革开放目前的成功,究竟是因为其本身的正确性,还是因为中国确实拥有让人嫉妒的好运气。而运气,则是无法预测、评估的。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