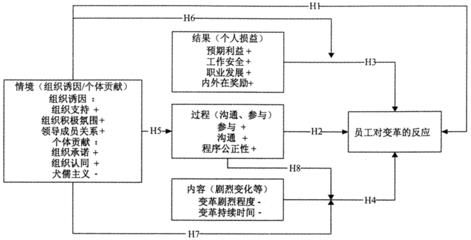国际货币体系核心霸权滥发货币的“货币洪灾”终于无可避免地冲进了中国经济的堤坝之内,10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涨幅高达4.4%,为25个月来最高纪录,涨幅比9月份扩大0.8个百分点,3%的通货膨胀红线失守。由于美国启动第二轮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相信未来我们这个全世界外贸依存度最高的大国必然会面临更大的输入性通货膨胀压力,人行高密度的提高准备金率举动、国务院宣布反通胀系列政策标志着中国宏观经济管理重心正在从“保增长”转向“抑通胀”。而要成功抑制通胀,我们需要做些什么?
毫无疑问,在这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反通胀是一项需要在国内外同时措手的系统工程;在国际上,我们需要尽力遏制国际货币体系霸权国家滥发货币的道德风险,以便从源头上削减、消除输入性通货膨胀压力,相信从刚刚结束的二十国集团汉城峰会、亚太经合组织横滨峰会到日后其它所有可能的国际场合,我方都会尽力狙击美国转嫁经济调整压力的行为。但我们也需要明白,美国是一个开宗明义公开宣布其国内法高于国际法的国家,又占据着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核心国家地位,任何经济政策,只要不是与别国达成了“恐怖平衡”以至于有可能两败俱伤,无论会对其它国家造成多么巨大的冲击,只要美国统治集团感到国内政治和国际竞争中有此需要,他们就有强烈的内在冲动将其付诸实施,其它国家目前尚缺乏有效手段制衡其道德风险,在很多情况下不得不被动跟随。因此,我们这一轮反通胀斗争的重点还是在于国内,只有在我们成功经受住了一次又一次外部经济冲击仍能脱颖而出之后,霸权国家转嫁危机的道德风险才能受到有效抑制。
那么,反通胀国内政策的关键又是什么?利率、准备率、资本管制、市场调控等各个方面可供选择的反通胀工具是人类社会千百年来积累的公共知识,问题是总有这样那样的局部利益羁绊使得决策者难以作出最优决策,或者决而不行,成功的经济调控必定是超越局部利益的成果。
闻鼙鼓而思良将;正值通货膨胀压力汹涌而来之际,让我们回顾新中国经济的卓越奠基者陈云。新中国诞生于民国末年天文数字通货膨胀的废墟之上,是陈云指挥反通胀的成功奠定了新中国经济成长的基础。从1949年5月、8月、11月到1950年2月,历经四个回合较量,新生的人民政权打垮了民国时期壮大起来的投机资本进攻,掌握了市场主导权,遏制了物价猛涨势头,为恢复经济及最终消除通货膨胀创造了条件,原来信奉“工不如商,商不如囤”的私营工商业开始洗心革面,倾注心力于实际生产经营而不是投机套利。通观陈云反通胀斗争的全程,其成功的关键正在于超越了局部利益的羁绊。
首先是超越曾断送民国政权的官商共同体利益集团的羁绊。1949年8月15日,陈云在上海财经会议的讲话中指出:“上海过去靠‘踢皮球’、‘抢帽子’的投机者有二三十万人,他们搞投机,是官商勾结,狼狈为奸,坏事正是出在政府手里。现在我们不徇情受贿,发现了还要严办,投机者不能为所欲为了。”[1]倘若没有二十多年革命中锻炼捶打出来的廉洁、精干、高效干部队伍,没有新中国领袖在开国前就下定决心对腐败苗头严打不懈,新中国战后国民经济恢复工作不可能赢得在全世界领先的成绩。
其次是超越党政管理部门内部的局部利益羁绊。为了调控市场,平抑物价,陈云非常重视运用收购和抛售物资的市场手段,以及打破国内市场封锁苗头。他指出:“只要有东西,该抛的就抛。过去,大多数同志是物资拿到手就不愿抛,这是历年物价不稳所造成的。现在要注意,什么东西什么时候抛有利。如果该抛的不抛,物价涨了,又要多发票子,从局部看可能有利,但对全局不利。要准备从稳定物价这个全局出发而抛售。”[2]为此,他强调实行内部贸易自由,打破当时常州不让粮食运往上海、赣东北不准粮食运往杭州的做法。

60年过去了,我们今天的反通胀斗争面临着同样的局部利益羁绊。首先是新生利益集团的羁绊。流动性泛滥造成的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会加大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居民生活压力,但高收入、高资产人士有能力调整资产配置,因此常常不仅能够摆脱通货膨胀冲击,而且能够从资产泡沫中牟利。正因为如此,尽管面对货币洪灾各国需要收紧国内货币政策,抵消流动性扩张造成的“基础货币扩张——带动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泡沫膨胀”压力,但受益于资产泡沫的利益集团往往拥有强大的实力操纵舆论和决策,夸大经济失速风险,从而扭曲了许多国家的宏观经济判断与决策。在今年早期关于经济“二次探底”风险讨论甚嚣尘上的背后,就不乏这种利益的扭曲;在下一阶段的反通胀进程中,我们还会遇到类似的干扰。
今天政府内部的局部利益同样也在抵消、削弱我们反通胀的效力。当前最大的通胀压力来自食品价格上涨,10月份居民消费价格4.4%的同比涨幅中,食品价格涨幅高达10.1%,非食品价格涨幅只有1.6%;这又是对社会稳定潜在冲击最大的物价项目;要有效抑制食品价格上涨压力,归根结底需要保障生产,而目前我们各大城市的“菜篮子”正面临着形形色色“开发”项目的蚕食。为了保障城市居民副食品供应,从建国初年起,国家在各主要城市郊区设立了一批国营农场,成为这些城市的“菜篮子”;但在“开发”的热潮下,各路神仙都不约而同盯上了这些菜篮子,因为这些国营农场都是国有土地,倘若用于工业、房地产等项目开发,无需经过高成本而且存在政治风险的向农民征地程序。在通货膨胀压力不大时,此举对通货膨胀压力的影响往往为人们所忽视;但正值通胀压力上升之际,此举的负面后果将迅速彰显。政府的决策和执行环节能否超越中短期“政绩”的羁绊,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我们反通胀的成败。
随着食品价格暴涨对普通居民生活影响日益突出,某些农产品产地政府可能会诉诸市场封锁手段,限制本地农产品销往外地市场,希望借此平抑本地市价。相信不少官员会认为此举是“为国为民”,上级政府对通货膨胀冲击民生的问题越发重视、某些舆论对通胀冲击的过度渲染……,这一切又会加大他们实施市场封锁的冲动。但此举仅仅是在一段时间内有利于一个小地区的城镇居民,却有损全局;各地区纷纷以邻为壑,最终只能是集体受损。重新阅读陈云1949年8月15日在上海财经会议的讲话《目前财经工作中应注意的问题》,我们对此当可加深理解。
3%的通货膨胀红线业已失守,是否需要提高红线,众说纷纭。我们无需提高红线,尽管在强大的输入性通货膨胀压力下,政府完全有可能无法实现这个年度通货膨胀管理目标;但只要政府在决策和执行中能够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超越了局部利益羁绊,就必定能够赢得绝大多数公众的认同,特别是“沉默的大多数”的认同。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