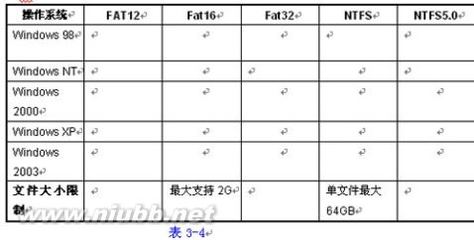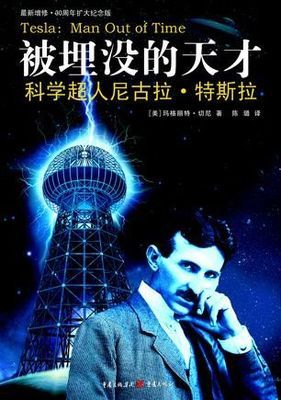第三章 初识贝尔斯登
贝尔斯登公司创建于1923年,在我进入这家公司时,它已经是一家赢利稳定的企业,尽管按照华尔街的现行标准,那时的贝尔斯登还算不上声名显赫的特权级金融机构。它有一个听起来不同凡响的公司地址——华尔街1号。如果你对这类事情很留意的话,那么,贝尔斯登应该是一个让你过目不忘的企业,但除此以外,它就再没什么与众不同之处了。走出大楼的16层电梯,进入一个光线灰暗的黑色隔断接待区,接待你的将是一位身穿蓝色工作服的老男人。主交易大厅约有1 000平方英尺,配备着木制办公桌,这些桌子似乎更像是英语寄宿学校里的书桌。所有电话均为直拨,可以直接和我们的竞争对手通话,包括高盛、约瑟芬哈(Josephthal & Co.)、亚伯拉罕(Abraham & Co.)、雷曼兄弟(Lehman Bros.)、勒布罗兹(Carl M.Loeb, Rhoades & Co.)等(顺便提一下,在这些公司中,只有高盛一家目前尚在经营,即使是高盛,也已经重新注册为州立银行,在2008年秋天,它也曾经一度濒临绝境)。交易大厅的操作区摆放着十几张办公桌,由零售交易代表使用。市政债券部有3名交易员,股票及公司债券交易员为6~8人。所有办公桌上都设有股票报价机终端,随时打印股价报价单,所有交易员都能随时了解市场行情。通过电话与客户联系的零售代表随时都可以了解某只股票或债券的最新交易价,但他们还需要了解当前出价。于是,他们会大喊:“市价是多少?”之后,工作人员将把询价指令传递给我们在交易所席位上的交易员。您肯定在电影里见过这样的镜头。
令人沮丧的是,尽管每个人似乎都忙不完手里的活儿,但这一切都与我无关。这个只有迪克森先生和我两个人组成的石油天然气部,按照公司规定,其工作职责乏味得令人可笑。我甚至觉得有点儿滑稽。在办公室的一面墙上,迪克森先生挂了一幅巨大的美国地图,我的主要工作就是用图钉装饰这幅地图。首先,我要查阅最近几期的《石油天然气杂志》,收集全国各地石油天然气勘探活动的最新动向;然后,用彩色图钉在地图的相应位置上作出标记。第三章初识贝尔斯登在第一天,我用了11分钟就完成了工作,我觉得这根本就不能检验自己的能力。相比之下,我更喜欢为期只有两周的内部培训。这样,我就可以有机会在公司的各部门走上一圈。一天上午,在被安排负责公司买卖交易的时候,我看到一群后台办公室的人正在讨论一笔刚刚完成的大交易:交易100万股明尼苏达“投资者多元服务”公司的股票。就在前一天,公司主管塞尔·刘易斯为公司最大的客户——铁路大亨罗伯特·杨买入这些股票,同时设置买入期权,并以支付给罗伯特·杨(Robert Young)的成本为基准,以高出半个点的价格买回这些股票。罗伯特·杨当时是阿勒格尼钢铁公司(Allegheny Corporation)的控股股东。现在,罗伯特·杨执行了该期权,于是,贝尔斯登便在一夜之内净赚50万美元。这笔令人瞠目结舌的交易自然让我大开眼界,更让我联想翩翩(但不要忘记,从长期看,赚到50万美元的也可能是罗伯特·杨)。但不管怎么说,我的最终工作还是用彩色图钉装饰美国地图。每天午餐时,我都会狼吞虎咽地尽快吃完,然后便马上径直跑进交易室,找一个尽量不被人注意的地方,边看边听。在那个时候,任何一家华尔街公司真正忙得不可开交都是不同寻常的事。而贝尔斯登之所以业务繁忙,部分原因在于我们精于风险套利——买卖有可能成为预期并购一方的公司的股票。负责该部门的合伙人是约翰·斯雷德(John Slade),他见证了贝尔斯登最精彩的65年。有一天,他终于注意到了我,并问我:“你是客户吗?”我回答:“不是,我是石油天然气分析部的职员。”“是吗?我们还需要一名做风险套利的职员,”他说,“但我不能把你直接从迪克森先生那里挖过来。你要想离开石油天然气分析部,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找塞尔·刘易斯。”找塞尔·刘易斯?好像不是个令人鼓舞的想法。塞尔是家里人对他的称呼,他的真名是塞雷姆·刘易斯(Salim L.Lewis)。1932年,他第一次跨进贝尔斯登的大门,成为公司的债券销售员。此前,他曾先后被所罗门兄弟和另一家公司解聘。塞尔是被首席运营合伙人泰德·洛(Ted Low)招进贝尔斯登的,而洛本人则是在4年前进入贝尔斯登的,发现洛的慧眼识珠的伯乐是公司的三位创始人——约瑟夫·贝尔(Joseph Bear)、罗伯特·斯蒂尔斯(Robert B.Stearns)和哈罗德·梅尔(Harold C.Mayer),这是一个均受过良好教育和衣着考究的三人组合,他们于1923年创建了贝尔斯登。贝尔45岁,他比斯蒂尔斯年长10岁,比梅尔年长17岁,他曾在法国、德国和瑞士受过教育,后来进军华尔街,从此便与资本结下了不解之缘,此前曾创办了一家名为丹奇格(J.J.Danzig)的小型债券交易公司。斯蒂尔斯的父亲创办了斯特恩百货商店,他本人毕业于耶鲁大学,之后,他出国学习银行学,完成学业回到美国之后,加入丹奇格公司担任统计员。梅尔和我一样,都是中西部人,我们很快就成了最亲密的朋友。他来自内布拉斯加州的林肯市,与斯蒂尔斯和我一样,梅尔的家族也是零售业里的佼佼者。他曾在常春藤联盟获得商业学位,但从不炫耀、声张(坦率地讲,这一点和斯蒂尔斯不太一样)。在20岁刚刚出头的时候,梅尔就创办了自己的进出口公司,在与斯蒂尔斯及贝尔合作之前,梅尔已经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拥有了自己的席位,这是他父亲出资97 000美元帮他收购的。塞尔·刘易斯和其他两位最大的不同点在于,他是独立创业打拼出来的,除此之外,极少会有人不把他当做绅士,因为他一贯穿着考究,但却举止平缓,镇定自若,仿佛一只美洲大白熊。他没有读完大学便进入美式橄榄球初级联盟打球,他有着职业橄榄球员的天然条件——身高6英尺4英寸,体重达到240磅,而且这还是发福前的体重。他聪明过人,极富个人魅力,绝对是一个天生的商人,既知道怎样让自己魅力无穷、诙谐幽默,又知道该怎样美言哄骗或是恶语恐吓。他本人也是犹太人,因此,肯定会有很多华尔街的“卫道士”对他恨之入骨。不过,他从来不以怨报怨。在很大程度上,是塞尔让贝尔斯登成为华尔街上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以前,贝尔斯登只是一家靠赚取佣金生存的小经纪公司,它的生存之道就是按照最低的风险承受度预测市场。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因为塞尔凭借其远见和胆量,发现了风险套利这个宝藏。然后,他用这个想法又说服了泰德·洛和比尔·梅尔(不过,他对斯蒂尔斯的方式估计是声色俱厉,最终还是吓跑了斯蒂尔斯,后者立即决定退休,成为公司的有限合伙人)。毫无疑问,创建风险套利部门的想法,将为我和贝尔斯登的其他年轻人提供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因为它让我们有机会进行实战交易,一展身手。塞尔培养客户的方式,既有精心策划、拉拢诱惑,也少不了卑躬屈膝。实际上,100万股“投资者多元服务”公司股票交易台前幕后发生的故事,就非常有代表性。多年以来,塞尔就对罗伯特·杨觊觎已久,只是没有靠近的机会,他渴望能把杨变成自己的客户,但却不知道该怎样拉拢他。塞尔知道,杨是一个狂热的高尔夫球迷,他经常到西弗吉尼亚的格林布瑞尔打球。塞尔不知从何处打听到,杨计划了一次长期出行。于是,他提前赶到那里,并找到了当地的一名职业高尔夫球手,聘请他和自己每天打一轮高尔夫球赛,连续两周。一天下午,这位职业球手突然告诉塞尔,自己第二天没有时间,因为杨要来这里,想和他打一场比赛。“哦,那可不行”。塞尔说,“你我是有协议在先的,但如果你一定要陪他打球的话,我更欢迎杨加入我们,我们可以一起打。”罗伯特·杨并没有拒绝,很自然,在打到第18个洞的时候,大家都有了一个新朋友。刚到贝尔斯登工作几年,塞尔的交易天赋和果断刚毅便让大家相信,他很快就会成为公司的领军人。他的率直和不谙世道尽人皆知,这也让我不敢接近他,每次见到他的时候,更多的还是毕恭毕敬。每天早晨,公司的三巨头——塞尔、洛和梅尔都要坐着梅尔的轿车到城里转一圈。我最大的希望就是,如果站在塞尔先生的办公室门口,他能因为我一直是公司来得最早的员工而认出我。三位老板走出电梯时能马上看到我,然后对公司的接待员说:真是个勤快的小伙子。我相信,我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表现自己的上进心;我更相信,迟早有一天,我会爬到更高的位置。在斯雷德告诉我必须当面征求塞尔的意见之后,我就开始心神不定。我花了几天的时间,才终于鼓足勇气。但令人丧气的是,当我最终惴惴不安地去找塞尔时,他的秘书aihuau.com却告诉我:“他今天不在,去打高尔夫球了。”“明天会在吗?”我问。“是的。”他的秘书说。于是,我不得不从头再来,重新酝酿感觉。不过,我还是走进了塞尔先生的办公室,并向他解释,我非常渴望能到风险套利部工作,而且斯雷德先生也已经同意接收我。他说:“但问题是,迪克森先生认为我在石油天然气分析部做油井地区分布研究也很有前途。”塞尔先生没有同意我的请求。“别着急,”他说,“我会认真考虑这件事情,就这样吧。”他确实考虑了,而且终于让我如愿以偿。我在风险套利部的第一天可以用不幸来形容。在午餐之前,泰德·洛走过来说:“你看上去不太好啊。出什么问题了?”他做了一个手势,示意我到合伙人用的盥洗室,我把一肚子的苦水全倒了出来。“斯雷德先生交给我的任务太多了,我根本就不能消化,”我解释说,“我要记下他的每一笔交易。”斯雷德的手里毕竟操纵着公司的大部分资金,“但我根本就跟不上,我连自己在干什么都不知道。”|!---page split---|现在回想起来,我承认,这是一次偶然——自从四年级时因为灯笼裤的事情和母亲发生过一次口角之后,我很少遇到过这样的尴尬,而且也是我在工作中仅有的一次不知所措。洛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带着我一起去见斯雷德,告诉他,对我不要操之过急。几天之后,我就找到了风险套利业务的规律,我的心情也随之愉快了很多。在被贝尔斯登正式录用之后,我就搬到了百老汇的77号大街,房东是赫尔曼·萨诺,他的妹妹杰伊是我的大学同学当中的交际花。那里和仓库没什么两样。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那里。尽管如此,但还是不影响我和另一个房客约会。不过,我从来没有想过替她付房租。后来,我们的约会也就越来越少了。在迪克森先生发现了我的住处之后,就对我说:“你必须马上从那里搬出来。”于是,我搬到了一个更体面的地方——公园大道莫雷山的一所高档公寓。父母来城里的时候,想看看我的住处,但我没有让他们来。我住在4层,共有6个房间,所有住户共用一个卫生间。邻居是西印度人,他们习惯于在夜里唱歌跳舞。尽管我也对他们提出意见,但似乎无济于事,因为他们有5个人,我只有一个人,只能少数服从多数。于是,我只能忍受着和他们住在一起,直到有一天,我在大街上遇到一个来自俄克拉何马城的老朋友,他来城里是为了见他的另一个朋友——艾尔·戴维斯。我觉得有必要重新安排一下自己的食宿,让我只有几千美元的存款尽可能在银行里待上更长的时间。艾尔在服装商业城工作,也正在寻找同租的室友,他还认识一个处境差不多的公关人员,于是,我们共同租下了一间地下室。我们在一起合租了两年,在这期间,几个人几乎一直争吵不断。有一次,我对他们说:“好吧,我也不想做什么好人,你们就说把我的箱子放在哪吧。”宿舍里的琐事都无关紧要,我来纽约是为了一个更宏大的计划。在那个时候,大多数风险套利的基础是铁路和公用事业行业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破产重组。这些业务是塞尔加入贝尔斯登公司之后才开展起来的。塞尔对铁路行业的衰落非常关心,也非常感兴趣。他认为,整个行业必将出现大规模的整合,而不是就此消失。1934年,他招聘了一个和他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大卫·芬克(David Finkle)。从表面上看,他们似乎是不是冤家不聚头,大卫足足比塞尔矮一头,举手投足之间,似乎都会让人感到,他的业余爱好就是看吉米·卡格尼的电影。他经常会大声告诉大家,他特别想穿上塞尔的山羊绒大衣——这件大衣足足能贴到他的脚踝,然后再戴上塞尔的卷边毡帽——这顶帽子实际上是架在他的耳朵上的。他们最大的共同点就是在买卖股票上的天赋,这两个人都是精力充沛的生意人。他们都善于和全国各地的银行、保险公司以及投资信托的财务总监打成一片,成为挚友,然后再向他们兜售股票和债券,而且交易量越来越大。他们的基本风险套利策略就是买进在法律上已失效的有价证券,并假设这些有价证券的发行人能以合法的形式脱离破产保护。在我实习的几个月里,已经成功的案例是联合轻轨公司(United Light and Railway),这家位于堪萨斯城的公用事业企业已经彻底经营失败。贝尔斯登买入联合轻轨的优先股,我们的赌注在于,在法庭判决重组之后,我们有权以这些优先股交换五家子公司的股份。在理论上,这些子公司均有较大的增值潜力。结果完全符合我们的预料。后来,我们在公开市场上抛出那些已经升值的新股票。
在贝尔斯登待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信心大增。于是,我给父亲打了一个电话,向他借了1万美元。我把联合轻轨公司的事情告诉了父亲,并说:“我觉得我也能在股票市场上赚钱。”他欣然同意,但又说,他自己也要向银行借这笔钱。六个月之后,我的第一笔投资翻了一番,我连本带利还清父亲的借款。既然我能为自己赚钱,为什么不能为客户赚钱呢?那时,我已经获得了经纪人资格证书。于是,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转变:我开始忙着赚钱了。在一次鸡尾酒会上,我认识了一个名叫莱奥·法兰德的家伙,他在莱瓦尔公司(Leval & Co.)工作,莱瓦尔公司是欧洲最大的农产品经销商之一法国路易达孚公司(Louis Dreyfus &Cie.)在纽约设立的分公司。他的办公地点距离贝尔斯登只有两个街区,我们在午餐时经常见面。法兰德又介绍我认识了他的一位朋友——马塞尔·奥布雷。于是,我首先和奥布雷先生有了业务往来。通过他,我又认识了莱瓦尔公司的总裁福纳德·莱瓦尔先生。莱瓦尔先生是瑞士移民,身材高大,嗓音低沉冷峻,但他对我却颇有好感,很愉快地接受了我的服务。莱瓦尔的所有交易都使用他的个人资金,最初只有几百股,逐渐地,他的交易量越来越大,到后来达到五六千股的大宗交易。赢得奥布雷和莱瓦尔的信任并不难,甚至可以说非常简单,那就是真诚、热心,一旦出错,绝不为自己掩饰,及时止损,绝不错上加错。在我的工作常用语中必须包括“是我的错”这句话。后来,我把这句话当做不可或缺的工作哲理,灌输给贝尔斯登的所有销售员和交易员。如果想要承担更多的工作职责,得到更多的认可,你首先必须让人们知道,你不仅熟悉全局,而且没有漏掉每个容易忽视的细节。通常,贝尔斯登在向机构客户提供债务性证券时,客户大多对这些产品没有什么认识。这就促使我开始对美国外国债券持有人保护理事会(Foreign Bondholders Protective Council)发布的月报感兴趣,虽然它名为月报,但内容却非常刺激。每天早晨阅读这份报告为我找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机会。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日本政府同意企业发行分10年偿还本息的战争债券。信越化学工业株式会社(Shin-Etsu Chemical Company)就是获得该项资质的工业企业之一。早在战争之前,信越化学工业株式会社就曾发行过企业债券。为保证企业按期偿还本息,所有日本债券发行人都必须建立偿债基金。但是,这些偿债基金在战争期间均被扣留留存,战争结束之后,这部分基金再次成为可动用资金。外国债券持有人保护理事会上的报告公布了所有被扣押偿债基金的金额,此外,由于存在大量的伪造现象,报告还列出了哪些基金为可赎回基金。这种筛选就相应地减少了某些债券的实际流通额,有些债券的流通额甚至有可能低于偿债基金的价值。对于信越化学工业株式会社,我认为,其债券目前的市价为60美元(相当于面值的40%),在两年后的到期日,很可能会按平价(面值)得到偿还。于是,我马上把这个想法向塞尔和约翰·斯雷德作了汇报,他们似乎和我一样兴奋。我们的交易员也非常激动,立刻在市场上尽可能地收购这种债券。实际上,由于债券的发行量很小,总市值仅有几十万美元。但这无关紧要——我的侦查工作毕竟给老板留下了特殊印象。他们不仅对我产生了特殊印象,更重要的是,他们最终看到了自己最想看到的结果。如果说目标就是赚越来越多的钱,那么,我就必须网罗越来越多的客户。多年从事美式橄榄球运动的经历,现在给我带来了预想不到的回报。我开始压缩进攻线,在最近的距离向客户发起进攻,从此不再忌讳给潜在客户直接打电话。我喜欢挑战,只要看到一个可能有希望的名字——或许认识他的某个朋友,或是随便能找到的什么理由,我就会抓起电话说“能不能见您一面”。每天上午8点到下午6点,我都要待在交易室里,因此,我的“冷呼叫”只能占用下班的时间。我曾经听说一个名叫加斯·林的不动产开发商,他住在华盛顿,拥有纯正赛马,经常到纽约参加跑马大赛。在给他打过电话之后,他听从了我的推荐,买了一些债券,但却很快就忘记了我的名字。因此,要把他发展成为稳定的客户,就必须当面见到他。事实证明,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有人告诉我,他在纽约参加比赛时,夜里通常都住在圣瑞吉斯酒店。于是,每天下班之后,我就会跑到这家酒店,在大堂里待上一个小时,等着他从赛马场回来。我希望能通过这个小小的伎俩,创造一次邂逅。虽然我的计策没有得逞,但加斯最终还是成了贝尔斯登的重要客户。在25年之后,由于塞尔·刘易斯和泰德·洛相继去世,他们的继承人撤出各自的资本,导致贝尔斯登出现严重的资金短缺。于是,我们决定引入有限责任合伙人。加斯是我们的第一个候选对象。(我们也咨询过前马萨诸塞州参议员爱德华·布鲁克,他刚在前一次选举中失利。在我向布鲁克提出这个邀请时,他回答:他非常感兴趣,但没有那么多的空闲现金。我问:“您能拿出5 000美元现金吗?”他说能。尽管这对他来说是一笔非常有诱惑力的投资,但最终还是没能阻止他的离开。几年之后,他在电话里告诉我,他准备把自己的账户从贝尔斯登转移到另一家经纪商,原因很简单,他们收取的佣金更低。)我们不得不感谢加斯,因为他的威信,招来了其他跟随者,他只是宣传了一下贝尔斯登的赢利能力,很多如饥似渴的投资者便蜂拥而至。多年之后,加斯和我成了最亲密的朋友。我非常珍重他对朋友的真诚和对事物的判断能力。在加斯于1983年去世的时候,他的家人请我为他致悼词,这是一个我永远也无法忘怀的时刻。这一切都是源自打给陌生人的一个电话。在信越化学工业株式会社债券这次意外成功后不久,我们又等来了另一个机会:刚刚走出破产重组的密苏里大西洋铁路公司。从根本上看,风险套利就是一场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通过判断作出的赌注,但其风险因素略微不同于普通的股票和债券交易。与接管或善意合并相比,要约收购受到制约性因素的影响更多。有些并购可能会触发政府的反垄断审查,此外,股东的反对也会对并购形成诸多不确定的影响。如果你确信政府可能会败诉或者被接管对象的管理层会束手就擒,你就可以打这个赌。从债权人的角度来看,密苏里大西洋铁路公司的重组结果取决于美国最高法院的宣判结果。假如法官能听到我在星期一上午12点30分向法庭书记员作出的口头申诉(星期一早晨宣布判决结果),并提出相同的问题:是否继续保留密苏里大西洋铁路公司?则最终的判决就是继续保留。当书记员向我宣读判决结果时,我马上意识到,有一种债券对我们特别有利。我立刻跑进合伙人的餐厅,把这个消息向他们作了通报,而他们的反应则是,迅速跑出餐厅,想方设法去到处收罗这种债券。它们的卖家包括了罗斯柴尔德(L.F.Rothschild)、约瑟芬哈(Josephthal)、亚伯拉罕以及高盛等银行。这些公司既是我们的对手,但有时也会成为能帮助我们的朋友。塞尔曾对高盛的董事长格斯·利维(Gus Levy)说过:“我们是友好的竞争对手。相互拆台,相互欺骗,游戏之后,还可以在一起说说笑笑”。在这次较量中,他们对贝尔斯登的做法非常恼火,并要求我们取消所有交易,我们最终还是妥协了。尽管双方都没有实现自己的愿望,但是从我的角度来看,这绝对是一次完胜。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