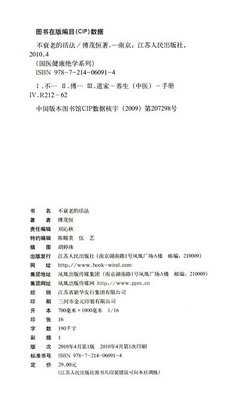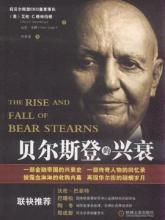第二章 昔日年少
格林伯格的相对论:只有在有机会的时候,你才能得到机会。
推论:在一帆风顺时,你根本就没有像你想象的那么聪明;在一切不如意时,你也并不是像你担心的那么笨。1948年,我还是一个21岁的小伙子。那时,我心里似乎总有一个理所当然的想法:离开家,只要能在华尔街上找到一份差事,就能赚到一大笔钱。在俄克拉何马大学读了一年之后,我转学到了密苏里大学,准备在那里获得一个商业管理学位。当时,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我在课外阅读的《流金岁月》(Gilded Age)和它讲述的传奇。我对书中的主人公完全着迷了——杰伊·古尔德(Jay Gould,出生于1836年,控制着美国最大的铁路公司之一伊利铁路公司,被誉为现代商业的创始人)、约翰·皮尔庞特·摩根(John Pierpont Morgan)、吉姆·菲斯克(Jim Fisk)和雅各布·希夫(Jacob Schiff,出生在德国的美国银行家和慈善家),他们的工作哲理、把握时机的天赋、在风险面前一如既往的理智以及在机会面前的果敢,无不让我敬慕。同样的原因也让我开始痴迷于伯纳德·巴鲁克(Bernard Baruch,1870~1965年,投机大师)(不过,我必须承认,若干年之后,我对巴鲁克的崇拜已经不如当初。原因就是我的朋友凯蒂·卡莱尔给我讲过一件事:巴鲁克曾邀请卡莱尔到他的南卡罗来纳庄园去打猎。卡莱尔发现,巴鲁克对打猎的看法和她截然不同)。他们作为社会公众中富于号召力的杰出代表,尤其是希夫的慈善事业,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希夫更是我心目中的神,这个口音浓重的德国籍犹太人移民后裔,居然能和摩根分庭抗礼,这让我感到不可思议。谈到机会,我觉得自己还不算缺少这种东西。1948年秋天,通过我父亲的一个朋友,我在P.F.Fox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这是一家专门从事石油天然气股票场外交易的经纪公司。但由于市场几个月持续低迷,于是,在快到圣诞节时,我被告知这份工作没有了。我的目的地再一次锁定在纽约,1949年2月,也就是在从密苏里大学提前一个学期毕业之后,我的父母、我的弟弟梅纳德和妹妹迪安妮在俄克拉何马市的火车站送我登上了纽约的行程。在送别时,父亲递给我一张3 000美元的支票,并对我说:“就这些钱了。”火车开动时,母亲哭着说:“我们永远也不能在俄克拉何马见到艾伦了”。这个场面很富有戏剧性,尽管有点儿伤感,但未必是悲剧。母亲或许不会知道,但我知道,我还会跑回来,到这个火车站台欣赏盛开的紫荆花。第二章昔日年少多年以后,你会看到圣塔菲铁路公司的一个旅客,他是谁呢?非常抱歉,我忘记了讲讲童年时令人心碎的磨难,不过,说句实话,我确实想不起自己经受过什么磨难。应该说,我的成长历程非常快乐。曾有人问过我的母亲:我是不是一个让人省心的孩子。母亲回答:“很难,你想象过和一个比你还聪明的四岁孩子打交道是什么感觉吗?”我当然不想当面揭穿她的谎言,在我的记忆中,我们相处得一直非常不错。我的父母是泰德·格林伯格和埃斯特·塞林格森,他们是散居在中西部犹太人的第一代美国后裔,他们的父母是俄罗斯和波兰移民。父亲是从堪萨斯城辗转至印第安纳州的埃文斯维尔的,母亲出生于爱荷华州的苏城,成长于内布拉斯加和俄克拉何马。1924年,他们相识于塔尔萨,并在一年之后结婚。当时,父亲20岁,母亲18岁。他们在堪萨斯的托皮卡做了很短一段时间的家务服务。父亲后来提到,托皮卡没有室内水管。于是,他们又来到了堪萨斯中南部的威奇塔市,两年之后,我来到了这个世界上。当时,父亲开办了一家很成功的女性成衣店。在相邻的俄克拉何马州,石油的发现已经给该州带来了几十年的繁荣。在1928年的时候,真正让父亲感兴趣的,还是俄克拉何马城那里开掘的野猫井(未经勘探盲目开掘的油井)。父亲似乎总有高人一等的感悟力,他是我见到的最有预见力的人(直到最近,才出现一个沃伦·巴菲特,但他也只能排在我父亲的后面,位居第二)。父亲清醒地意识到,他在威奇塔的生意没有什么前途,无论怎样也比不过石油城的商机。于是,在我刚满5岁的时候,父亲带着我们举家搬迁到俄克拉何马城。在那里,父亲的服装店生意兴隆,深受女士们的青睐。最后,店面扩张到了11家。在随后的60年里,这家小有名气的服装店支撑着格林伯格家族的6个家庭,还有他们的子孙——尽管父亲在兄弟姐妹中年龄最小,但却是这个连锁店的老板。我为这家连锁店没作过什么贡献。15岁的时候,我在市区商业区一家大型旗舰店的信贷部找了一份兼职工作。当时,获得商店信贷的唯一条件,就是要让你的实际消费超过自己的真实消费能力。商场风险最低的品种就是预付销售:顾客发现自己喜欢的商品后,可以采用分期付款,商店先代为保管顾客购买的商品,直至顾客付清全部货款,才能提货。有一天上午,一位女士以预付购货方式买下了一件连衣裙,并支付了20美元首付款。下午,这位女士就再次回到店里付清全部余款。这让我感到很意外,并马上把这件事报告给经理。经查实发现,商店向她错误地发放了一笔200美元的信贷优惠,她想尽快花光这笔从天而降的意外之财。“我下午可以休息了,”我告诉经理,“今天的活我已经干完了,我给商店省了180美元。”这是迄今为止我在商业界取得的最大成就。|!---page split---|媒体在报道摩根大通收购贝尔斯登事件中犯了很多明显的错误,但最夸张的莫过于《名利场》(Vanity Fair),他们在没有经过验证的情况下,便居然毫无根据地声称:在流动性危机的谣言被公开的那天,我“在早晨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吓得目瞪口呆,无所适从”。可以这么说,我最后一次不知所措的时候还要追溯到1936年,在上四年级的时候,母亲有一次曾让我穿着灯笼裤上学。我家所住的地区是相对较为富裕的,这个新近开发的住宅区室外空间很宽阔,都是红砖砂石结构的永久性住宅,而且我们在这里也算是比较富裕的人家。几年之前,俄克拉何马城的这片地区还属于一片没有名字的农村地段,基本都是刚从外地搬来的农民家庭。我的很多同学还住在农村。在读四年级之前,我一直穿长裤。在一个很多孩子连鞋都穿不起的学校里,穿灯笼裤可能是一个很严重的社会问题,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母亲居然没有想到这个。这所学校的名字叫霍雷斯·曼恩,校长埃弗里特·马歇尔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我们都非常喜欢他。在大约20年前,他的健康状况极其恶化,但他还是让儿子联系到我哥哥,把我父亲去世的消息通知哥哥。父亲去世于1980年,在去世之前,他还以匿名的方式为霍雷斯·曼恩小学的贫困儿童购买鞋子,而且要求马歇尔先生一定为他保守秘密。马歇尔先生泄露的消息让我们都感到非常意外。尽管父亲做慈善事业并不总是匿名的,但他和马歇尔有一个共同点,都非常讨厌自我夸奖、自我炫耀。但我不得不说的是,至少马歇尔先生的平等主义思想让我不愿意接受。因为很多孩子买不起垒球手套,于是,他干脆就不让所有人戴手套——除了接球手,而且这副手套还是马歇尔先生自己出钱买的。于是,在我们和其他学校的球队比赛的时候,对方都戴着手套,我们却赤手空拳。好在我们总是赢球。在我开始计划当一名冷酷无情的资本家之前,体育运动一直是我最大的爱好,我几乎把全部的激情都投入到体育中。偶尔,我也会想:如果在13岁之前不是每周都要到希伯来学校读四天书的话,我后来会不会成为一名杰出的体育运动员呢?在读高中的时候,我的历史老师克莱森也是学校的助理橄榄球教练。我在他的课堂上一直是第一名,因此他非常喜欢我。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参加了他的春季训练营。在训练营的第一天里,总共有15个孩子参加,每个孩子都跃跃欲试,希望能在教练面前一展身手。因为他很了解我,于是,我自然得到了第一个出场的机会——这样的机会当然是不容错过的。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得到了教练组的注意,这也让我此后的训练和比赛一帆风顺。春季橄榄球训练异常艰苦,整整持续了30天——我们每天都在一起混战,教练根本就不在乎我们是不是会受伤,因为他们知道,你可以有一个夏天的时间用来疗伤。我得到了一个替补中卫的位置。父亲也来看我集训。在看到首发中卫的表现之后,他问我:“你和那个叫吉米·欧文斯的家伙是同一个位置,是吗?”我说:“是。”“他和你还是一个年级的吧?”我回答:“是的。”“你要么退出,要么就换一个位置。”后来,吉米成为俄克拉何马大学橄榄球队的队长,此后,球队几乎战无不胜,并在1949年赢得美国大学生美式橄榄球“砂糖碗”大赛的冠军。事实证明,父亲在这件事上同样是正确的。春季训练营结束时,我的体重是148磅。我觉得这个分量显然是太轻了,于是,我开始狂吃暴饮。母亲以为这要归功于她的厨艺精湛,但看着我暴饮暴食,父亲却感到有点儿担心。到秋天的时候,我的体重增长到171磅——我花掉了整个夏天的时间来帮人卸货,主要是为了健身——但这对我的速度一点儿也没有影响。春季里,我还参加了田径训练。如果你现在看到我的话,肯定想象不到我当初的样子,但只要查一下资料,你就能知道了。我的100码成绩曾经达到10秒,在初中和高中时,我一直是俄克拉何马城及所在地区的100码冠军,并在俄克拉何马州田径锦标赛中获得过100码的第四名和220码的季军。此外,在高中阶段,我还曾代表学校赢得了州际比赛冠军,还赢得了全州最快橄榄球选手的称号。为此,俄克拉何马大学为我提供了橄榄球奖学金。1945年秋天,我迈进了俄克拉何马大学的校门,并且在第一场比赛中有上佳表现。但是,在第二场对内布拉斯加大学队的比赛中,我却很不走运,比赛中,我的背部严重受伤。更糟糕的是,这场比赛也就此结束了我的橄榄球生涯,也迫使我转学到了密苏里大学——如果我不想继续打橄榄球的话,我还是找一个离家18英里以上的地方,这也让我的身份略有转换。在密苏里州,男孩和女孩的比例是5∶1,我的男同学大多都比我大5岁,因为很多人都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服过役。我的室友之一就是杰伊·萨诺,他后来成为拉斯维加斯最著名的赌场开发商之一,他最早提出了开发“凯撒宫”酒店和“马戏团”赌场饭店的想法,并将这些想法付诸实践。他曾对我说:“格林伯格,你长得很帅气。但是你的这个名字可不怎么样,很难让你在社交圈里出名。”于是,他帮我想了一个名字,他认为我应该叫“大腕·盖恩斯波罗”。几天之后,我还是把自己的名字改回了格林伯格,我可不喜欢“大腕”这个称呼。也许这个名字确实给我带来了很多不便,不过,我自己好像没有注意到。在向未来的老板介绍自己时,我还是自称“艾伦”。我一直认为名字不会对人生有什么影响,尽管我最初应聘的几家公司都觉得我不合适。我遇到过一个来自威奇塔的人,他叫内特·艾普曼,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石油商人,后来也搬到了纽约。艾普曼先生曾为我写过六封推荐信,他在信中写道:“我不认识艾伦,但我认识他叔叔,如果您能帮他一把,我会感激不尽。”于是,他帮我在P.F.Fox公司得到了一份工作。父亲叮嘱我,一定要住在条件好的酒店,我一切照办——住进了38号大街的托斯卡纳酒店。每个工作日的早晨,我都会穿上西装,系上领带,到位于下百老汇的P.F.Fox公司办公室上班。公司的老板弗莱迪·福克斯一直不好意思收回为我提供的这份工作。于是,他给我找了一张办公桌,配了一部电话,给我创造一个继续找工作的条件。他的秘书海泽尔很喜欢我说话的声音,但又不习惯我的俄克拉何马鼻音。于是,我还要经常给她讲讲笑话。在纽约,我唯一的熟人,就是在威斯康辛大学暑期班里认识的一个女孩。我以为她会愿意做我的向导,但是在我给她打电话的时候,她的第一个回答竟然是“我刚刚结婚”。有一个周末,我独自一人去看冬季古董展销会,在那里,我遇到了一个娇小可爱的女孩,我主动提出和她约会。我可不想一个人干熬。这里的天气非常寒冷,我一点儿也不习惯。于是,我干脆就把大部分时间都打发到纽约公立图书馆的主阅览室,因为那里既干净、温暖,还有整洁的盥洗室和世界上所有的书籍。我每天都要去那里,但看得最多的就是介绍魔术的书(8岁的时候,我在俄克拉何马城看过一场哈利·布莱克斯通的表演,从那以后我就开始对魔术着迷了)。对于纽约公立图书馆带给我的快乐,我后来给予的报答就是慈善性捐助。后来,内特·艾普曼的推荐信让我有机会在几家华尔街公司得到面试的机会。巧合的是,这些公司的老板几乎是清一色的犹太人:沃特海姆公司(Wertheim)、勒布罗兹公司(Carl M.Loeb,Rhoades & Co.)、萨托留斯证券(Sartorius)、贝奇证券(Bache)、亨氏投资(H.Hentz)以及贝尔斯登。但每个人都劝我回俄克拉何马,直到我走进贝尔斯登的大门。当时的确算是天赐良机,就在他们的石油天然气部门急需人手的时候,我适时地出现了。于是,我就成了迪克森先生(他的全名是莱昂纳德·迪克森,但我从来没有听到有人叫他的姓氏)的助理。尽管还没人向我介绍过这份工作的职责是什么,但我马上认定,这就是属于我的工作。我得到的月薪是135美元,随后的星期一就可以上班。我一天也没有推迟,1949年3月8日,我开始了自己的贝尔斯登之旅。那一天,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交易量为80万股,道琼斯指数收盘为180点。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