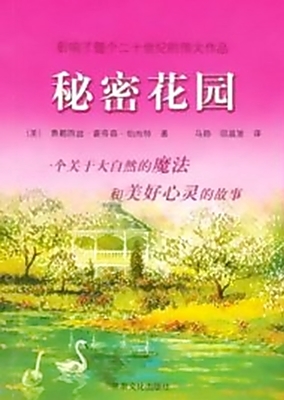拐大弯,走长路 我提出联想要做“没有家族的家族企业”,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关于事业心的问题,即接班人是不是拿企业当成事业来做。接班的人不仅要考虑企业当前如何生存和发展,还要考虑怎样让企业长久地发展下去,一代一代地把事业心传下去,把事业传下去。没有家族,不能够真的传给自己的儿子,因此事业的相传难度就挺大。怎样从物质利益到精神利益上都能够让接班的人感觉到,这是我自己一生的事业,这是联想在谋求的一种创新型机制。 我大约从1990年就开始考虑选拔接班人的问题。不是因为创业者的年龄大了,而是那套班子都是技术出身,综合能力不够强。杨元庆和郭为都有很强的能力,郭为比较早地就进入到了决策层,杨元庆则是从底下做起,但有更大的战略。经过认真思考以后,联想的自制产品业务肯定是要杨元庆做的,因此杨元庆负责总体业务的可能性会更大。但由于历史的原因,集团代理销售的业务与自制产品的主体业务是两块业务,甚至领导人都在不同的位置,郭为相当长的时间在香港、在南方。如果没有过渡地把两块业务合到一起,就不仅仅是郭为配合不配合的问题,而是无视历史情况存在的问题。 1997年,联想的一个重大举动是把香港联想和国内联想合并。不同业务的融合需要时间,但我们没等融合就采取了措施。如果那时我不把两者分拆,等到我已经不在直接指挥者的位置上时,谁有这么大的权威来不伤筋动骨地进行调整呢?如果两个人产生矛盾,将会给企业带来很大的损失。我的年岁大一点,是创业前辈,再同具体职位的权威合在一起,才能解决两方的问题,否则留下的肯定是无穷无尽的困难。 所以我用了中国式的解决方式。为了分得好,我还采取了另外一种措施:先叫二位合作一段,我不管事,以杨元庆为主,郭为做副手。不到半年两个人提出来,谁也受不了。杨元庆提出,他愿意积极配合拆分,郭为当然更愿意配合。这样对郭为本身是一个很大的支持。分了以后,郭为的代理业务在全国做到老大,每年平均20%的增长,当然我还是不满意。

从这个角度讲,分拆的处理方式也是创造。我的治理情况是怎么样,我就怎么做,现在实际效果还是可以的。现在我们出售神州数码的部分股票,让郭为能够对这个企业负有更大的责任,有更直接的关联,这是件好事。联想控股会站在为股东获取最大商业投资回报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而不会以太多的情感来说:“这是我一手创业的,我舍不得卖”。这不符合市场的规律。 现在我不是考虑具体领域的投资,而是考虑例如“联想控股未来是不是就这么发展下去”这样的问题。到了一定的时候,逢山有路,遇水有桥。我做事喜欢“拐大弯”,酝酿很长时间以后,在联想控股放出什么理念,统一在什么思想下,肯定会有具体的部署。 从实业家转到投资家,我感到最大的差别是:实业家要上台演戏,投资家要懂得看戏。投资家把戏演好的规律要总结出来,未必上台自己演,我就是一边演一边总结规律。 会看戏的人,就懂得找什么样的人去演,给什么样的人投钱。这是第一层差别;第二层就是实业家领导的是军队,而投资家领导的是武艺高超的侠客。相对来说,实业家难度更大,难度就在于你带领千军万马,这个执行力的掌握是有困难的;而对于投资家,执行力就是两三个人的事,自己说怎么做就怎么做。好的投资家最好应该要做过企业,对企业的事能弄得明白,不是吃了第三个馒头就说前面的馒头不用吃了。如果你要问我创业与守业孰难,我的感觉是创业更难。虽然创业之后,让别人来接班并把它稳住也是很困难的,但是真正最要命的还是白手起家。现在我对投资家以后的生活还没有更多的考虑。我以前到今天走过这段路,是因为我非常明确地给自己一个定位,就是要做好企业,做一个好的企业家。围绕着这个怎么做想了很多,超出这个以外还没有想过,没有想明白当然不敢说了,这也是中国特定的环境。
 爱华网
爱华网